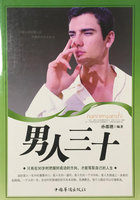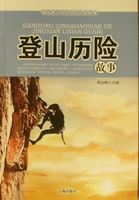老刘哥俩在老油灯下,头碰着头,拧了一夜的眉心,老屋地板上扔下半堆土烟头。最后,老大吐掉黑黄的烟蒂,一拍大腿,定下主意:也买辆滑溜锃亮的摩托车,在村里显显眼。
这几年,眼看着乡亲们一天天光鲜抖擞,一个个置起那两个轮子、四个轮子的铁玩意儿,在身旁哧溜哧溜地闪过,带过一阵昂扬的风,老刘哥俩心里便酸不拉搭的,窝着一口闷气。老哥俩一直守着那间破石屋和那摊小生意,日子一天天磨蹭下去,把自个儿也磨蹭成老光棍,日子总过得紧巴巴的。乡亲们的日子却是越过越红火,走起路来脖子上那玩意也越抬越高。老哥俩便自觉埋低了黝黑的脸,胸口憋得慌。
“哥,咱俩有车也骑不了呀。”老二疑惑地眯着眼。
“骑啥呀。”老大吐着烟圈,显然早有打算,“咱哥俩一辈子都没走出这村子,两个脚板还不比那铁玩意活络些?人活着,为的争口气呀。”
老哥俩勒紧了腰带,把祖宗的老木柜翻了个底朝天,把沾着边儿的亲戚都兜了一圈,磨薄了脸皮把钞票一点点凑起来。几个月后,拣了吉日,哥俩收拾齐整,把包了几层烂布废纸的钞票揣在怀里,挺直了腰板儿,挑车去了。
老刘这穷哥俩也买上摩托车了!这消息比他哥要娶亲更让人稀罕,谁不知这对光棍连脚踏车也从未碰过。
“小心!小心!”老大跟在搬运工人后面指指点点,“放下,放!”车果然锃亮气派。老刘哥俩把新车停在寨前晒谷场中,一前一后,一人推着,一人扶着,绕着谷场走。引来大群乡亲驻足,对着那车、那哥俩直挠脑久,琢磨不清,便三三两两谈论起来。老刘哥俩几时出过这等风光,兴奋得满脸通红,两眼放光,高昂了头,推着新车,绕得格外起劲。老哥心里叹道:娘的,活了这辈子,就显了这么一回啦,也不冤了。
绕完场子和巷子,新车被搬进了网满蛛丝的老屋。放哪儿哥俩都觉得不对劲儿,屋里旧铁罐、破木凳、废电线,还有分辨不出来的东西,沿墙根杂成一堆堆。新车这么一横,人连闪身都有问题。哥俩又心疼车,怕它碰了、脏了、潮了。最要紧的是,现在的人猖狂得很,上了几层锁的车,一忽儿就会被贼儿开得没了踪影,室内失窃也不再是新奇事。于是,老哥俩又在油灯下嘀咕起来。商量出一个主意,哥俩委屈些,挤一张老床,挪出一个老炕,把那宝贝蛋般的车抬上炕,横放下来,盖上两层旧席子,放下熏得乌黑的帐子。想来那车该是十万分的舒适妥当了,老哥俩挤在老床上也顿觉舒畅了。
这事又让乡亲们饭后茶余的闲聊几天都显得别有兴味。老刘哥俩在村里人此不再板着脸、靠着路边儿走了。也学会了倒背了双手,迈迈大方步,高着调门讲话,如今哥俩也是有车的人了。没事时,哥俩就把车推出来,扶着绕绕走走,脸上便即时镀了一层光,暂时忘了借来的钱并未还,要债的人也正盯着不放。
未过一月,老刘哥俩又闪在路边儿走,脸又埋下去,变得更黑了,蓬乱的发却变白了。原来,这些日子当初借钱给老哥俩的人,见他们借来的钱竟是去买来这么一辆用不着的车,只显摆不使用的,心里便不满了,向老哥俩要不到钱时,嘴上也说不管客气不客气的,说的话也难听起来。老哥俩穷虽穷,还是有点心气的,哪受得了这些熟人的冷言冷语。可心气归心气,钱还是还不上,理亏气短,见了人那头又不知不觉低下去。这样一闹,推着车出来绕圈还有什么意思?再说,那车贼重贼重的,老哥俩虽是找锄头的主儿,那扛不住那东倒西歪的大家伙。新鲜劲一过,溜车就成了一种苦差事。这新车也成了一个甩不掉的累赘。慢慢的,那车在账子里一点点爬上铁锈,每每老哥俩看到那床,就不由得相对着叹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