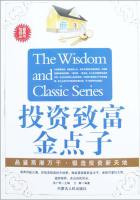错落昏黄的灯圈中,才看得出雨丝依然密密地织着撒着,远一点的地方就分不出天上和地下了,夜色让雨浸成一块巨大的灰黑的布,粘在每一块裸露在外面的皮肤上。灯圈是卖菜人放在车架,挂在车头上的手电筒发出的。他的车就挤在这一队凌乱的卖菜人行列中。身后就是市场,可卖菜的人都列在市场外的路边,仿佛这样就能快一点把菜卖出去。其实他们都列到这路边,生意并没有好起来。站了快一个钟头了,可这队里成交的人寥寥无几。
他扶着车架后那筐堆得高而实的菜,轻轻地跺着发麻的脚。一阵酸麻过去,寒气立即顺着又湿又粘的裤脚漫上来,不仅两条大腿,全身都止不住发起抖来。雨衣仿佛也让雨丝一点点渗透了,粘腻地贴在身上、脸上。他扯扯脸颊边的雨衣帽,目光定在那光圈里斜而密的雨丝上,仿佛从那儿看到与别人眼中不一样的世界。
梦让闹钟扯成两半的时候,他眯着眼按了床头灯,已经是他睡前设置的第二次闹钟,三点十分了。他轻轻动动身子,想把胳膊从妻子的怀里抽出来。妻子在梦里呢喃了句什么,把他的胳膊抱得更紧,头也往枕头上落得更舒坦些。他让手静静地固定成一个半抬半抽的姿势,望着妻子脸上浓得化不开的睡意和嘴角那丝大概从梦里带出来的笑意,不舍得再动。用另一只手揉揉眼皮,让自己清醒一些。望望闹钟,长针又走过了两格,该起床了,爸妈想必早到菜园里了。他边把胳膊一点点抽出妻子的怀,边轻拍着她的颊唤着,我该摘菜去了。不知是因为他的呼唤还是突然失去那只壮实的胳膊,灯下看到妻子长长的睫毛抖了一会,稍稍扯开一丝缝,嗯,睡吧,还早着哪。说罢,下意识地又扯了他的胳膊,把半边脸颊枕上去,睡得更自在些。他抬头去看那扇小窗,确实只有黑乎乎的一团。但还是晃晃妻子的肩膀,得出去啦,要不就太晚了。这回妻子清醒了些,她睁开朦胧的眼,打了个柔软而绵长的呵欠,半是心疼半是撒娇,哪有半夜摘菜的,外头还下着雨,又冷成这样,出去把人冻坏了。说着干脆伸出暖柔的胳膊把他拥住,春天的雨夜还有什么地方比被窝更留人的?本来已半爬出被窝的他忍不住又沉到被窝里去,像哄孩子般拍打着妻子的后背。
他们两个多月前刚结婚。就这两个多月,妻子已经养成了睡觉或者半拥着他或者抱住他一条胳膊的习惯,她一向怕冷。不行,闹钟的长针又爬过了两格,无论如何要起来了,他挪挪枕头,说我出去了,你好好再睡一觉。妻子睁开眼睛看他一件件穿衣服,身子渐渐蜷起来,他刚刚出被窝,她已经感到冷了。他最后站起来,给妻子掖掖身四周的被子,说你睡吧,回头我给你带点东西来。妻子让被子围着的脸就展颜了。几乎每次他半夜出去摘菜,都要给妻子许下这小小的礼物。卖了菜,镇上一些店面也就开了。他就给她带点东西,有时是几个热乎乎的肉包子,有时是一两个她爱吃的粽子……
雨丝在雨衣帽檐凝成大大的水珠,滴起他眼里,他猛地一闭眼,眼光从光圈收回来,又落在那筐菜上面。菜还没卖出去,但他并不急,正想着这回得给妻子带点特别些的礼物,今天是妻子的生日,他昨晚就琢磨开了,今天不买包子粽子之类的。
其实卖菜并不是他的本行,他大学毕业后在镇政府当着一个小小的办事员。他的大学就是靠着爸妈种菜和养猪供起来的。工作后,家里依然种着菜,只要到菜的收成期,爸妈和他大多得半夜起床到菜园,赶在天未亮之前把菜摘好。他大学毕业后,为着多卖点钱,摘了菜后,除了一部分卖给菜贩子,另一部分就同爸妈轮流到菜市场零售。毕业后,没再让年纪已大的妈去卖菜,多半是自家摘了菜,让菜贩子到菜园直接称去。但最近雨水好,菜长得快,整片菜区的产量都在上升,菜价大降,菜贩也难等了,只好自己把菜载到镇上批发出去。
到菜园时,爸妈果然都到了,一人披着一领雨衣,就着风雨灯,蹲在湿湿的泥上割着菜。菜已割下一截子——菜太便宜,买菜的人都挑剔起来,菜根要割去,不能整棵拨的,还要一捆捆摆整齐。他跟爸妈招呼了一声,蹲下去,打开小刀去割菜,每棵菜择去烂叶子。刚割了两捆,手就冻得有些僵,雨落在背后的雨衣上,窸窸窣窣,手指头的冷意似乎又重了些。但胸口处却暖暖的,绕着一团温软的东西,好像刚刚从被窝里带出来的暖意都挤到那儿去。突然,几滴雨水顺着脖子往领口直滑到胸口处去,他打了个激凌,不觉用手背隔着雨衣去揉胸口,把那几滴雨水揉出此许热量来。
一个多钟头后,他觉得手指上的冷意一点点爬满全身,整个人发冻发僵的时候,妈手半撑着腰,缓缓站起来说,今天就这么多吧。
他抬起头望望着面前一大片油绿的菜说,就这么多?前面这些都该割了,过几天就老啦。
妈稍稍叹口气,老了就老了吧,行情不好,这一百多斤能卖出去就错了。
于是,他站起来,把菜捆捆在菜园头的水池里洗了,装进筐里。到这市场门口的时候,卖菜的已来了不少人。
面前那块灰黑的湿布不知觉间一层层变淡,渐渐的,近处公园大门的轮廓像让什么人一点点描出来,一点点加深,也能认出身边同在卖菜的一些熟人来了。不早了,雨虽然没有停的意思,但天亮的速度并不因为雨而慢一些。卖菜人之间的谈话和议论焦灼起来,谈着眼下这让人发愁的菜的行情。天亮了,意味着菜摊子需要批发菜的大都把菜买回去,准备零售了;天亮了,菜还没有批发出去,错过了早上卖菜的黄金时间,除了零售一些,菜是批发不出去的;天亮了,菜批发不出去,把菜再载回家,还要费些精力,菜带回去除了喂猪,就是沤肥了。
他终于有些急起来,眼光四处跳来跳去的,来批发菜的人很少,且大多向平日相熟的主顾走过去,这个时候,照顾到某一个人就算是人情。毕业前是妈来卖的菜,毕业后在菜园卖菜居多,因此,他在这卖菜的队列里算不得熟面孔。青菜摊子主人的目光多半从他面前轻轻掠过去。他也不好意思像一些人那样,挥着手引人注意地招呼主顾。
天完全亮了,有人开始降价了。更有甚至者,把满筐的菜原样载走,说是镇上有几家亲戚,各家多多地分几斤,剩下地带回去喂猪。他想着,自己镇上没有亲戚,自他毕业后,为着不让爸妈太幸苦,猪也不喂了,他没有勇气把菜带回去。他突然想起妈半撑着腰站起来的样子,还有早上出来时对妻子说的那句话。
卖菜的队列零落起来,已经有满脸睡意的主妇出来买菜了,他的不远处就摆了一个零售摊,他围着自己的那筐菜,无目的地走来走去。每每眼光落在那筐菜上,就默默安慰自己,这样的好菜会没人要?油绿鲜嫩,爸妈种菜是舍得下大功夫的。价钱低点也行。
终有个中年人走近来,看着他那筐菜。他认出来了,以前卖菜时,这中年曾买过他几回菜,算半个熟人。他立即带着笑迎上去。中年人说,现在菜价太低,他贩菜也难。他急忙说,都知道,随便给个价就行。
中年人说,只要一百斤。
他说,这就一百二三十斤,都称去吧。
中年不再说什么,帮着他把菜从车上解下来。
卸完了菜,中年人的手从裤袋里摸出一个薄膜袋裹着的包,数出几张票子,轻飘飘放在他的手心,转身拉着菜走了。他的目光落上手中那几张票子上,好半天发着呆。看看那中年人的背影,再看看自己的手,突然有种滑稽的不真实感。一张五元的,三张一元的,一共是八块钱!
好半晌,他弯腰地提起地上的菜筐时,才突然发现几张钞票还攥在手里,本来就有些破旧的钞票让他的湿手揉得粘乎乎,皱巴巴的。他把票子揣进口袋,边把菜筐绑在车架上,边想着这几块钱能妻子带点什么。本来,就在中年人过来称菜的瞬间,他想好了给妻子带束花回去,她一向爱花,常到菜园田头摘些野花野草之类的,拢得热热闹闹插到透明的玻璃瓶里去,也颇象模象样。但现在这八块钱能买上什么花呢,或者连走进花店的资格也不够吧。当然,也不是非得用这八块钱买花,重新买一束花也不算什么难事。然而,他脑里不知哪个角落里扯出种莫名的固执,非要像以前那样,用他半夜摘菜,半夜卖菜的钱给妻子买东西不可。
几个人冒着寒雨,蹲了大半夜,顶着夹雨的风摘了菜,把一百多斤菜载到市场,站了将近两个钟头,够不上买一束花?这念头如魔咒一般绕着他的脑子,一圈圈地缠,缠着缠着,仿佛连心窝处也绕上了一些,有些发闷。
载着空筐的车在市场周围无目的地转来转去。雨虽然依旧密而冷,街上还是在一点点热闹起来,大都是出来买早点,买肉菜的理家人,街边的店面一个接一个打开来。得回去了,要不上班会迟到。心里急着,可踩着自行车的脚仍然迟缓着。
他两眼稍显空洞地直视前方,习惯性地让自行车朝前慢慢而去。在自行车驰过了那农民的小摊十多米后,他才突然想起什么。猛地一捏车刹,自车行吱吱尖叫了两声,他一只脚支住地,一步步往后踩退着,退到一个农民摆的摊前面。这摊不知该叫什么摊的,看来是自家种着什么就卖什么。左边摆着几种家常菜,右边摆着十来盆普普通通的盆景花之类的。一只最边上一只塑料桶胡乱插着一些百合花,他没有理由地觉得这是农民种在家门口的篱笆边,要摆摊时顺便摘下来凑数的。不过,百合看起来挺精神,除了没什么包装,细看起来丝毫不比花店里卖的差。他仍半坐在车上,指着百合问,一支多少钱?
农民直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好像听不懂话里的意思。终含含糊糊地反问,要多少支?大概他也还没想好价钱吧。
他支了自行车,蹲下去挑了四支,向农民晃了晃。
一块钱。
他大为惊异,真是想不到的便宜——此时他完全忘了这四支花该当他多少菜。立即又挑了四支,凑了八支,从衣袋里抽出刚刚揉得发皱的两张一元钞票递过去。
八支百合,跟小摊上的农民要了几根稻草,缚成一束,轻轻固定在筐内一边。百合花绽放在筐内,一路上的心情便无比灿烂起来。
回到家,妻子刚刚起床,洗过了脸,等他回来吃早饭。看见随着他摆曳而近的那束百合,笑意一点点浓稠。她把半个脸埋到洁白的花朵里去,喃喃赞着,太美了。
他身上的衣服湿湿地粘在身上,剩下的六块钱皱成团缩在半湿的衣袋里,但看见妻子那张从百合花后抬起来的笑脸,刚刚卖菜脑里心窝处的那些缠缠绕绕软不知怎么受了热,软软地化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