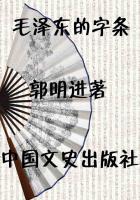儿童
我刚上小学时,家里出了件大事。
我们搬进有两层楼的新房,第二层还没收拾利落,叔叔拿块砂纸打磨着窗栏,院子里是一群人,因为新房子而激动得大声嚷嚷。我和那群人的孩子,表弟表妹们看电视。
忽然“扑通”一声闷响,院子里嚷得更加厉害,我们把音量开大些,因为太吵。
最后一个大人走过来责骂我们……原来叔叔从楼上摔下来,而我们只顾看电视。
我们一哄而出围在平板床四周(他已被放好,并有人去找车)。叔叔青紫着脸,已不会说话。我们敷衍地看一眼又拥回去看电视。
但平静已被打破,大人不住叫我做这做那,在我看来,他们只是激动地大喊大叫走来走去,没有任何意义。而我因此不能再看电视。他摔的真不是时候啊,我想。我怀着敌意,看那个脸青紫的人,很不高兴。
少年
叔叔因肿瘤到市里住院开刀,但情况一直不好。
忽然一天从医院打回电话,他梦见门口青石板下有块石头,挖出来他的病就会好。
说的人眼睛放光,听的人欣喜若狂。
堂弟从医院回来后我们就开始干。镐、铁锹,青石板被刨开,掘地三尺。
姑父们干干停停,显是觉得青天白日做这个有些滑稽。停下来抽颗烟,互相打趣两句,谈谈昨晚电视。
表弟一直不吭声,蹲着把每块土坷垃拣出来丢掉。
“行了吧?”姑父和爸爸已经汗流不止,有些不耐。
表弟不做声,发狠地拣土坷垃,可是—没有找到那块石头,连一块稍微成型的砖头都没有。
人都走了,坑也填上,表弟受委屈似的站着不动。
他甚至不懂肿瘤是怎么回事,化疗是什么。也许他只觉得这一切很麻烦,想快点结束快点恢复。而这些成年人却漠不关心,不帮他把那块石头找出来。
他在烈日下站了很久。
青年
叔叔住院后我一次也没去看过。
有成把理由:要上班,去看望的人那么多也不缺我一个,夏天病房人多反而闷热等等等等。
那天晚上深夜,看病的姑姑们从医院回来叫醒妈妈,隐约听到“不行了”……我忽地坐起来:糟了,我还没去探望过呢。我叫住大姑问能不能第二天一早去看中午赶回来就成—大姑打断我:人已经拉回来了。
我猛地咬住后半截话,为自己的自私震惊。没有人注意我,他们匆匆忙忙地办这办那。
而我,就在夏天的夜,静静地,出一身汗。
舅舅
夏季到了,听人讲着哪里的刨冰好吃,想起我第一次吃刨冰。
大舅得了血液病,挨过手术、放化疗,渐有起色,就到我家住散散心。
县城里其实闷得很,一到晚上就都坐到电视机前。于是,舅舅对我说:我们去舞厅玩吧。
我吃一惊,还是去了。俩人像傻瓜般坐在舞池旁边长椅背上,看人群转来转去灯光明明暗暗。我很冷淡,但看到十几岁的女孩们低着头小心翼翼地踩步子,还是觉得心里微微一动。青春的气息像暗器一样伤人。
我不知道舅舅怎么想。
他问我要饮料不,我摇头。他沉吟一下,果断地走向刨冰摊,要了两杯。
刨冰是红色,味道忘了。回去的路上,感慨一晚上消费7块钱,常来是不行的。
再后来,又在郑州见过他一次。做例行化疗,光头,戴帽子。我们又出去逛街,土包子进城般盯着夜总会、盯着食品房看。而他能吃的东西已经不多。他说,过阵子好点,就去炒股,给孩子攒点钱。说话时,他淡淡笑,又认真,又烦恼。
最后一次见他,是在他家。他终于不用为钱烦恼,为病操心。
五月是个残忍的季节,春天的花凋落,而绿叶却不可遏止地蓬勃起来。空气中充满生长的味道、欲望的味道。人们袒露四肢挤在热风中人堆里,揣着各自的一肚子心事。
其实世界本质就是残忍。只有从临终眼中才能看到美好。然而那时,他已来不及享受。
1998-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