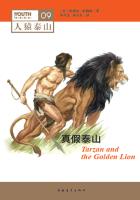宝玉伤得不轻,于是众人都来探望。先是薛宝钗来看望。她手里托着一丸药走进来,袭人赶紧上前迎接。宝钗来到宝玉床前,见他慢慢睁开了眼睛,可以说话了,心中宽慰了些,便抱头叹息着说:“你如果早听人们的一句话,也不至于有今天的结果!”
宝玉已被打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只有呻吟的份。
宝钗劝慰了一会儿,便走了。这里宝玉无奈臂上作痛,如针挑刀挖一般,加上天气炎热难耐,于是昏昏沉沉地又睡着了。迷迷糊糊,感觉琪官好像走了进来,向他诉说被忠顺府捉拿的事;过一会,又好像看见金钏向自己哭诉她投井之情。宝玉正处在半梦半醒、迷迷糊糊之际,突然觉得有人在推他,便从梦中惊醒,睁眼一看,不是别人,正是黛玉。黛玉两只眼睛哭得像个桃子似的。
宝玉看见黛玉哭泣成这个样子,心中非常难过,于是长叹一口气说:“你来做什么嘛?
太阳刚刚落山,那泥地上依然是非常热的,如果中了暑,咱俩都病倒了,怎么办才好!”然后又咬牙忍着伤痛宽慰黛玉说:“我挨了打,现在也觉不出痛来,我现在这个模样,是故意要装出样子来吓他们,好让他们在外头散布消息给老爷听,我真是假装的,你别信以为真了。”
宝玉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听院外有人喊道:“二奶奶来了。”黛玉便知是凤姐来了,连忙起身说:“我从后院走吧,回头再来。”宝玉一把拉住说:“这又奇怪了,好好的,怎么怕起她来了?”黛玉说:“你瞧瞧我的眼睛,他们又该拿咱们取笑了!”宝玉听了,赶忙放了手,黛玉三步并作两步转过床后,刚刚出了后院,凤姐从前门进来了,问宝玉:“可好些了?想吃什么,叫人上我那里取去。”接着薛姨妈来了,贾母也又打发人来看了。
晚上宝玉睡了,王夫人打发人来叫一个跟宝玉的丫环去,袭人去了。王夫人问了宝玉的伤情后,袭人正要走,王夫人说:“站着,我想起了一句话问你。”袭人忙又回来。王夫人见房内没人,便悄悄问袭人:“我好像听说今日宝玉挨打,是环儿在老爷跟前告了状,你听到了这话没有?”
袭人说:“这个话,我倒是没听说,只听说,因为二爷认识什么王府的戏子,人家来和老爷说了,为这个打的。”王夫人摇头说:“不止这个,只怕还有别的缘故吧。”袭人说:“别的缘故,我实在不知道。”袭人低头迟疑了一会,说:“今日我大胆在太太跟前说句莽撞的话,论理——”说了半截,又咽住了。王夫人说:“你只管说。”袭人说:“太太别生气,我才敢说。”王夫人说:“你说就是了。”
袭人说:“论理宝二爷也得老爷教训教训才好呢!老爷再不管,不知将来还要做出什么事来呢。”
王夫人听了这话,便点头叹息,不由得对着袭人叫了声:“我的儿,你这话说得很明白,和我的心里想的一样,并不是我不知道管教儿子,只是我已经快五十岁了,仅仅剩下他一个。他又长得单薄,况且老太太疼得宝贝似的,如果有个好歹,上上下下都不安。”
袭人看王夫人对她态度极亲热,又说:“我一直惦记着一件事,要想给太太说,只怕太太疑心,不但我的话白说了,且连葬身之地也没有了!”
王夫人听出这话内有话,忙问:“我的儿,你只管说,近来我常听人夸你,我还以为你不过是对宝玉照顾得好或说话和气,谁知你刚才说的话全是大道理,正合我的心思,你想什么,只管说什么,只别叫别人知道了就是了!”袭人说:“我是想,请太太怎么变个法儿,把宝二爷从大观园里搬出来住才好。”王夫人一听这话,忙问什么意思,袭人说:“太太别多心,我想宝二爷如今也大些了,况且林姑娘和宝姑娘又是两姨姑表姐妹,虽说是姐妹们,到底是男女之分,日夜在一处,起坐不方便,不得不让别人挂心……近来我为这件事,日夜操心,又恐怕太太听着生气,所以总没敢说。”
王夫人听了越发喜欢袭人了,笑着说:“我的儿,你竟有如此心胸,想得这么周全,你且去吧,我自有道理,只是还有一句话,你如今既然说了这样的话,我索性把他交给你了,好歹多留点儿心。”
袭人走了之后,宝玉便叫丫环晴雯来到跟前说:“你到林姑娘那里去一下,看她在做什么,她要问我,你只说好了。”晴雯说:“平白无故地去干什么?到底捎句话,或者送件东西去,不然,我去了怎么说呢?”
宝玉想了一下,便伸手拿了两块白手帕,递给晴雯说:“你去了就说,是我叫你送手帕来了。”晴雯一看说:“这可奇怪了,她要这半新不旧的两条手帕干什么?她一看就恼了,说你取笑他!”宝玉笑着说:“你放心,她自然知道是什么意思!”
晴雯听了,只得拿了帕子,往潇湘馆来。
到了潇湘馆,黛玉已经睡了,听说有人来了,在屋里问:“谁?”晴雯回答:“是我,晴雯。”黛玉问:“做什么?”晴雯回答:“宝二爷叫我给姑娘送帕子来了。”
黛玉听了心中纳闷,心里想,干什么送帕子来?便问:“帕子是谁给他的?必定是好的,叫他留着送别人吧,我这会儿不用这个。”晴雯笑着说:“不是新的,是半新不旧的。”
黛玉听了,更加纳闷。考虑了一下,忽然恍然大悟说:“放下,你去吧!”晴雯只得放下手帕,抽身回去,一路寻思,不解何意。
这黛玉体会出帕子的意思来,不觉神痴心醉,想到:宝玉能领会我这一番苦意,真令我可喜;这番苦意,不知将来是否能如意,又令我可悲。要不是这个意思,忽然间他挨了打,那么疼,为什么送两块手帕来,竟又令我可笑了。他既对我如此好,我却每每烦恼伤心,反觉可愧……如此左思右想,一时心潮涌动,由不得余意缠绵,便让人点上灯,研墨蘸笔,便在那两块旧帕上写了几首诗:
其一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更向谁?
尺幅鲛绡劳惠赠,为君哪得不伤悲!
其二抛珠滚玉只偷潸,镇日无心镇日闲。
枕上袖边难拂拭,任他点点与斑斑。
其三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糊;窗前亦有千竿竹,不识香痕渍有无?
黛玉本来还要往下写,却觉得浑身火热脸上发烧,走到镜台前一照镜子,只觉腮上通红,真正压倒了桃花颜色,却不知病正是由这里引起的,一时上床睡去,仍拿着那帕子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