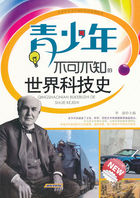爱迪生又有了新的实验场所,这是母亲重新为他开辟的。为了防止意外,新实验室设在顶楼上,地窖里只堆放器材和杂物。爱迪生利用这个新的实验室开始进行电学实验。其中之一就是“电报游戏”。
爱迪生原来就喜欢电报机,尤其和一个叫狄克的朋友一起去参观电信局以后,他对电报的兴趣,就更加浓厚了。
1878年的爱迪生“狄克,我们两个人来做电报机,互相通信吧。”
归途中,两个孩子就这样约定好了。
不论清晨或者是半夜,只要一有空闲,爱迪生和狄克就翻阅有关电信的书,热心地研究机器的制造。
那时,电信事业刚刚开始。所以要找一个隔电瓷和一条电线,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绞尽了脑汁,终于想出用空瓶子来代替绝缘器。不过,最伤脑筋的是电流。
“啊!有办法啦!摩擦猫毛就能产生电流呀,我们来试试看!”
他们捉来了一只猫,开始用力摩擦它的毛。猫由于很不舒服,就在爱迪生手上抓了一下,大叫一声后便跑掉了。
经过这样可笑的失败之后,他们终于从狄克家的屋顶到阿尔瓦家的树尖上,装好了一条电线。
电报机开始发报的时候,他们俩真是兴高采烈,唯一不高兴的是爱迪生的父亲。
“阿尔瓦,不要玩得那么晚,十一点钟就应该睡觉的。”
这样一来,爱迪生太失望了,卖完报纸回到家,总是在22时左右。如果23时就得睡觉,那可就没有多少时间了。很快,爱迪生又想出一个妙计。
有一个晚上,爱迪生空着手回家。
“怎么啦?阿尔瓦,今天的报纸全部卖光了吗?”
父亲在就寝前,总要读爱迪生带回来没卖出去的报纸,这已成为他每天的习惯了。
“不,还剩下几份,可是全都被狄克带走了。”
“那你去跟他要一份回来好了。”
“好,请您等一下,我去叫他看看。”
他走到电报机旁,“喀嗒、喀嗒”地搞了一会,电报机开始响了。
“爸爸,狄克说要把重要的新闻,用电报发送过来。噢!是南北战争的消息,格兰特将军……”
爱迪生的计谋成功了,父亲关切地问:“格兰特将军怎么啦?”
于是,他们俩便借机实验到晚上一两点。
但是,有一个晚上,一只牛跑进果树园里来,牛的犄角勾住了电线。牛着了慌,它越想摆脱掉,电线越是紧紧缠住它不放,它大叫起来。附近的人们闻声赶来,立即把电线割断,这只牛才获得解放。可是,爱迪生最感得意的电报,却因此不能再通信了。
一个名叫华德的铁路工人,住在离爱迪生家只有一公里远的地方,他的继子詹姆士·坎西对电报也特别感兴趣。爱迪生便邀请他一同工作。
在当时没有一家专门出售电报材料的商店,所有材料都得自己做。爱迪生收集了好些拴烟囱管的铜丝,把铜丝拴在他们两家的屋顶上,在树枝上离地七八尺处把电线架设起来,用玻璃当作绝缘器。
爱迪生实验用的所有零部件都是手工制成的。电磁线圈的电线外面包了些破布,用来绝缘,而电键是用一些零星的金属片来充当。取得电源是实验中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爱迪生翻看资料,然后自己动手制造简单的电池。
一切准备就绪,两人开始实验通报。坎西在电线那头接收,爱迪生在电线这头。长短不一的“嗒嗒”声,在夜深人静时分显得格外清脆悦耳。
电报是爱迪生真正搞出来的第一项发明。在爱迪生15岁那年发生了一件事,因而改写了他的人生。
那是8月的一个早晨,爱迪生像往常一样在大干线铁路上卖报,他看到一个小男孩正站在铁轨中间玩抛石子的游戏。突然有一列货车从他身后驶来,爱迪生急忙扔下报纸,冲下站台,抱着那男孩摔倒在路基上。
被爱迪生救起的男孩叫吉米,他父亲名叫麦肯基,是克利门斯山火车站站长。由于感激,他邀请爱迪生住到他的家里。
爱迪生在卖报之余经常到火车站的发报室去研究那里的仪器,这一点麦肯齐也注意到了。因此,麦肯基认为爱迪生也许想学电信技术,将来做一个通讯员。
麦肯基对爱迪生说:“爱迪生,你救了我的小孩,我应该好好报答你。我看你对电信方面的机器很有兴趣,我可以教你掌握电信技术,是免费的。”
于是,爱迪生一面在车站卖报,一面在发报室做见习报务员,不久,便以一个正式报务员的身份加入车站工作人员的行列。
当时,电报还是一个新生事物,没有多少人能够收发电报,最好的报务员每分钟只能收45个字,想干好这行的确很难。所以,能收发电报的人几乎到哪儿都能找到工作。
掌握了电信技术的爱迪生打算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爱迪生要找到一个能运用这种新的电报技术的地方。他找到一个店铺,这个店铺设在休伦港的一条主要街道上。那里有空地,只要付钱就能用。然后,他从自己的电信局到休伦港间架了两公里多的电线,他准备开办自己的电信局。
爱迪生的电信局开张很久,却一直没有多少生意,因为在这个小镇上,早已有了另一家电信局。
托马斯·沃勒是另一家电信局的负责人。沃勒在他的店铺里经营许多项目:珠宝、书籍、钟表。沃勒急于参军,在离职以前,他急需找一个能够顶替他的人。爱迪生聪明伶俐,又是麦肯基的徒弟,当然是最合适的人选了。于是爱迪生顶替沃勒,负责电信局的工作并且经营店铺。
爱迪生接手了沃勒的电信局,这使他不仅能自由自在地工作,而且由于电报房的办公室又是珠宝店的一部分,钟表匠的工具也放在这里,他可以随意使用这些工具,用来制造自己的电讯设备。
1864年冬天,连接休伦港和加拿大城市萨尼亚的大湖冰封雪冻,水底电缆被冰块划断,湖面停止了交通,两座城市的通信处于瘫痪状态。人们都在急切地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爱迪生提议如果能给他一辆车头和一个司机,他便可以和对岸通讯。铁路公司同意了。
爱迪生爬上了靠近湖边的休伦港路段的一段机车,拉响了汽笛,用笛声发送莫尔斯电码。对岸的人被这长长短短的汽笛声吸引了,大家都聚集在岸边倾听。这笛声不久便被加拿大的一个电报员听到,马上跳进那边的火车,也发出汽笛回答。就这样两座城市又恢复了通讯。
用火车汽笛声也可以发送电报传递消息,实在是太新奇了。于是,铁路公司雇爱迪生做斯特拉福特枢纽站的电报员,负责在夜间接收电报,工作的时间是从晚上19时到第二天早上7时。
按照铁路当局规定,值夜班的报务员是绝对禁止当班的时候睡觉的,到9点钟以后,每小时必须发送一次信号,以表明他正在清醒的执行任务,没有偷懒睡觉。
爱迪生白天专研电报原理不肯休息,晚上不免眼睫毛打架,要小小的打上几个盹儿。他也知道,工作时间睡觉是不对的。可是一晚上收报的次数并不多,而且已经摸出规律,时间方面完全可以把握住。那么,在不妨碍正常业务的前提下,利用空隙适当休息一下,也是无关紧要的。只是这一小时发回信号的规定,真像根细麻绳在心上打了个死疙瘩,叫人牵肠挂肚,烦躁不安。
人们说,需要是创造发明的母亲,这话一点不假。为了解掉心上的这个死疙瘩,值班时可以安心休息,他设计了一种小小的装置。这种装置能叫电报机自动按时拍发信号,既准确又可靠。
总局里管电话的莫斯先生,看到爱迪生所发信号准确无误,甚至一秒钟也不差,认为这绝不是一般人能办得到的,心里十分佩服爱迪生,表扬了斯特拉福特分局这位夜班报务员。
年轻时的爱迪生说是斯特拉得福分局夜班报务员,工作勤勉,忠于职守。
爱迪生也暗自高兴:“这倒不错,今后白天钻研电报原理,晚上当班找空子睡觉,也可以更加放心了。”
但是爱迪生“放心”了没多少日子,他那值班打盹儿的秘密,到底还是被表扬他的莫斯拆穿了。
这天夜里,莫斯有事要跟斯特拉得福分局联系,便发出呼唤信号,喊对方回答。可是喊了半天,竟似石沉大海,毫无反应。心里禁不住焦急起来:奇怪!刚刚还准时发出规定信号,怎么一下子变成哑巴了?线路有毛病吧,才检修过的,总还不致于。值勤人员贪睡偷懒吧,该局夜班报务员一贯认真负责,从无苟且失职等情。两种假设都不能成立,其中一定另有缘故。
于是,见多识广的莫斯又想到:连年内战,兵荒马乱,枪杀案件多如牛毛,数都数不清。莫不是斯特拉得福分局碰上强人打劫,夜班报务员英勇抵抗,横遭不测。
想到这里,车务主任不觉打了个寒颤,坐不住了。他吩咐立刻准备手摇车,带着两名助手,风驰电掣般赶到了想象中的肇事地点。
夜深了。满天里雾气腾腾,出去十来步就看不清人影了。斯特拉得福分局里狗不叫,人无声,阴风惨惨,真个是一片劫后凄凉景象。莫斯叫两个助手在外守护,自己一步步摸进报务室里。昏暗的灯光下,只见爱迪生直挺挺的躺在椅子上,看样子早已一命呜呼,断气多时了。
看到此情此景,车务主任不觉倒抽一口冷气。他两眼发直,楞住身子一动不动,呆了老半天,才象大梦初醒,哆嗦着腿走过去,探个究竟。
首先,他发现爱迪生面目如生,看不出一丝丝惨死暴亡的迹象。再哈下腰把耳朵凑到对方鼻子上,又觉得热风拂面,明摆着还在喘气儿;只听见呼声作响,分明是均匀的鼾声。
“他妈的,活见鬼!原来是在睡觉!”
莫斯嘴里狠狠地骂着,心上象架起了一堆火,直冲天灵盖。刚要伸拳往对方身上打去,眼光突然落到了那个小小的装置上。心想此物摆得蹊跷,灵机一动,又把手缩了回来,咕嚷着说:
“让我看看这小子到底在搞什么鬼把戏。”
他跟着脚走上去,仔细观看。那小装置结构并不复杂,是在发报机和一只闹钟之间。安了个缺口轮,缺口轮上搁着根小棒子。闹钟走动时,缺口轮也跟着慢慢打转。他边看边寻思:“没有错,一定是个警报器。到时候这么一响,这小子就起来拍发规定讯号,完了再安心睡大觉。”他决定耐心等下去,亲身实地观察,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这时,他心上那堆无名之火,已经被好奇的泉水泼熄灭了。他找了个阴暗的角落,再搬把椅子作掩护,蹲在那里以侦察的眼光,窥探周围的一切。
眼看规定发信号的时间渐渐临近,莫斯嘴角上泛起一丝笑意。他仿佛置身在戏院的包厢里,只要铃响幕启,便可大饱眼福,欣赏一出名角儿的拿手好戏了。
正想到得意处,那只台钟扯开铜嗓子,“当当”的报起时来。车务主任心上一机灵,不知不觉收起脸上的笑意,鼓着眼珠静等事情的发展变化。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并没有听到任何报警的声响,爱迪生还是若无其事得睡得又香又甜。正疑惑的时候,随着闹钟的最后一次敲打,只听得“咔嚓”一响,缺口轮上的那根小棒子从缺口里落下来,扣在电报机的电键上。准确无误地把规定的信号拍发了出去。
车务主任看罢,又呆了老半天,才将吐出的舌头缩回去。
“难以想象!”
他啧啧赞叹着,打屋角里走出来,重新把那个小装置细看了一下。这下他才发现,缺口轮的转动,跟闹钟分钟的步调是一致的。分针从“12”走到“12”是一圈;缺口轮也从缺口转到缺口,也是一圈。时间不多不少,刚好一个钟头。
原想识破机关,当场要人家好看的,结果弄巧成拙,反过来倒叫人家耍了猴把戏。莫斯越想越不是滋味。羞惭、恼恨绞在一块儿,由不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他气势汹汹走上去,当胸一把拉着衣领将爱迪生拖了起来,狠狠地骂了一顿。就这样,爱迪生被从斯特拉福特枢纽站赶了出来。
此时,南北战争硝烟冲天,正厮拼在火头上,而信息对于战争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于是大批报务员被吸收到了军队里,地方上通讯人员奇缺。因此,掌握最新式通讯工具的报务员,便成了左右逢源,到处吃香的人物。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面。
另一方面,在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社会里,重的是情面靠山,专讲究拍马吹牛。只要他的来头大,会阿谀奉承,即使不学无术,彻头彻尾的废物,也能捧上金饭碗。相反,就算你本事很大,能力很强,也会到处碰壁,弄得英雄无用武之地,找不到工作。
对爱迪生来说,头一个条件是有利的。所以从斯特拉福特枢纽站一出来,立即又在阿德里安找到了新的工作。可是拿第二个条件来衡量时,爱迪生就不合格了。因此他在新岗位上呆了没多久,就被人家扣了顶“冒犯上司”的帽子,一脚踢出门来。接着,他又到威因炮台当上了报务员,但也不过三个月工夫,还是得卷铺盖滚蛋。原因很简单:据说是所在单位的主任有个朋友,看中了爱迪生占据的那个职位。
现在,威因炮台也待不下去了,可爱迪生并没有难过,更没有气馁。他想起了爸爸塞缪尔常说的那句话:“没关系,‘手眼为活’,走遍天下,也是指着两只手来打拼的。”于是又迈开脚步,走上新的征途,来到了举目无亲的印第安纳波利斯。
冬天的早晨,气候格外寒冷,大街上,屋顶上,树梢上,都披着一层厚厚的霜雪。爱迪生头戴破呢帽,身穿斜纹布裤褂,拖一双后跟倒塌的大皮鞋,在大街上转悠着寻找工作,打听有哪里需要报务员。
接连问了好几家电报局,都说没有空位置。后来在联邦西部电报公司找到一个报务员的工作。
当时的美国,电报才发明不久,正处于草创阶段,很多地方还很不完善,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报务员对于市场来说却一直是供不应求,一般懂得电报方面技术的报务员只要得到了这份工作就很心满意足了,不肯再在上面多费心血。
可是爱迪生却不这么认为。他是从《派克科学读本》上得到启发,把它当作一门科学知识,一种科学实验开始学习的。此后,拜麦肯基为师,买书探索原理,也抱着同样态度。在他的心目中,从事这项工作,钱并不重要。问题在于如何往深处专研下去,步步提高,精益求精,能够在这方面作出点有益的贡献。
如今,他在电报方面的造诣,可说是已经相当深远了。
不但操作熟练,业务水平很高,而且通晓科学原理,从深处理解和掌握了这项工作。也正因为如此,他来到联邦西部电报公司以后,便对电报机的结构、性能,开始不满起来。他首先感到:电讯越来越繁忙,需求在逐日增长,而一条线上每次只能发回一个电报,未免太死太慢了。如果能同时发送两个,那效率岂不是能一下子翻一翻,提高一倍。还有纸条记录设备,也可以改进一下,如果能提高纸条的记录速度,抄报质量就能大大提高。
有一天,他找到跟他一起值班的那个同事,把改进记录设备的想法说了说。同事一听,抽着烟想了会儿,疑惑地说:
“好是好,不过一定得有把握才行。不然,耽误了收报,这个责任我们是担当不起的。”
爱迪生没跟他多费口舌,伸手拉着他走到宿舍里。搬出一套收报装置,将自己几天来的实验结果,干净利落地当场表演了一番。
表演完了,他又把机器拆开,把改进了的地方,依据的原理一一给同事说明清楚:托马斯·爱迪生与他早期发明的留声机。
我把它叫作二重记报机,上下安着两套记录设备。上面这套跟原先一样,完全根据对方拍发的快慢将电讯记录下来,对方拍得快,它记得也快,对方拍得慢,它记得也慢。速度掌握在发报人手里,收报者无法控制,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可是下面加装的这部记录机,情况就不同了。报务员通过它进行抄报的时候,速度快慢,可以随心所欲,任意调节,所以抄下来的电文质量比过去有显著的提高。
那个同事看了实地操作,听了详细讲解,一脸的兴奋与惊奇,先前笼罩在心上的那团疑云,象是骤然遇到一阵疾风,早刮得烟消雾散,无影无踪了。
看到同事这股高兴劲儿,爱迪生满心欢喜的说:
“行,我们今天晚上就用它试试看。”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们决定偷偷进行试验。上班的时候把新设备装上去,下班再拆下来恢复原状,以求不留一点蛛丝马迹。
不久,公司经理逐渐发现,凡是爱迪生当班抄得的报文,不但从无差错,而且清清楚楚,整齐美观,心里也很是欣赏这个年轻人。他拣了几份特别好的,让人贴到大厅里去,公开展览,让大家见识见识,学习学习,同时也是对爱迪生的一种鼓励。
“展览品”一贴出去,使招引来很多观众。有的是爱迪生同行,有的是普通职员。这些人着眼点虽然各有不同,可是观后感却差不多,一个个都异口同声地喝采叫好,佩服得五体投地。其中有个报务员看了以后,禁不住握紧拳头直敲自己脑袋,说:
“怎么回事!他当夜班,我值白班,用的是同一架机器,可抄出来的报文,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简直没法比!”可是他哪里知道,夜班报务员怀里有件法宝,是跟着他一起上下班的。
试验二重记报机获得成功,爱迪生又集中精力,开始着手研究二重发报机,打算实现他一条线上同时拍发两个电报的愿望。不料就在这时候,偏偏节外生枝,又生起变故来。
这天夜里,气候特别冷。即使坐在屋里向着火,手指头还是不大肯听使唤,有点僵硬。电线上的电流,也象耐不住这分严寒,拼命伸胳臂抬腿,展开了急剧的活动。收报机忙碌不停,大批新闻电稿以最高的速度倾发过来。爱迪生和那个同事把全身的本领都用上了还是应接不暇,对付不过来。当对方发完“晚安”两字宣告终结时,他们这边才只抄收了一半的电报,在时间上几乎慢了两个小时。
新闻电稿是报纸的重要资料来源,你这儿一慢,那边报馆里的编辑人员,也跟着发起慌来。第二天的报纸在等着新闻电稿发排哪!于是,从报馆通到联邦西部电报公司路的上,派来催促电稿的人,象走马灯儿,一个跟一个,接连不断。开头还只是催促一下,后来话音里含着埋怨,到最后,口气越来越难听,终于竖眉瞪眼,扯开嗓子骂起街来了。
这样一来就惊动了公司经理。查问下来,根由出在夜班报务员身上,经理一生气,来到了报务室,爱迪生恰好抄完电稿,正想动手把那个小设备往下拆。
经理喊了声“慢着!”大踏步赶上去,虎着脸,拧着眉,朝那个小设备瞪了一眼:
“这是什么?”
那个同事见经理亲自出马追问,晓得事情严重,生怕野火烧到自己身上,便说是爱迪生搞的二重记报机。
经理不容分说,当即武断地作出结论,对爱迪生说:“我知道你是一个优秀的报务员,可是你私自拆毁公司设备,造成严重事故,损害了公司信誉。公司不能再继续雇用你了,你可以走了。”
爱迪生默默地回到宿舍里,把东西收拾了一下离开了这个地方。他像一片在水面上到处漂游的浮萍,不声不响漂到这里,停了停,又不声不响漂往别处去了。而在这段短暂的停留时间里,也还是不声不响地埋头专研,只不过在停留过的水面上,微微引起一丝涟漪,在联邦西部电报公司印第安纳波利斯分公司职员名册上,留下了这么几行简单的记载:
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二级报务员。1864年12月到职,1865年1月离职。月薪75元。
爱迪生离开了联邦西部电报公司,城市里,到处都很热闹,人们穿梭般来来往往。可他心里却冷清清的,好比一叶孤舟漂行在茫茫大海上,望不见陆地,辨不清方向。
母亲南希住在休伦港,靠着塞谬尔做点生意生活,孩子们不时会寄回些钱来,因此生活得倒也还算充裕,日子过得相当美满。她看见大闺女大儿子,出嫁的出嫁了,成家的成家了,心想一辈子担惊受怕不容易,现在总算熬出了头,不必再为他们操心呕血了。
只是对于小儿子爱迪生,还没有成年,却走南闯北,游荡不定,南希现在最担心的也就是小儿子爱迪生了。如果隔了一段时间接不到爱迪生的信,她就坐不稳,站不定,连觉也会睡得不舒服。直到爱迪生寄信回来,说自己身体很健康,诸事平安,南希的心才像绷紧了的弹簧,一样松弛下来。
每当这个时候,塞谬尔总是在屋里抽着烟,看着妻子走出走进,他知道她是在担心爱迪生的情况,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呢。因为事情摆得明白,孩子这么长时间不往家写信,十之八九不是好兆头。而这些塞谬尔自己也是经历过来的,饱经风霜,倍感辛苦,走过弯弯曲曲的路,知道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总是伴随着很多的无奈。
但是转念一想,这也没什么。年轻人总是要多受一点挫折,多经历一些风浪的,也能借此磨练磨练,长长见识,学点本事。再说,这些年来,察言观行,他总觉得爱迪生这个小儿子与其他孩子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因为爱迪生从小就不看重那些虚无奢华的东西,踏实深沉,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干成。
因此虽然爱迪生经常出门在外,南希和塞谬尔对他还是很放心的。所以,等到爱迪生再一次寄信回来时,他总会很满足似的望着南希,好像是在说:“怎么样,我想的不错吧?爱迪生根本用不着为他担心。你看,这不是一切都挺好吗!”
寒来暑往,日子过得很快。到了1867年秋天,南希想想爱迪生又好久没有来信了,心里不禁又笼上了一丝忧愁。她想:
这次可是跟以前不一样了,爱迪生出了远门,想要到南美洲去,可是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去。如果还没有去成,应该是会写信回来的。要是去成了,那真叫千里迢迢,关山重重,眼睛看的是异国风光,耳朵听的是外邦口音,生活习惯截然不同。万一有个什么事,有谁能来照应呢?没有找到工作,现在又在靠什么生活呢?此时她又想起了当时爱迪生突然回家的情景:
当年春天,爱迪生还在孟斐斯工作的时候,因为试验二重发报法,跟经理的一个亲戚闹了冲突。原来那家伙也在想一根线上能够同时拍发两个电报的方法。他看见爱迪生比他高明,研究工作明显已经走在了他的前面,便心生忌妒,怂恿经理借故把对手开除了。但是爱迪生紧接着又在路易斯维尔找到了工作。并且还来信说:
眼下除了研究二重发报法的同时,还在拼命的学习西班牙文,希望不久的将来,在读写方面能够跟西班牙人媲美。接到这封信,南希和塞谬尔看了一遍又一遍,都为孩子的孜孜上进,感到难以形容的欣慰。
可是没过多长时间,爱迪生突然出人意料地回来了。上一次爱迪生回家还是三年前的事了,看到站在眼前的爱迪生,南希和塞谬尔真的是有点喜出望外了。
面包和牛奶在桌上冒起腾腾热气,满屋都是诱人的香味儿。爱迪生回家来,南希特别备置了美味的饭食:煎制牛排,红烧土豆搭配鸡块,油煎荷包蛋撒上火腿丝。又端来一大盆鲜美可口的浓汤,说:
“这些都是你最爱吃的,今天我可要看着你把它吃完了!”
说完,坐在对面笑嘻嘻地看着爱迪生吃。
发明灯泡时候的爱迪生爱迪生回来了,长成了一个强壮的小伙子,不光是南希高兴,塞谬尔也也是很高兴的。他跟在南希后面地忙了一阵子,直到动定思静,才猛然想起:“阿尔瓦出外三年了,从没提过回家的话,而这次怎么都没提前打个招呼就回来了?会不会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发生了。”
他正想要问一下的时候,爱迪生似乎猜到了他的心意。一边吃,一边笑着问南希:
“妈妈,你知道我这次回来是干什么的吗?”
南希把菜盘往孩子面前推了推,说:
“我正要问你呢,你怎么没提前打声招呼就回来了。”
爱迪生瞪起大眼睛,望着南希和塞谬尔说:
“我回来是想跟你们说,我想到南美洲去。”
“上哪去?”
南希和爱迪生面对面坐着,明明听得十分清楚,可还是不敢相信,侧起耳朵再问一句。
“我想到南美洲去。”
爱迪生重复着说,语气非常坚决。
“我知道那里的物产很丰富,市面繁荣,情形很好。我已经跟两个朋友约定,明天回路易斯维集合,马上就动身。这次是特地抽空回家来跟你们说一声的。”
南希一听,像椅子上一下子长满了刺,一下子跳了起来。连声说:
“不行,不行!你不能去,说什么也不能去!”
爱迪生笑了笑,安慰南希道:
“妈妈,我都已经出去逛了三年了,现在不是也好好的回来了吗?南美那边的情况比这里要好一些,如果去那边发展我一定会发展得顺利一些。”
可是南希觉得南美太远了,于是一个说不行,一个说挺好,各有各的道理。塞谬尔听他们一搭一理儿说着,心里也犯了思量。他想:怪不得上次来信说,在拼命学西班牙文,还要跟西班牙人媲美,原来是早就准备要到正好说西班牙语的南美去了。
现在看这副架势,应该是已经下定了决心要去,再想叫他打消这个念头,就算磨破嘴皮子估计也是没用了。
既然这样,已经没有阻拦他到那里去的必要了,但是要提醒他:人言不可尽信,一路上最好多多留意,再打听打听。如果南美真的有那么好,就去;要是并没有那么理想,再回来也不迟。
拿定主意后,塞谬尔就把自己的想法和爱迪生说了。爱迪生当然满口应承,南希起初还是不同意,后来架不住孩子苦苦央求,丈夫又从旁帮腔呼应,只好勉强点头同意了。
第二天,爱迪生就动身走了,一走就是几个月,直到现在也没个音讯。是到了南美洲,还是没到南美洲,是吉还是凶,全不知道。就在他们还时刻在为爱迪生的情况担忧的时候,原本一点音讯也没有的爱迪生,又跟上次一样突然回来了。
原来,爱迪生和两个朋友一起,从路易斯维尔出发,赶到新奥尔良,准备在那里搭船去巴西。不料一到新奥尔良正碰上出了事儿,当地政府颁布戒严令,轮船火车一概不准开动。没办法,三个人只好暂时住下来等着。后来两个朋友按原计划搭船去巴西,爱迪生则循原路回到了路易斯维尔。
他在路易斯维尔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到辛辛那提作了短期的逗留。这时他才听说,那两个固执的朋友,好不容易到了墨西哥,却染上了流行性黄热病,就这样永远留在那里了。婉惜之余,他又想起了家,想起了亲爱的妈妈,于是又回到了休伦港的家中。
可是,他这次回来,日子也并不好过。因为虽然南北战争结束了,可还是乱得厉害。爱迪生回家还没几天,地方当局就借口军用,强迫爱迪生一家搬走。可是事出突然,现在到哪里去找合适的房子?一家人只好在一个朋友那儿暂时挤一挤。
在异乡客地东奔西走,飘流了三年多,回到家还是没有一个安稳的落脚处。眼看两位老人日夜焦虑,一天天瘦下来,爱迪生感觉很不是滋味。
他写信给在波士顿的米尔顿·亚当斯,托他代谋一个职业。亚当斯便把他的信交给了西方联合电报公司的监察米利肯。
米利肯见了这印刷体般的书法,赞赏地说:“他抄电报时也能写得这样整齐吗?如果他能够的话,那么叫他来,我马上雇佣他!”
爱迪生接到亚当斯的信,决定去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