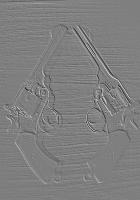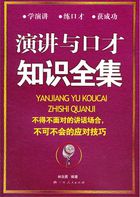6月8日,耆英到达天津。他求见各国公使,却遭到了来自英、法方面的拒绝。原来,英国公使得知,耆英这次到津,是为通过支持桂良、花沙纳所持的强硬态度来改变他自己的形象,从而担心耆英的介入会给他们的逼降带来麻烦。英国译员李泰国和法国译员威妥玛在两国公使的授意下,当面羞辱了耆英。年逾七旬的耆英抵津后,尽管已老眼昏花,但还是察觉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四国侵略者面目虽然各异,但贪婪卑鄙如出一辙,尤其是英人不仅桀骜不驯的张狂态度比以往更甚,而且他们的武器装备也比16年前有了明显的更新。咸丰拟定的妥协办法与侵略者的蛮横要求差之千里,战争简直是一触即发。尤其让耆英狼狈不堪的是,同英、法代表会谈时译员李泰国等人不断逼迫清朝三位钦差大臣,用书面形式完全同意英国提出的条款,咆哮要挟,无礼至极。另外,竟然拿出一份在叶名琛衙门里获取的耆英写给清廷的奏折,其中大谈自己的驭夷之术和同夷人虚与委蛇的情况。两个西方的小人物,以此物当面斥骂三朝元老的钦差大臣,使耆英无地自容。他只得惶恐离去,并且不等咸丰允准就擅自回京。
这样,耆英最后的一次政治活动,不但没有完成咸丰的重托,反而受敌侮辱,并与桂良等人联名同意咸丰最不愿意接受的公使驻京等条件。为此,咸丰大为震怒,命令把耆英下狱问罪。同时,一面严谕桂良等人拒绝英法要求,特别是公使驻京一事;一面先行与俄、美两国签定《天津条约》,依然幻想以此让步来换取他们的感恩图报,劝说英、法两国放弃公使驻京等要求。但这种与虎谋皮的做法,只能是使咸丰再一次受到欺骗而已。
仍在天津谈判的桂良、花沙纳接到咸丰旨意后,依靠卞宝书等人穿梭于海光寺、风神庙。而同清方交涉的列强代表主要是一批年轻的“中国通”,最主要的人物就是李泰国。
李泰国是英国人,小时候就随父亲来中国学习汉语,曾经在英国驻上海领事馆供职。1855年,他被聘任为上海江海关税务司之一,年薪达到12000元,十分讨清朝钦差吉尔杭阿等人的赏识。
天津谈判时的李泰国,年方26岁,年轻气盛。由于精通京津地区的语言,狡诈诡谲,被聘为英国公使的翻译官,实际上成了操纵英国与中国交涉的主谋和代言人。
李泰国在与谭廷襄、崇纶、桂良、花沙纳、耆英等清廷官员的谈判中,出语狂悖,十分无礼。连在场的外国人回忆当时的情景也这样指出,桂良、花沙纳两位钦差在李泰国等人走进时,“就陷入一种极端委屈的状态中,桂良已经完全沮丧,而花沙纳显然从烈酒中寻找到了安慰”。李泰国在清政府钦差面前放肆争执,毫无畏惮,强词夺理,使得清朝官员十分被动。
如何对付李泰国呢?让清政府大伤脑筋。户部侍郎宋晋提出,李泰国这人贪图利益又狡猾多谋,如果派能言善辩的人暗中用利益来作诱饵,离间他对其主子的忠心,使之不再从中作梗,谈判就应当容易驾驭了。这似乎也算是一个办法,但对付李泰国未必行得通。因为他可是个具有更大野心的人物,岂能那么容易被小恩小惠所拉拢?年轻的恭亲王奕,身为皇弟,血气方刚,初涉外交,更是火气十足。他的外交知识非常有限,错把李泰国当成了广东的市井无赖,认为这种不知法度、形同叛逆的行为,足以将他正法。因此,奕上奏咸丰皇帝,要求下令桂良:等他无礼取闹时,立即拿下,或当地正法,或押解到京治罪,这样就可以除去英人的心腹主谋,谈判便容易着手了。这么可笑又不合国际惯例的意见,桂良以“恐立起兵祸”为由而没有执行。
在无奈中,经过李泰国、威妥玛等人恫吓威逼之后,6月14日,桂良、花沙纳对英方提出的大部分条件都答应了。只有洋人进京一事,相约缓期办理。咸丰对此颇为不满,惟恐这种推脱之辞以后若不能实现,导致失信于夷,又带来无穷后患。要求桂良等人,选那些可以答应的答应,不可以答应的就拒绝,并斥责道:“若必事事皆准,何用大臣会议耶?”皇帝认为,要是那样的话,有什么必要派你们去议和谈判呢?
桂良等人一面受到朝廷责难,一面又被洋人步步紧逼。两难之中,桂良还是不敢得罪洋人,随即上奏咸丰,以“与英交涉不可决裂”吓唬清廷,迫使咸丰帝再作出让步。
英方再次向桂良等人提出进京换约和公使驻京问题。理由是中国地方督抚过分蒙蔽朝廷,必须派公使驻京,以便迅速知道照会内容进行交涉。桂良在转奏朝廷时提出倾向性意见:即有数十洋人在京,尚易防范,断不可因此中断交涉。
“公使驻京”,无疑是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它对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让洋人住在皇帝的身边这还得了?果然,桂良关于公使驻京的奏报到京后,立即遭到群臣的强烈指责。都说这是“千古未有之奇闻”,洋人一旦驻京,就会窃取中央政府的动静,蛊诱首都百姓的人心;只有外夷臣服中国,入修朝贡之事,哪可让他住进京城,与皇帝平起平坐?“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甚至要求撤回桂良、花沙纳,另外派员“查办”。
朝臣的议论,掩饰不了他们思想观念上的封闭、迂腐。公使驻京是否有损国家主权,归根到底决定于国家实力的强弱。自修古训,沉湎于祖宗昔日辉煌的臣子们大概忽略了,大唐盛世之时,长安也曾处处有外夷商客;元世祖忽必烈也有诸名外籍总督,同样是黄发蓝眼的马可·波罗甚至也贵为钦差。如今的大清国呢?积贫积弱,任由外人宰割,又凭什么来拒绝夷人的入京“妄念”。国家安危并不在于是否有几个外国公使驻在京城。
在朝臣的激烈抨击下,清政府指示桂良,仍以公使驻京碍难应允加以拒绝。只同意“有事进京”,并且“须改中国衣冠,听中国约束”。桂良等人将谕旨转达给英、法方面,结果可想而知。无论他怎样绞尽脑汁、口焦舌燥地进行解释,英、法方面始终不为桂良的说辞所动。
6月22日,英、法方面再次恃强要求公使进京。清政府在第二天的军机大臣会议上激烈争论,是战是抚,仍举棋不定,致使谈判毫无进展,陷入僵局。
在清廷举棋不定之时,英、法方面向桂良发出照会,威胁道:再不下定论,就要举兵北上。英方又在6月25日向桂良等递交了自定条约,即“中英天津条约”草案共56款,并且声称,没有可以商量的余地,一个字也不能更改,其中内容当然包括公使驻京。
清政府得到奏报后,才立即做出反应,一面说大局仍是应当以抚为主,如能挽回,就尽量少答应一些要求;一面说,如果挽回不了,就听任其决裂,命大沽逃将谭廷襄抵御英、法联军,保护桂良、花沙纳抽身虎口,又命僧格林沁在通州集结马步,备军备战。看来,为了维护体面,咸丰痛下了决心。
不想,桂良却不等朝廷圣旨到津,就再也抵挡不住英方代表咄咄逼人的攻势,在李泰国等人的逼迫之下,已经应允了英国方面提出的全部条件。
6月26日,英国公使额尔金率从官20余人,分乘20顶大轿,带兵560人,吹鼓乐队50人,威风凛凛,鼓乐齐鸣,趾高气扬地来到海光寿。相比之下,桂良、花沙纳所率领的随员和地方官10余人,实在是毫无光彩。双方在中英《天津条约》上依次签字画押,继而不外是再大摆宴席,豪饮一番。第二天,法国公使葛罗也同样与桂良、花沙纳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
这两个不平等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一、公使驻北京,用平等礼节;二、开放牛庄、登州、台湾、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海关雇佣外人;三、耶稣教、天主教可入内地自由传教;四、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五、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六、外国兵船、商船可在各通商口岸停泊;七、对英赔款400万两,对法赔款200万两,交清后退还广州。
一副更加沉重的枷锁,又套在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大清国身上。
咸丰变卦和第二次大沽战事
《天津条约》的签定,使大清“天朝上国”的尊严又一次受到了嘲弄。这种嘲弄,就像背上的芒刺,搅得咸丰一刻也不得安宁。
连洋人也觉察到了咸丰的极端不快。“在惊慌失措之际,这个皇帝可能什么都答应。但是,当压力消散,舰队离开的时候,他的‘法老之心’一定又会故态复萌。那种中国人的狡诈一定会肆无忌惮地用在回避条约的义务方面。”
这种认识除去对中国人的轻蔑与诽谤的口吻,基本上还是准确的。血气方刚的皇帝对“手枪抵在咽喉上”的城下之盟,不但没有屈服,而且立刻准备推翻成议,伺机报复。
《天津条约》签订的第二天,咸丰就怒不可遏。他召来团练首领罗淳衍,命令其立即激励团练,鼓舞公愤,大胆出战,实力攻剿,“不必因城中尚有官吏,致存投鼠忌器之心”。当然,他也小心谨慎地叮嘱罗淳衍,虽然是奉旨办理团练,但是剿杀夷人时,仍然要以民心义愤为口号,不要泄露是带兵勇打仗,以免被洋人抓住把柄。此后,咸丰又多次密谕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暗中统帅各乡,联络激励,以挫外夷之势,而振中国之威。
咸丰这种“不必官与为仇,只令民与为敌”的作法,既有顺民心,恃民力,以垂万世之基的民本思想,也有官府力量不足,不得已借助民力的苦衷。他是幻想用“明和暗剿”的方式来惩罚侵略者,以排泄他心头的怨恨。咸丰甚至一厢情愿地以为,只要用这种“官与绅民貌离神合”的斗争策略,激励沿海绅民,轰轰烈烈地声讨夷人背约攻城的罪恶,自己则躲在幕后,就能将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使令他蒙羞不已的《天津条约》成为一纸空文。
此外,他还想启用自己的八旗王牌。列强兵船刚一起锚,咸丰便急命爱将僧格林沁火速进京,面授机宜,来布置海口设防。同时,他召回了桂良等人,对其指示了挽回条约的“内定办法”。
根据《天津条约》,中外双方约定在上海举行改订税则和通商章程的会议。咸丰决意把这次商定税则,作为中外关系的一大转折,所以在桂良、花沙纳等人离京前详细制定了“一劳永逸”的计策。这个让咸丰自以为得计的内定办法,就是用外国来华贸易全部免税来换取《天津条约》中的外国使节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和赔缴军费后退还广东省城的四项条件。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公使驻京问题。糊涂的咸丰帝以为,洋人来华的目的就是要通商获利,只要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他们的欲望,洋人一定会感动驯服,所以他们想用全部免除关税的条件来换取以上四款。
然而,列强侵华却远远不止要通商获利,更要把持中国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命脉,使她永远沦为任由宰割侵蚀的殖民地。咸丰皇帝的计策实在不过是一厢情愿。
在侵略者看来,清政府一心要挽回的四款要求,也正是他们所要攫取的主要目标。美国公使巴驾一语道破天机,“从遥远的地方无法驾驭中国的政府,只有到了它的身边,它就会变得驯服多了”。列强坚持“公使驻京”的目的,就是要直接控制清政府,以便于随时夺取更多的侵华权益。而英国则还有扩大在华影响,抵制沙俄势力南下的小算盘。所以,英国公使额尔金也毫不松口,声称如果没有公使驻京一项,《天津条约》是一文不值的。
为了防止清政府毁约变卦,英国人李泰国在天津谈判时便指名要江苏巡抚赵德辙和苏松太道薛焕为上海会议的代表,以便摆脱执行咸丰旨意的桂良等人,进一步扩大侵略成果。到上海后,英国人得知赵、薛二人没有谈判的权力,大为光火,便以再次举兵北上来要挟清政府授予他们谈判的全权,同时,蛮横地要求清政府立即撤销在广东坚持“攘夷”的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的职务,否则,拒绝出席上海税则谈判。
这种以武力为后盾、明目张胆地指定谈判对手、迫使清政府放弃“明和暗剿”的做法,使咸丰十分恼怒。但更让咸丰愤恨不已的是,桂良一行到达上海后,还没有同李泰国等人会晤,就自作主张地放弃了自己冥思苦想出来的“一劳永逸”之计。谈判大臣之一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向咸丰帝解释称:夷商与夷酋是两回事,如果全免了夷人的关税,夷商当然很乐意,但夷酋并不会领情;带兵来侵犯我国,攻陷我们的城池,都是夷酋所为,与夷商无关,应另外筹划别的办法。这种把“夷商”从“夷酋”中割裂出来的看法并不准确,但何桂清对夷人的认识却比皇上要稍深刻些。接着桂良、花沙纳等又联名奏报咸丰:即使把课税全部免掉,也不过是夷商感激皇恩,想要夷人放弃全部条约,势必不可能。然而,对商务税则懵懂无知的咸丰帝依然固执己见,严谕桂良等人,仍然遵照内定办法行事,力图补救,非得把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设防及赔缴兵费退还广东省城,四项条款废除才肯罢休。
咸丰为什么宁可全免关税也要取消这四项条款呢?归根结底,还是要维护他心目中清王朝的长治久安。以往只有进宫朝驾的宗藩使臣才允许进入京师,叩见天子。而如今一旦允准这些“化外群藩”长驻京城,与真龙天子平起平坐,实在是对统治中心北京的玷污,为大清国国体所不能接受。而且,会严重地损害皇帝的尊严和威信,影响清政府对人民的统治。所谓“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禁止令行,四夷来王”的封建统治,是咸丰帝和他的大臣们极力想恢复的“世界秩序”,而如果允许洋人驻京,那么祖宗的一统天下将立刻解体,微小的肘腋之变会随时祸及天朝。一再饱受列强利炮坚船惊吓的清朝统治者们,还是不敢也不愿睁开向海外世界探索的眼睛,还是无法对自身及洋人的力量对比弄个清楚明白,实在可悲,而朝廷惶恐担忧的情绪也波及民众。当时的“市井闲谈,士大夫清议,无不以夷人驻京,为宗社安危所系,而惴惴不安”。另外,咸丰还害怕外国人与内地的反清势力,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联合起来推翻他的统治,所以对长江通商和内地游历、传教等项也是讳莫如深。
但是,洋人又岂肯放弃到手的肥肉。他们强硬地坚持,“条约以外之事均可以商量,条约既定之说,万不能动”。结果,在英、法两国,也是在何桂清、薛焕等人的导演下,上海税则会议形式上只开了3天。就在成丰八年(1858年)十一月八日(9月14日)和二十四日(9月30日),桂良等人代表清政府分别与英、法、美三国签订了《通商税则善后条约:海关税则》。
咸丰见桂良等人不仅没有挽回上述四项条款,反而增添了许多新的不平等款项,气愤至极,便在奏折上朱批道:
“览此折不觉愤闷,尤堪痛恨!汝辈此行,不但不能清弭,反而不如原约。”
这样还不够解气,他又大骂何桂清:
“此次办理夷务,独存成见,不准他人入手,殊属胆大,是以视朕旨如弁髦,罪有浮于耆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