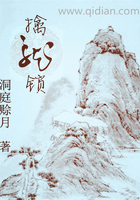昨天,我去参加了一个武林大会,以及其毒辣的手法杀死了武当耆宿抹茶道长,对此我感到十分的悲哀,我辜负了唐家对我的栽培和师长的期望,我保证不会再有下次了,如若再犯,就把我打入小黑屋,永世不得翻身。好了,检讨就写到这里吧,出于我成长经历所形成的一些惯性,我做错事总喜欢写一封检讨,并且出来不辩白什么,因为辩白只会招来我爹一顿毒打,但这次事情真的闹大了,村子口撑死那位,也就是打扮的跟工地上的那位,竟然实实在在就是武当掌门抹茶!他会出现在这么一个小地方是因为一个更悲哀的原因——武当被灭门了!实在太让人震惊了,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朝廷干的,江湖门派之中,即便少林也没这个实力。而我在那么一个时间那么一个地点那么巧合的被干掉了抹茶,又使大家一致认为唐门和朝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说不清了,反正不是什么好事,在江湖上跟别人说我朝廷里有人是会被孤立的,因为江湖,就是一个黑社会。
我爹作为黑社会里的一门大佬自然不是白给的,很快就发布了公开声明——“近期有不明人士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假冒我唐门子弟,杀害了抹茶道长,败我名誉,祸害武林,人人得而诛之!鄙人谨以唐门门主之名,下唐门追杀令!唐门弟子,必杀此人而后快!”撇的一干二净,因为提到了“唐门追杀令”,这么多年了,这张追杀令上的名字没有活过一个月的,但我可能会打破这个魔咒,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时间,我就马不停蹄的往家跑,我在外面就是那个不明人士,回到家就成了唐门四少爷,那个追杀令对我来说自然就不起作用了。给了外面一个交代又把我逼回了家,我不得不佩服我老子的办事能力和我的理解能力,果然是很有默契。
默契归默契,我却从来不愿意配合,已经到了大巴山,我又拨转马头往回走,不是改了决定,而是在犹豫。如果我回去了,除了肯定会被禁足,相当于什么事也没发生,但是我见识到了,武林接下来一定会发生什么大事,三哥说:“一直以来,我都在等待大事发生”。现在我有一个机会,并且这事还和我有关系(如果能解释清楚那就一点关系没有了)。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去一趟武当,搞不好这只是一起谣言,要是真的,那里现在就是一座荒山,我却仍要往那里去,只因我曾对彼向往,我喜欢这个不是理由的理由,它让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做一个随性快乐的****。于是马蹄沿原路返回,路过海坪餐馆,铁脚帮正在利用武林大会的噱头大肆招生,我悄悄的走过,竟没人认出。
这一路没再逗留,我快马加鞭,三天两夜到了武当。武当的确是受了攻击却没有灭门,物证是修补过的建筑和真武大帝像,人证此刻正站在我面前,“鄙人代理掌教花自羞,阁下是?”我说:“在下唐门唐漱,近日江湖传言武当罹难,又有人说是唐门下的毒手,家父特命我到此澄清误会。”。我对花自羞的第一印象非常好,因为他长得很委婉,不是那种男生女相的阴柔,更似女扮男装的娇俏,武当真是个风气自由的地方啊。花自羞说:“没人能证明你就是唐漱,也没人能证明不是唐漱杀了我们掌门。”对于这种悖论式的提问我完全可以用“没人能证明我不是唐漱,也没人能证明是唐漱杀了你们掌门。”来作答,但这显然毫无意义。我说:“如果我不是唐漱,以唐门的做事风格,我出了这个山门很可能就死于非命,我何必冒这个险?”,但我是实实在在的唐漱,这就是我现在还敢在外面晃的原因,一切的黑锅,都有那个不存在的冒充我的不明人士来背,真是辛苦你了。花自羞无话可说,既不赶我走,也不请我坐下,我只好深情的凝望着他以表达我对他的尊重,长达两分十三秒。
我决定打破这份尴尬,两个人对望着气氛有些暧昧,我脑海里已经出现他头发披散下来的画面。我说:“人道武当已满门被灭,看来事实并非如此。”花自羞伤感的说:“只怕事实也并非如此,我们不过是外出公干才逃过一劫。”我说:“大家都说是朝廷下的毒手。”花自羞说:“目前只有这一个合理的猜测。”我问道:“朝廷为什么要这样做?”花自羞说:“我不方便说。”不方便说,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一言难尽,那就是有一个简单直接又讳莫如深的理由,我俯脸贴在花自羞的耳畔轻轻的说:“只怕抹茶道长那晚的姑娘颇有来历。”花自羞没有表现出吃惊,我猜他是反应迟钝,过了良久,他手一挥说了两个字:“送客”,我就被赶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