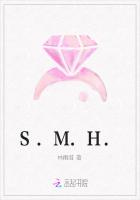生存教育是指与衣、食、住等物质生活有关的知识教育,并且与生产教育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是衣饰教育。壮族的衣饰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比如在制作技术上有“冬编鹅毛、杂木页,夏缉蕉竹、麻纻以为衣”(《岭外代答》),在穿着方式上有“男子左衽”和“女子通裙”,在人体外形上有“椎结徒跣”、“被发文身”,在物品装饰上有“银梳银簪”和各类玉佩等。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审美能力的提高,壮族的衣饰文化也在不断发展,直至近现代有与当地汉族趋同的情况。应该说,在衣饰的制作、使用及经验传导的过程中,妇女的作用要比男子大。比如,妇女作为自己和儿童的主要装扮者,在这过程中肯定对儿童的审美观念和装饰能力起到最直接的引导、培养作用。另外,在前面我们已多次提到,原料种植和服饰制作的教育活动主要在女子之间进行。“女孩们出生以后,就受到母亲在这方面的熏陶和指导。训练出各自巧夺天工的本领和审美的情趣,奠定了后来为人们称赞为‘壮妇手艺颇工的基础。”[6]二是饮食教育。壮族地区有着丰富的食物资源,因此饮食文化十分发达。就总体而言,主要是:以稻米、猪肉、蔬菜最为常见,辅之于各种野果、野味;以熟食为主,辅之于生吃猪血、鱼片等;以煮炖和现做现吃为主,辅之于竹筒饭、五色糯、米粉等花样及粽子、米花、糍粑等“方便”食品。在这一过程中,青少年通过耳闻目睹、口手相传和亲身体验,就逐渐达到了“吃什么”和“怎么吃”的知识和经验的承接。在其中,男女两性各自都发挥着相应的作用,但“炊爨为女子分内职业者”,因此她们的作用更大。三是居住教育。壮族群众从古时的穴居岩处、巢居树宿,到后来的定居干栏,乃至到现代的“洋楼别墅”,使得对后代教育的内容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说在住地选择、房子建造的经验传授上是男女互相补充的话,那么在房屋打扫、布置和料理的言传身教上则是妇女独挡一面。
伦理教育是指与处理家庭关系或社会关系有关的行为教育,它的目的就是解决为人处世问题。如前所述,壮族社会也经历着从群婚到对偶家庭、一夫一妻制的演变,每一种婚姻形式都有相应的禁忌和习俗,因而所起的教育效果也大不相同。在壮族地区,比较常见的婚姻家庭教育就是倚歌择配和婚庆仪式,而这些场合都是妇女起着主导作用的。歌圩主要源自族外婚的要求,这已是很多人的共识。反过来,歌圩促使人们扩大交往,因而有利于对近亲结婚的超越;歌圩通过男女双方的思想交流和互相考究,对为人索养的修炼也起到重要的宣传、引导作用。而在婚庆仪式上,也有很多以女性为主体的礼规习俗、山歌对唱的活动,主要就是对伦理纲常的宣示和强调,从中人们尤其是儿童在亲属制度、长幼孝悌关系方面可以得到最为直观的教育。比如,流传于红河水流域的《盘同古》就是在婚宴夜晚唱的歌,其主要内容就是“借用婚筵向亲朋好友,尤其是青年后生,讲述壮族祖先盘和古再造人类的故事和婚姻的来由,教育青年人要珍惜婚姻之幸福。”[7]又如,“舅公坐大堂”是壮族婚筵中必须讲究的场面,即只有母亲娘家的长辈才有这种资格,也只有等到他们坐好后其他人才能开席。显而易见,这种舅权教育实际上就是一种“母权”教育,它对下一代的辈分秩序观念、伦理道德意识也具有直接的强化作用。当然,处理社会关系的经验教育远远超出家庭婚姻教育的范围,并且男性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但这一切都是以女性占主导的家庭婚姻教育为基础的。
宗教教育是指与信仰对象、礼仪行为、禁忌戒律有关的情感教育,它的主要作用就是解决人们的精神慰藉问题。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指出,宗教也是壮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原始宗教、麽教、道教和佛教等,原始宗教又可分为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在原始宗教教育中,壮族男女具有各司其职的特点。作为长辈,他们万物有灵的种种观念及驱邪祈福的各样仪式,都能使后辈们确信:自己处于一个由超自然力量控制的环境中,因此要四季平安、五谷丰登,就必须崇拜各种神灵。在麽教教育中,壮族男女的地位作用开始出现等级倾向。一方面,男女巫师在教育作用上有差别。就总体而言,做巫婆和请巫婆多为妇人,做麽公和请麽公多是男子;麽公包办祭天、祭地、祭祖等“大事”,女巫则只能从事祈子、治病、招魂、求雨等“小事”。当然,所有这些活动对人们尤其是对下一代的“布洛陀崇拜”,都会起到强化作用,区别只在于作用的大小而已。此外,无论男女巫师,他们都会通过接纳一些男女青年做徒弟,把这些特殊技艺和宗教文化推而广之。另一方面,麽教的男女信徒在行使神权上有差别。虽说无论男女都可以得到麽公的帮助,但在秩序上是严格分为先后,并且仪式一般都是由男性家长来主持。不过,只要是父母长辈主持或参与的宗教活动,都会在禁忌戒律、仪式行为等方面对少年儿童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另外,在壮族地区,无论是道教还是佛教都具有突出的性别等级特点。比如,壮族的麽公和道公都只能由受戒后的成年男子来担任,因此,女性基本没有机会向少年儿童传授招神劾鬼、符箓禁咒或者炼丹修道、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知识。又如,在壮族历史上,相对于较多“花僧”的信息,我们很少见到关于壮族杰出女门徒的记载。当然,在日常生活中向少年儿童描述如来佛祖、观音菩萨的故事,或者提出因果报应的告诫、积阴德的好处,无论男女长辈都是能够并且确实经常做到的。
三、壮族学校教育与男女结构失衡
学校教育是指受教育者在各类学校内接受各种教育的活动。学校教育是生产力发展的的要求和标志。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学校教育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以男女结构失衡为特征的,正如汉克斯所指出的:“正规学校仅限于男性”[8]。在中国,虽然学校教育在夏代已经出现,但直至清朝后期是才出现女子教育。壮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出现于东汉时期,比中原发达地区至少晚了一千多年。但是,壮族学校教育同样经历了私塾、官学、书院、社学、义学、学堂等的历史演变,并且在迈进20世纪门槛的时候才出现女子教育。
在秦及先秦,从出土文物和史志资料上看,都没有壮族地区办学的迹象和记载。壮族学校教育应该说是始于西汉时期的南越国,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当时南越国的丞相吕嘉为越人,宫廷百官、将军中有70多人也为越人,如果没有正规的汉文教育(包括私塾)这是不可想象的。之后,岭南的学校教育不断获得发展,正如黄佐在《广西通志》卷40所说的:“冠履聘娶,华风日兴,人汉以后,学校渐宏”。但是,这种情况可能仅限于桂东,桂西等地区是否有学校则无从稽考。到了东汉,壮族地区有了开办学校的明确记载,比如《后汉书·南蛮传》说:合浦郡对俚人进行了一系列教化活动,即“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聘,始知婚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唐代,壮族地区开始出现州县学,这是各级行政单位承办的学校,当时共创办州学、县学11所。宋代,壮族地区除了学校增加、推行科举外,还办有书院,以作为学子研读学问的地方。此时广西共设置府学、州学、县学共有41所,有清湘书院等9所(元明清时还陆续出现新书院,至科举废时共建了259所,其中南宁地区51所、百色地区12所)。明代,壮族地区开始出现社学。社学在元代已经出现,这是州县学的预备学校,目的在于强化农村的启童蒙、兴教化。但是,广西的社学直到明洪武八年(1375年)才开始创办,此后建有社学232所,不过到明末时几乎全部停办。清代,壮族地区开始出现义学,这是在清初统治者采取抑制书院政策之后,一些地方官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产物,开始时与书院有相同的规则和功能,后来则与社学、义塾性质相似。据已有的历史资料统计,壮族地区共建有义学237所。除了官办或半官办性质的学校外,壮族聚居区的私塾也创办得比较多,这种由家庭、宗族或教师自己设立的特殊教学处所,在广西始于汉代苍梧的陈氏家塾,后来相继获得发展,凡是交通比较方面、人口比较集中、商业比较发达的壮族圩镇,都陆陆续续地办有私塾。
以上这些学校的创办和发展,尽管因朝代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但对壮族教育的深入开展、对汉文化在壮族民间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这些学校教育是以男女在教育机会和教育内容上的不平等为主要特征的。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学校教育只是少数男子享受的权利,社会上根本不存在为女子开设的学校,因而女子被排除在学校之外,没有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即使有少数开明人士在家设塾延师教授自家女子,其教育内容也无外一是《女诫》、《烈女传》、《女孝经》、《女训》之类,从严格意义上讲算不得真正的女学。另外,女子作为教育者的情况在历史上也是很希罕的。直到1898年,以第一所女子学校成立为标志,中国女学才真正出现。壮族是一个女性文化比较突出的民族,但其学校教育的形式,无论是私塾还是官学、书院、社学、义学都是从中原传人,其学校教育的内容乃至所使用的语言都是尽量向汉族地区靠拢,因此壮族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和权利是可想而知的。当然,限于文献资料,我们难以全面窥见壮族妇女被挡在学校之外的情况,但相关壮族学校教育的描述都是采用“将男子经历设为普遍经历”的模式,由此我们就不难作出整体性的判断和结论了。在新学之外能与壮族妇女有一些联系的,同样也只有私塾了。“清末壮族地区有些垫师还开展女子教育,如柳州府欧岳楼、柯孟远、欧阳以圭等私塾兼收女学童,女塾师胡淑按,专设女塾,因此教材之中另有若干专为女子学习诵读的“课本”,如《女儿经》之类。”[9]而女子充任教育者,我们见到了壮族女诗人张苗泉到“亲戚家去教授蒙童,勉强补贴家计”的记录。应该说,类似这样妇女能成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情况,在过去的壮族地区还是非常有限的。历史的发展日益清楚地显示,教育是妇女提高地位作用的重要前提,因此,基本与学校教育无缘的壮族妇女要继续扮演源于远古的重要角色,此时的制约因素是越来越增加了。
清末以后,壮族地区逐渐兴起新学热潮。1902年,桂林等5个县就已开办小学堂。1904年,受维新所需的驱动和影响,光绪皇帝下令废科举兴学堂,于是各地纷纷把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即最初的小学),把私学改为初等学堂(初级小学),其教学内容涉及算术、自然科学或英文等,从而打破儒家经典独霸天下的局面。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广西各类学堂迅速增加,壮族聚居的州县也不甘落伍。到1909年,全广西建有小学、高初两等小学堂1078所,在此期间,中学、大学和职业教育也相继兴起。按时间顺序,至清末广西有高等学堂(大学)2所、简易师范学堂34所,至1909年建有实业学堂7所,至1911年建有中学学堂16所。这些,都使广西初步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为后来的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个阶段也为实现男女在教育上的平等做出了初步的努力。据钟文典教授的考证,成立于1904年、由女性作为教习的容县珊萃女学堂是广西较早的女子学校。次年,容县又有龙胆女学堂成立。[10]1907年,桂林女子师范学堂成立,标志着广西女子师范教育的开始。到1909年,共建有20所各类女子学堂。这应与极力倡导“男女平等之学”的康有为多次来广西讲学大有关联,也说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在壮乡已开始被摒弃。不过,此时的女子学堂所占的比例还是较少,而且极不稳定,没过多久就停办的很多。
民国成立以后,壮族教育在艰难中跋涉。1911年至1925年旧桂系时期,受军阀混战的影响,广西教育没有大的发展,并且封建办学思想仍十分突出,从女学来讲甚至有些倒退的迹象。比如,重男轻女现象严重:无师范女校;中学以上学校不招女生,“民国十一年三月,省立第一中学招女旁听生数名,省当局发觉后明令辞退”[11]。即使是小学教育,女校及女生数量、比例都很有限。新桂系时期,受统治者培养和延揽人才需要的驱动,广西各类教育获得了较快恢复和发展,其中,男女教育平等方面的成就是:在加强女子师范、女子中学建设、创立师专的基础上,设立男女兼收的高中师范科、师专师资班;设立民众学校,男女兼收,后来还根据有关规定把失学成人男女分别强迫编入成人班,让他们接受基础教育;进行教育大众化宣传,实施有利于壮族女性接受教育的民族教育等。总体而言,民国时期的壮族教育虽有一定发展并为广西的各项建设培养出许多栋梁之材,但由于原有基础、制度体制等原因,这种发展离男女教育平等的真正实现还有不少差距,比如还存在教师中女性偏少、一些地方“女子概不读书”(民国《崇善县志》)等情况。看来,壮族地区男女教育平等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一种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社会制度,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比如,早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党和政府就把“实行男女共同教育”作为一个重要方针和政策来强调。新中国成立以后,壮族儿女幸福地生活在祖国大家庭里,平等地沐浴着社会主义教育的阳光雨露,共同成长和进步。
(第二节)壮族科学与两性智慧
很多研究成果表明,科学是最具性别分层特征的领域,“科学是一种男性智慧”的观念源远流长。[12]从历史上看,科学无非是关于世界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及其知识体系,由这些认识发展成的各种操作方法和技能就是技术。壮族及其先民在长期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科学认识,但基本没有形成文字形式的成果,并且偏重于实践经验的层次,尤其源于种植、健康等直接生存的需要。正因为缺乏深层理论研究(与性别二元对立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加上浓厚女性文化传统的影响,因此壮族科学技术中的性别对立相对较缓。
一、壮族种植科学与女性的主导地位
梁庭望教授指出:“长期以来,水稻一直是壮人的主食,所以壮人对它也就格外用心。因而水稻种植科学,便成为壮族种植科学的代表。”[13]壮族很早就成为稻作民族,尤其在甄皮岩人时代可能已有水稻的栽培,所以,经过几千年的摸索和积累,形成了丰富的水稻种植经验,有些还是很符合科学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