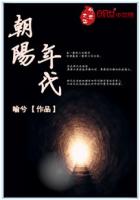“夜王道是衷心?”听禹缓缓问道,“衷心嘛……不是没有,只是夜王不知。”
“的确。我找不到如瑾雍将士忠心于主的人,大概是我这个人吧,实在不值得为人所忠。”夜满楼叹息,看了看墨焱,看了看听禹,最后目光不知偏向何处,似是在青州也似是在天边。
听禹追随着他的目光,看向青州看向天边,迎着夕阳,任着夕阳在她的脸上留下金色的温暖痕迹。许这番事就这般结束了,或许,这也是最好的结果。
夜满楼无声的叹了口气,拉过缰绳,将墨焱带到自己面前,红袖轻甩,翻身上马。他笑道:“于我来说,瑾王一直都是为帝的首选,何甘受困雍州?”
听禹从容的抬头看他,仰视不失贵者风范,王家所养育的人,永远都不会低人一等。“因为于我看来,七世子才是为帝首选,我何苦……两两相争,敌损一千,自损八百。”
夜满楼无声的勾了勾唇角,渐渐地视线移到她的双眸,清澈无暇,淡如水、轻如云,就如这世间没有一物能令她沉重、没有一物能令她激动,她太过平静、太过超脱,或者说她从不在意世间百态如何变化,或者说她是什么都在意,但一旦一双眼睛看透了所有,那这颗心,就会变得无情。
“瑾王……多情又无情。”当他第一次在帝都看见她,就对她下了这样一个定论。她对万物都关心,却没有一件事能上心,许是为王者都是如此。
他笑笑,拱手一礼:“今日,多谢瑾王来送。”
“夜王可有去处?”
夜满楼摇头,扶着额头叹气,同时有些遗憾道:“我是准备去绀玺山的,可想想我这三千青丝……全都剃了岂不可惜。”
“哧……”听禹失笑,无奈的摇了摇头,脚步轻移到了墨焱面前,抚了抚它头顶,“要去哪便去哪。待定下了,记得来信就好。”
听到这一句记得来信,夜满楼心下顿时一软,不知被什么东西刺痛了一下。眼底,就是她浅浅带笑的脸,只要他俯身就能触到,亦或是只要他一句话,他就能带她走。
张了张口,已经到了喉间的话马上便要说出,他却无意间看到了她腕间的水晶链,兀自舌尖一转,只说了两字:“走了。”
黑马飞去,带起一阵细风,卷起一地落叶,吹翻她的裙角。
待到这一红一黑在夕阳下渐渐消失,渐渐没入夕阳,渐渐与这天地融为一体,她方才收回视线。无声的笑笑,听禹抚平被吹皱的衣摆,正得见她脚边落下的一颗黑石。
她拾起,将石上的土擦拭干净,才知这只是一枚小小的棋子,棋子上清晰地刻着一个字:楼。
时至亥时三刻,雪羽骑军中各个营帐的灯都还亮着,听禹走进不禁觉得有些不对,至于哪里不对,她也说不清楚。
军中留有一部分巡夜的将士,篝火依然是点着,有人进进出出气氛也算是和谐,实在找不出什么不对的地方。
走去她营帐的路上分别要经过柘青、言柒的军帐,柘青似乎也未睡下,帐中灯火依然点着,只是没有什么声响。
待到言柒帐前,听禹顿了下脚步,薄唇微不可见的一抿,脚步一转,便朝帐门走去。
撩帘进去,帐内柘青、苻遗、裴墨严正以待的坐在两侧,帐帘正对的正坐上,言柒正低头看着手中的卷宗。
听禹进去,坐在两侧的那三人微不可见的呼了口气,然后同时看向正坐上的那人。
言柒依然看着书,似是没注意到帐中进来一人。
见主人不说话,那三人又看向听禹,只见听禹不见任何神色,只抱拳略略躬身淡淡唤了句:“世子。”
言柒翻书的手指一顿,抬头,便见一头墨发,合上书,言柒靠进椅背,“瑾王来了正好,言柒正准备与瑾王商量些事情。”
“世子请讲。”听禹起身看向他。
“请瑾王回雍都。”言柒也看着她。
随着尾音落下,帐中温度从最初的不冷不热一下子跌入冰窖。两人对视,这样一般深情对视本该是男女情愫的开始、是郎情妾意的源头,可这两人之间不知有无情感溢出,但帐中温度就是在他二人的目光中骤然下降的。
不知过去多久,听禹缓缓垂下眼睑,一拜道:“本王听从世子安排。”
言柒随之收回视线,从容的落回书上,大致看了三四行,记下一些字句,他提笔,在书中圈下一行字,淡淡念道:“施人之慧,受人之恩,一不心记,一不心忘。”
“不知世子想要本王何时出发?”置若罔闻,事不关己,听禹问道。
“后天,一百雪羽骑护送,瑾王说,这样可好?”言柒放下笔,搭在玉砚边沿,思索一刻又道,“不若两百吧,瑾王身份高贵,切不可忽视了。”
“雪羽骑乃雍州军队,一切交由世子定夺。”
“也好。”言柒点了点头,起身绕过案前,走到听禹面前,一边伸手请她随自己来,一边出了帐外。
绕至雪羽骑军中,经过几间帐中,便到了苻遗帐中。身后紧随着的苻遗会意,从自己桌上抽出一本雪羽骑将士登记册,摊开递到两人面前。
言柒翻开,提起朱砂笔递给听禹,“由瑾王亲点,两百雪羽骑随行。”
“多谢世子。”听禹接笔谢道。
言柒不以为意的回之一笑,转头对身后随来的几人道:“你们先出去吧。”
“是。”三人同时应声,同时抬头瞥了两人一眼,叹了口气,这才退下。
垂首看着名册上落下一个有一个朱砂记,言柒呼了口长气,惆怅愁苦,又不知何来惆怅,何来愁苦。
点名的笔尖顿了下,遂又点起,耳际紧接着就传来听禹如玉珠落盘的声音:“世子拖本王回去,所为何事?”
言柒绕到听禹身后,坐到她身后的椅上,“倒不是什么重要的事,王妃又在蠢蠢欲动,言柒希望听禹回去能多多少少让她收敛些。”
“这样……”听禹不气,反而意味深长的笑道。
言柒双手一僵,试探着问道:“听禹……若是不愿,言柒不会勉强。雍州的事,毕竟……”
“无妨,”听禹丝毫不以为意,点好了二百将士,将名册放回原处,朱砂笔放回笔架,她这才不疾不徐的接着道,“反正这战场上也没有本王用武之地,倒是雍都比较适合本王。”
“如此……也好。”言柒抚了抚额头,他倒是后悔个什么劲儿,怕是没有几个女子会喜欢战场。
七月二十七日,瑾王受七世子所托,启程转回雍都。
七月三十日,瑾王一行人途径瑾州,停歇一日。
踏着一条条碎石铺成的羊肠小道,两人穿梭在高高的芦苇荡里,风轻拂着大地,听着飒飒的风声和清脆的蝉鸣,一种美感油然而生,这时,只需用心去感受这纯洁的自然之美。
她闭上眼,聆听着夏的宁静。
偶尔传来的蛙鸣声不禁使人想起一句诗来。
“须找人,稻海深处;一步步,踏停蛙鼓。”
正如诗中所说,刚刚停下脚步,就听到了声声蛙鸣。忽然,水面上一只蜻蜓点过,在水中散开了一朵涟漪,渐渐的氤氲开来,宛如一朵清莲在水面轻轻绽放,水因为映了夜空的颜色如墨色绸缎,点缀着晶莹剔透的珍珠。又是一阵风,芦花飘落像下雪一样。
芦苇荡深处是一处凉亭,两人不约而同的走了过去,在石凳上坐下,同时看向月色。六月中旬,月还是圆的。
“也不知那边怎样了。”风中,御寒芙的声音凉凉的响起,和着夏日月夜独有的凉,显得有些孤苦和怅然。“瑾王不会担心吗?”
听禹倚在亭柱上,恍若未闻,自顾说道:“郡主的歌声最动听了,便唱首歌吧。‘醉江山’可会?”
“醉江山……”御寒芙叹了口气,“为什么会不想不问不顾呢?”
“他当初的决定就未把你的担心放在心上,郡主何必自作多情呢,更何况这个地方再怎么忧心他也看不见,不是吗?”听禹笑道。
“那便为王唱首歌吧。”御寒芙迎着茭白的月色轻起歌喉。
镜,人似水,当时惘然,不察。
夜,水似花,未雨绸缪,不却。
莲,花似月,纤尘不染,不浊。
琼,月似人,相约无期,不念。
无琴相伴,孤独的歌声与孤寂的月色相依,在这芦苇荡中唱出她心中的花间醉。无谓情、无谓人,她心中所想似是从未有过任何事,但又像什么事都在她的交合混杂。
御寒芙的歌声一直都是她的心声,许是她不爱言谈,她的心事便是心曲,一旦唱出,便是哀婉凄美。
她低着头,看着自己随风起伏的裙摆,紫绫纱的外裙在月色下闪出一点荧光,孤单、落寞。
“想他,是因为在乎他,在乎他,是因为心中所想,既然这样,就该去说。”殇儿曾对她说过这句话,可是被她忽略了。
初见他时,醉江山被她的一个错音破碎,也是那时,便对那个身影有着些许在意。事件不断推移,那点在意便在心中阴暗的角落生根发芽,最后成长壮大,便成了再也无法割舍掉的盘根错节。
“郡主不善言谈,若是钟心于谁,便告诉本王,本王自会为瑾州的郡主做主。”听禹看着她,缓缓道,“郡主的年岁也差不多了,倒是与七世子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