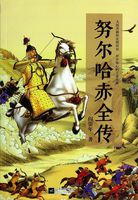陈群将司马懿请进自己的屋子,陈群原本拉他与自己平坐,但司马懿还是依宾主之礼就座,陈群正准备整整衣冠端坐于席,这时只见司马懿如同孩子一般从席上跳起,笑呵呵地走到陈群身旁,问道:
“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
“什么?”陈群一脸疑惑。
“匈奴人的事啊,河南尹怎么有匈奴人?还有,刚才我分明听到喊声说匈奴人闹事,你却不痛不痒地来句‘这种事天天都有’,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想到仲达的好奇心这么强,好吧,我就说与你听。”陈群捻须道,“我朝自光武皇帝将内附的匈奴安置于边境八郡以来,虽时有冲突,但彼此大体还算相安无事。到孝桓皇帝时,朝局动荡,国家多事之秋,南匈奴趁机侵占我内地郡县,百姓死伤无数,好在匈奴中郎将张耽率兵平定,然而此后南匈奴各部时有暗自迁移内地之举,朝廷也无力禁止,只好听之任之。现在光平县就有百余匈奴人,这些匈奴人目无法纪,整天惹是生非,不是抢东家的粮就是偷西家的牛。”
“百姓不恨,官府不管吗?”司马懿一脸严肃。
“恨有什么用,来气了打他们一顿,是泄了恨,但事后匈奴人逍遥,百姓却得坐牢,所以只能干瞪眼。不过有时民愤过大,官府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否则激起民变,那就不是打一顿、坐几天牢那么简单了。今天的事,我看小不了。唉——”陈群无奈地摇摇头,“都是朝廷不争气!别说匈奴了,就连乌桓、鲜卑,甚至南蛮这样的蚁虫之流都欺负到我天汉的头上。真不知这世道会变成什么样。”
陈群所叹其实也是司马懿所忧,但他不像陈群那样悲观。大乱之后必定大治,《易经》里说“否极泰来”便是此理。天下大乱则必有真龙出,也是我辈施展才华抱负之时,如此有趣之事,何苦唉声叹气,像个小媳妇儿。
司马懿瞧了眼陈群,心中继续想道:只是,谁会是这条真龙呢?他记起父亲在自己出门前跟自己说起的一个人,那个人叫孙策。
孙策是破虏将军孙坚长子,其父死时,孙策才十七岁,为继承父亲遗业屈附袁术,如今这位孙郎已聚有近万人马,逐渐摆脱袁术控制,正在江东大展拳脚。
父亲为什么要跟自己提起这个人呢?大概是他青春年少,却已名声赫赫,父亲想以此鞭策我吧,不过孙策年纪尚轻,谁能料定他今后如何。
说起少年郎孙策,司马懿想起了十三世祖司马卬。司马卬二十二岁为赵国先锋,与诸侯伐秦,秦灭后被封为殷王。每次想起这位先祖,司马懿总会热血沸腾,脑中浮现出金戈铁马铿锵,气吞万里如虎的情景。虽然自曾祖开始,司马氏便以儒学传家,但先祖的武将血统,早已沁入家族的骨血,可以说,司马氏文武相济,有别于一般的士族,这一点让司马懿格外自豪。
当晚司马懿与陈群聊《易经》直至天亮,却丝毫不觉困意,似乎还意犹未尽,只是还需赶路,否则司马懿真想继续与陈群讨论义理。洗漱完毕,吃了些家仆准备的点心,司马懿打算拜过陈老爷子就离去,但家仆说老爷还在屋里睡觉,司马懿只好跟陈群道别,说身上还有急事,恕礼不周,有缘再见。
“其实我昨天就想问,结果一聊别的就忘了。”陈群笑道,“仲达,你此番不顾兵荒马乱来到河南尹,定有什么要事吧?”
“也说不上什么要事,只是家父准备让我出仕,但所学尚浅,便来此地求访名师。”
“哦?”陈群有点诧异,“河内司马氏百年名门,家学悠远,还需要拜访名师吗?”
“长文兄有所不知,按理说我想要出仕无须费这份心力,但家父教导极严,家学之外还要求我们博采众长。所谓学问在他家,访师问道总是好的,况且现在这个世道,你认为,出仕就是唯一的正途吗?”
这句话把陈群问住了。
陈群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他出身于传统的官宦之家,在早就被固化的观念中,像陈群这样出身的人,人生的道理莫不是熟读儒经,察举孝廉,郡县为官,而后兢兢业业,侍主奉公,这是一条被视为正途的出仕之道,而今司马懿却质疑起这条道路来,他那颗大脑袋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我并不是说传统的出仕之道不好,而是说,人活一世应该有很多种选择,尤其是现今这个世道,即便举不了孝廉,我们也可凭自身所学,辅佐明主干出一番事迹,以昭后世,如此岂不更好?家父让我访师问道,为日后出仕多添一个好名声,而我只想增加自己的才学,至于前者,并不在所想之列。家父不也是正途出身,到头来又怎么样?”
司马懿如同看透了陈群的心思一般,道出了答案。
“仲达的这番话,要是被令尊大人听到了,非把他鼻子气歪不可。不过你年纪尚浅,却有这般见地,实在难得。”
“我这也是一路所思所想,见笑了。”
“不过,你要拜访的那位名师到底是谁呢?”
“是现居陆浑山的孔明先生,姓胡名昭。虽然现在才出来拜访孔明先生,但几年前便已心向往之了。不过听说孔明先生深居山中,轻易不见人,我又不知他具体在山中哪处,心中打鼓,还不确定能不能顺利找到他老人家。”
“等等,你说你找孔明先生?”陈群的声音有些不自然。
司马懿点点头。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陈群挥动着手,像是跳舞一样,围着司马懿转了好几圈,“真是耽误事。”边说着,边钻进陈谌的卧室,一刻钟不到,便乐呵呵地走了出来。
“有了这个,孔明先生一定会见你的。”陈群把一张帛书交给司马懿,继续说道,“陆浑山有个叫红石峡的险处,一旁为峭壁,一旁是只容一人的山道,沿山道走半个多时辰,你会看到一处山洞,孔明先生就住在里面。”
司马懿打开帛书一看,是介绍信,上头写着自己的家族事迹及基本情况,此外并没有特意赞美的话。
“我怕你初去,迷了路,特意给你画了张图,你照此寻路即可。”
司马懿接过地图,心头涌上一阵暖意。
胡昭曾客居冀州,专研书法,那时陈谌正在冀州游学,对于书法也略懂一二。两人因志趣相投而结交为友。胡昭比陈谌足足大了十二岁,当陈谌称其为“先生”时,胡昭却说“太生分,你我之间不要这么虚套”,陈谌称其为“兄”,胡昭还是觉得“又玄又虚,叫我孔明更为省事”。
于是,一对忘年交,居于陋室,切磋技艺,谈经论史,一晃两年光阴便匆匆而去。陈谌遵从父命,出仕为官,去司空府做了一名属官,而胡昭为了避开请他出仕的那些地方豪强,也计划着离开冀州。
分别的那晚,两人都喝醉了。陈谌本是滴酒不沾之人,刚喝上半口就头晕不止,但还是忍着难受陪胡昭将打来的酒全数喝完,说了些什么,陈谌都已忘在脑后,唯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胡昭的哭声。
他不知道胡昭为什么而哭,他很惊讶,胡昭粗眉圆眼,身材魁梧,声音洪亮,给人以军中武将的印象,根本没有人会想到他只是一介文人。两人交往两年,这是陈谌第一次看到胡昭哭泣。他在想念什么吗?陈谌这样想道。
翌日下午,两人默默无言,挥手而别,陈谌上任的第二天就给胡昭去了一封信,但胡昭没有回信。陈谌并不在意,还是继续写他的信。
司空属官,尤其像陈谌这样的掾佐,每天的工作无非就是整理文牍、管理档案、写写公函,陈谌自认有些屈才,但自己刚刚出仕不能急于一时,他只能将心中的郁结写在给胡昭的信中,这世上或许只有他才最懂自己。
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有余,这天中午,陈谌正在掾厅小睡,突然有人进来通报,说门外有人找他。陈谌到外面一看,门外站着的竟然是胡昭。
“孔明,你这是……”
“别来无恙,季方(陈谌表字)!”
胡昭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颌下的胡须随风摆动,头发稀疏了不少,略有些苍老,精神却依然矍铄。
陈谌告了假,拉着胡昭上了洛阳城内最好的饭庄,点了胡昭最爱吃的清蒸黄河鲤鱼,没等菜上来,陈谌便耐不住性子问道:
“孔明,你这次来是专程看我的?”
“这偌大的洛阳城,我可只认识你一人。”
“你这一去,音讯全无,快说说,你都干什么去了。”
“季方,你今年都二十七了吧,还一点都沉不住气?仕宦之路荆棘丛生,依你的脾气秉性,怕是很难高升。”
“也就孔明你能说这番话。”
“离开冀州后,我就回了家乡,耕读过日。上月家母辞世,世上已无牵挂,你也知道,我本是闲散之人,做官入仕非我所愿。我已经打算好了,去陆浑山隐居,我现在孑然一身,倒也轻便,陆浑山离洛阳不远,咱们随时可以见面。”
“还是你好啊,随心所欲,而我,却像是关在笼中的小鸟。”
这次别后,倏忽十余年,陈谌从司空属官转为淳于县的县令,三年后又从淳于县县令转为昭县的县令,此后一直在县令这个位子上迁来迁去,将大半个大汉天下都走遍了,还真是应了胡昭的那句话。
无论去哪里任职,陈谌每年都会去陆浑山一趟,两人见面后话不多,彼此情谊却随着岁月的积淀越发醇厚。近几年,两人相见甚至无话,一人哼着歌谣,一人望着近处的溪水,一坐便是半天。
陈谌如今早已没了年轻时的毛躁,到他这个年纪,该想开的都已想开,想不开的就让后辈去想吧。陈群倒是个好后辈,只是阅历尚浅,再过段时间,也该让他出去了。
陈谌看着陈群手捧帛书、高兴离去的背影,这样想着,很快又陷入睡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