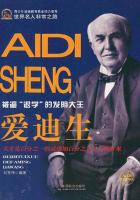汉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五月,曹操失去了一位谋士。
这位谋士叫戏志才,三年前经同乡荀彧推荐辅佐曹操,所献筹划无不应验,被曹操倚为左右手,与荀彧同列。只可惜天不假年,刚过而立之年便病逝于南征张绣的途中。
曹操失去一臂,悲痛不已,连夜写信给身在许都的荀彧,让其再为自己推举人才,因崔琰身在城内,他便很自然地想到推荐自己这位老友入幕,崔琰与荀彧同年,如今也已三十有三,但还没有家世妻儿。作为朋友,荀彧很想让他安定下来,娶妻生子,有个安稳的家庭,安居才能乐业,古来皆是如此,但崔琰忙于给《公羊传》作注,拒绝了他的好意。
“文若(荀彧表字),许都内人人都称你公允,可在这件事上你却没做到啊!”见荀彧一头雾水,崔琰笑道,“你只记得你的老朋友,却忘了你年轻时开馆招的学生,我是说郭嘉郭奉孝啊,你这大脑袋,竟没装着他?”
“郭嘉?”一听到这个名字,荀彧才明白过来,“都怪我糊涂了,糊涂了。”
荀彧放下手中曹操的信,往文案左侧的青铜油灯里添了些新油。
“我追随司空以来,五载光阴,都在征战中度过,年初幸得主公攻取许都,我才能在阔别多年之后踏足桑梓之地。本想访旧拜故,可如今我身负尚书令重任,领百官政事,又得为前线供应米粮,征送兵卒,一刻不得闲,也闲不下来,竟然把我的得意门生给忘了,这真是家中有宝向外求,差点误了他的前程。”
“文若的辛忙,我怎能不知呢,用不着一件件都跟我说,难道是怕我骂你懒不成!”崔琰抚手大笑。
“我来许都前,曾路过阳翟,在西市恰巧遇到了他。他如今也在家中设了学馆,有模有样的,口碑极好,还真是你的好学生!”
翌日天色微明,在崔琰的陪同下,荀彧策马来到郭嘉家中,也不叙师生之谊,直接说明来意。郭嘉见老师不顾路途劳苦,亲来求贤,不好推辞,也就应允下来,不过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在于郭嘉对天下形势的观察。
两个月前,曹操听取荀彧意见,将皇帝从洛阳迎入许都,并营造内城供皇帝嫔妃及公卿居住,曹操以迎驾有功被封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对内总览朝政,对外奉诏讨贼。
郭嘉判断,曹操虽然处处以皇帝诏令行事,但那诏令本身,与皇帝一样,根本只是个傀儡,曹操才是幕后总指挥。此人起兵之初,名微众寡,如今却能占得先机,定然是个有能耐的人。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自己辞袁绍归故乡,无非是待明主,托所学。
正事谈完,郭嘉招待参观自己的私塾,说是私塾,只是后院猪圈翻造的石头小屋,内中不过七、八个孩童,正冲孔子牌位行礼,礼毕后正欲出屋玩耍,见老师带着两位客人进来,又循礼拜见。
孩童们走后,荀彧感慨道:
“腹有诗书气自华,行无仪轨人自厌,不管什么世道,诗书礼仪都是立身根本,奉孝啊,你是有心之人。”
崔琰也点头称赞。
郭嘉谦虚地笑道:
“先生,你可还记得陈长文?”
“记得,记得。”荀彧瞧瞧崔琰,像是担心他又说自己把门生给忘了,“他出师后举孝廉做县令,还常写信问候我,后来世态多变,我先是避乱冀州,后去幽州求访高明,又辗转到了兖州,这中间先是误投袁绍,再遇司空,居所迁移,庶事多杂,渐渐地就没了联系,看来我这个先生做得还真是不称职啊!”荀彧自嘲般地一笑,问道,“你有长文的消息?”
“曾见过一面,后来去了陆浑山。”
“陆浑山啊!”崔琰若有所感地捻捻自己的八字胡,“那座山能塞得下那么多人吗?”
见到崔琰是在一个下着雨的早晨,司马懿吃完饭,正准备去帮胡昭清扫山洞,快到洞口时,看到一个身体微胖,身着粗布衣,头戴斗笠的人背对洞口,背着手,欣赏雨幕中的山中风光,时有鸟儿在耳畔啼鸣,这景象,真真如一幅高逸图。
再定睛一看,那不是崔先生吗?
司马懿正要喊他,又突然闭上张开的嘴,在这种诗情画意间,高声喊叫,岂不煞风景!他轻轻挪步来到崔琰身边,顺着他的视线,注视着一片挂满雨滴的阔叶。就这样两人默默无语地站了一刻多钟,雨势逐渐转弱。
“司马小弟,要是每天都能与这样的美景相伴该有多好。”
崔琰依旧目不转睛地盯视那片叶子。
“先生好兴致。”司马懿睨了眼崔琰,说道,“先生说得这般感叹,不会是又遇到什么事了吧。”
“我是来送信的。”崔琰从怀中掏出两份帛书,这两份帛书分别是荀彧和郭嘉写给陈群的,前者述师生别来之感,并问其是否愿意效力曹操,后者告知陈群自己投曹一事,并说明原因。两人言辞各异,但都是希望陈群识大势,建功业。
郭嘉更是在信末这样说道:
曹公恢廓大度,行法治,明赏罚,将士用命,群属一心,故而陈留起兵以来,虽有颓唐,亦不过万尘归土。士人以学立身,以智谋功,择明主而事,言听计从,岂不快哉!曹公言平定天下,谋功最高,才为世出,世亦须才。人杰盛年,焉能图一人之安乐,忘苍生之倒悬,兄若不出,更待何时!
崔琰将帛书收入怀中,说道:“许都堂皇热闹,却也容易令人生腻,荀彧、郭嘉要遣人送信,我也正想换换环境,就揽了这份差事,来这青山幽谷间,洗洗我这双有点昏花的老眼。”他回过脸对着司马懿,“司马小弟,你可曾读过《公羊传》?”
“读过,先生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
“有什么心得吗?”崔琰摘下斗笠,弯下腰轻轻甩了几下。
“《公羊传》不重释史,以解《春秋》微言大义为其要旨,论而无偏,不杂私意。世人言其文辞有失精细,在下倒觉得,粗疏俗气其实也显出作者的洒脱自在。”
“司马小弟,你说的都是平常之论,没什么新意。”崔琰重新戴上斗笠,笑道,“我且问你,《公羊传》宗旨为何?”
司马懿对崔琰跟他谈起《公羊传》十分不解,既然有荀彧、郭嘉所托信札,就先把这事了了,还在这细雨中聊什么宗旨,但崔琰毕竟是长辈,岂能不恭敬答对,于是他扬扬头,咽下一口唾沫说道:
“在下以为,《公羊传》宗旨是贬纷乱,正一统。纷乱不是常态,一统才是王道,它应人、应运、应天而行,合秩序纲常,明君臣之义,顺昌逆反。昔秦皇扫六合,文同书,形同俗,车同轨,度同制,结束战国大争之世;秦二世大兵四起,高祖皇帝白蛇起义,造天汉基业,民安于太平,士乐于学业。从高祖到如今,四百余年乾坤浩荡,天下又遭分裂,不过在下相信,它终究还会归于一统。高门世族承朝廷恩惠在上,系百姓举望于下,受圣人之教,诗书传家,当尽自己一分绵薄之力,开万世之太平。”
“正一统!”崔琰低眉一笑,“司马小弟,你说得好啊,这也正是我笺注《公羊传》的目的,越是纷乱之世,越要倡导一统,而这一统的前提,便是你说的合秩序纲常,明君臣之义,如此,刘家天下当有再兴的那一天。”
对司马懿,崔琰始终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既赞佩他过于常人的才华,又对他的狼顾之相怀有深深的芥蒂,只因第一次见到司马懿时,留下的印象实在过于深刻。
赞佩他的才华,于是介举给胡昭,胡昭本不想再收弟子,经他反复说明才答应下来,在山洞外头次看到他,胡昭就体会到了挚友口中所说的“颤悸”——那是一种让人不由自主倒吸凉气的惊诧,因此在传道解惑之余,常以旁论感怀的方式,让其知晓为人大义,希望他能从中有所发散领悟。
崔琰跟他谈论《公羊传》也是出于同一个目的,司马懿既然说出了自己想要听到的“合秩序纲常,明君臣之义”,他也就不用再往深了去讲。他确信,司马懿能了解他的用心,因此也就能理解他为什么会跟自己聊起这本古籍。
他欣慰地一笑,转身正要向学馆方向走去,蒋济这时急匆匆向上跑着,边跑边喊:
“仲达!仲达!”
一见崔琰在侧,急忙施礼,崔琰知道他有事,径自走了。崔琰走远后,司马懿把蒋济拉到山包旁,怪道:
“你大呼小叫的干吗!读书人遇急不躁,遇乱不危,遇难且忍,这些你都不知道吗?”
“哎,仲达,你要是知道是什么事,你就不会这么说了。”蒋济嘿嘿一乐,说道,“你大哥来了。”
司马懿一听大哥来了,心里猛地紧缩一阵,看着蒋济没心没肺似的笑容,他丝毫不感到有什么可乐的。他第一反应,会不会家里出事了?难道是母亲病故了?
一想到这里,顾不得刚才自己说的什么“遇急不躁”,撒开两条腿,奔下山洞,见大哥正与陈群谈笑,心头这才放宽,看来是自己多虑了。他缓了缓急促的呼吸,趋前几步,向司马朗行兄弟之礼。
“仲达,你们兄弟俩聊着,我告辞了。”
陈群正要走,司马懿急忙拦住,“长文兄,别急着走,还有事跟你说。”
原来司马朗这次上山,还真与母亲有关系,不过不是母亲病逝,而是母亲想念远方的亲儿。两年前,司马懿回家,母亲恰好在张世伯家小住,回来后因虚累,也不能与之长聊,故而司马懿虽在家日久,但并没能天天在母亲榻前陪伴。
可能是岁数越长,思子之心越为迫切,加之如今众儿都在家中,唯有司马懿远在他乡,心里头极想招回儿子,陪伴左右,但她也知道男人志在四方,不能因一己之心耽误了儿子。司马朗不忍母亲整日唉声叹气,恐伤肺腑,便替母亲前来看望司马懿,只要儿子一切安好,母亲也不会过于担忧,虽不能亲见,但也可安慰其心。
行至山下,司马朗改了主意,二弟如若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不妨让他跟自己回家一趟,待上个十日一旬,以解母亲思儿之苦,司马懿听罢,立刻答应。
“大哥远来,先在山上住上两日,咱们再回。”
兄弟俩说完家中的事,陈群开口道:
“仲达,你说有事找我,什么事?”
“崔先生来找过你了吗?”
陈群一听这话,立刻明白司马懿想要说什么。
“你说的是这事吧!”陈群从袖子里掏出帛书摊在地上,凝视了一会儿,“一个是我的蒙师,一个是我的同窗,前后都投了曹操,我这个后学自然不能故作清高,没有不去的道理。”
“这么说你已经打定主意了?”
“蒙师是本郡世家领袖,他既然投了曹操,我想这个人必定有不同之处,我投曹操,也算是追随蒙师吧。”
“他的确有不同之处。”司马懿想起了曹操的那双小眼睛,不禁一笑,“这样一来,曹操的帐下谋士,你们颍川郡可占了大头,这对你来说是好事,对别人就不一定了。”
“这就是后话了。”陈群说得很淡然。
他有理由淡然,他的想法很简单,合则留,不合则去,其他的并不挂在心上,即便挂在心上,可能也是徒劳的,很多时候,人算不如天算,既然算不准,操那份心又有什么用。
“辛毗走了,这次你又要走了,以往的热闹景象,越来越淡了。”司马懿惆怅地看着地上的帛书,道,“春发秋落,四季轮回,可是人呢,就此别过,也许再无相逢的时候。”
“仲达,无须长吁短叹,人生长久,相逢有期……”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真不知为谁辛苦为谁忙啊!哈哈——”
老远就听见胡昭的声音,没多会儿,他与崔琰从雨幕中进来,三人起身施礼,陈群问道:
“二位先生,什么事竟让你们这么高兴!这可少见。”
胡昭示意他们坐下,用一双长袖掸了掸衣裳,笑道:
“方才季珪跟我说起去年郭汜与张济相争的事。”胡昭在陈群和司马懿中间坐下,“两人都想据天子为私物,以获得至高的地位。先是郭汜被张济击溃,杨奉去河东召集白波旧部,还请了南匈奴右贤王相助,郭汜借此反扑,这回是张济栽了,听说他有一队铁甲骑兵,甚是厉害,可是碰到匈奴人,就如同俎上鱼肉,只能任人宰割了。之后张济卷土重来,与郭汜、杨奉等人相持于安邑,天子派董承与郭汜、张济讲和,这个时候,彼此对垒已两月有余,兵士都已疲惫不堪,于是趁此给自己找了台阶,各自罢兵,让天子一行人回了洛阳。”
“那渔翁呢?谁是渔翁?”司马懿急切地问道。
“司马小弟也有这么急躁的时候,呵……”开口的是崔琰,他说,“皇帝回到洛阳后,以董承行事机敏,护驾有功,选他家的姑娘入宫做了贵人,董承一晃竟成了国舅。得渔翁之利者,董承可算一个,不过,真正的大渔翁非曹操莫属。”
“季珪是说曹操胁迫天子入许都这件事吗?”司马朗问道。
“正是!曹操以洛阳残破,不适銮仪久居为由,强逼天子随他去了许地,并以此为新都,皇帝虽高坐殿上,但实际发号施令者,则是曹操。现在许都城内早就传开了,说什么‘权归曹氏,天子总己’,这或许是我那老友荀彧没有想到的吧。”
“先生以为曹操有篡汉的野心?”司马懿上半身稍稍前倾,两眼盯视崔琰。
“那倒未必。”司马懿的这种眼神让崔琰很不舒服,但他还是徐徐说道,“以我之见,纷争之世,确需强人力挽狂澜,现今天子年少,非常之时,非常之策,曹操如能扫荡群雄,复兴汉室,权柄在手,荣宠加身未尝不可,我想,他顶多只是霍光之辈。”
“霍光尽心汉室,但他的后辈子侄欲除孝宣皇帝而自立,也是不争的事实。”
“百年之后的事,谁能料到呢?”崔琰意味深长地一笑,“即便料到,那时你我都已成灰土,也无能为力了。”
“正因这样,才要防患于未然,先生不知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吗?”
崔琰咳嗽了几声,微垂着头,看上去有些疲惫,他抬眼瞧了几眼司马懿。比起两年前,这个年轻后生的面相成熟了不少,山上的生活使他的肤色变得更黑,胳膊变得更粗,声音虽然还是一如从前般的糙,但也更为洪亮。
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崔琰思量着,久久没有说话。
“季珪,你怎么了?”司马朗关切地问道。
“我在想司马小弟刚才的那番话。”崔琰抬起头,视线扫向某个角落,而后落在司马懿的脸上,“司马小弟,听孔明先生说,有个叫周齐的人自打你上山后就一直跟你过不去?”
“嗯!”司马懿应了一声。
“你既已知道他屡屡与你作对,为什么不先制伏他,让他不为难于你?先下手为强后先手遭殃,不是吗?”
原来他是在这里等着我!司马懿这才回过味来,崔琰突然提起周齐,他这是明摆着噎我,一代名士竟然也做这等事,有趣,有趣。
半个时辰前还是瓢泼大雨,现在已是艳阳高照。马蹄踏在被雨浇湿的大地上,溅起半腿高的泥水,沿途花草茂盛,气味清香,让司马懿郁闷了半晌的心情,稍微纾解了不少。
“仲达,长文已走了多时,你还不能释怀?”
“我记得得知佐治走的那天,也是下了一阵大雨,因此触景生情,发了许多感慨,大哥不会是在笑话我吧?”
“我怎会笑话你,大丈夫理当重情重义。”司马朗打住马蹄,深吸一口气,说道,“如今稍有名声的人,都去许都投了曹操,我看哪,用不了多久,天下必有一番新气象。仲达,你说呢?”
“崔先生不是说‘谋定而后动’吗?现在的局势,我还说不好,静观其变,再做定论。”
这时司马朗放声大笑,仿佛被人挠到了胳肢窝。司马懿奇怪地看着自己的大哥,司马朗一向沉稳,似这般大笑,极为少见,这是怎么了?
“你一说起‘谋定而后动’,我就想起季珪那张脸来,哈哈——”
司马懿没觉得有什么可笑的地方,倒是很感谢崔琰有意无意地又教了他一课。
崔琰问起周齐的事,司马懿回答说因是同门,不忍先发,且他认为,周齐只是不了解自己才有所误会,因为这个而心有不快拳脚相加,器量未免太小了。
崔琰由此引出他对司马懿那番话的不同看法,语重心长地对他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