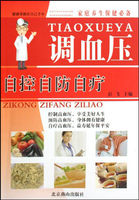在我恢复意识时,只觉得反胃、恶心,干呕,然后想哭。
在泪水溼润了眼睛后,我缓缓撑开眼皮。
我站在一座岌岌可危的小石台上,就像电视游乐器那种很贱想摔死人的关卡──两枚圆锥体尖头对尖头地顶着,只要没掌握到中心点保持平衡,我就会咕咚摔下去呜呼哀哉,而且没有下一条生命重新挑战那样。
不过情况又有点不太一样。
我虽然站在石柱圆锥体上,我的头发和衣服,却不停地向上飘着,害我很别扭地要不停压住白色女鬼装的衣服,以免自己在这个鬼地方曝光。
就算是在鬼地方,我也不想变成曝露狂或是走光的高中生啊!
过了好一阵子,我才反应过来为什么头发跟衣服会一直往上飘……
我现在在一片红红的水里,这个地方的引力重力好像不能用人间界的常理去推断,我实在分不清楚到底哪里是这片红色海水的海面,哪边是海底。
耳边不停传来痛苦的呻吟声与哀嚎声,那些声音都是地狱里众生受苦的呼喊。
我一点都不难过,但还是泪流不止。
脑中跑过的思绪只有「为什么我在水里可以呼吸」、「为什么我在光线根本透不进来的水里可以睁开眼睛,看清楚一切」?
我到底在哪里?是在梦境里面吗?为什么周遭的场景那么熟悉,就和我这几个月来梦到的梦那么类似?即使还是有一点点的不同……
这里不臭,我也感受不到水的温度,就好像这些血水只是看得到而已,但它实际上并不存在,如同幻灯片之类的投射。还是它其实存在,只是我的感觉神经和大脑已经坏死了,什么都察觉不出来?
还是,我已经死了?现在在血海里站着的,是我的灵魂?
我低头看看下方,隐约间似乎有好多黑色模糊的影子闪过来闪过去,偶尔还会有金光反射下来,如果这样做判断的话,我脚底下的区域才是血海海面吧?
那么上面呢?
我仰起头,看着顶端──
那里彷彿是另一片血海,一片藏在在血海之中的另一片血海,它就像冰块一样凝固的红色冰海,而且一点都不透明,不像我记忆中的任何结冰物那样晶莹。
有两个小小的人影被綑绑在那个固体冰海的外面,其中一个留着短发,另一个是卷卷的长发,他们看起来就像沉睡中的小孩子一样,垂着头,一点反应也没有。
「偎偎?摧摧?」我喊出声来,双脚蹬着所踩的圆锥平台,石平台立刻自顾自地晃了起来,就像我那千篇一律的梦一样,但是我并没有如同梦里那般摔下去,反而自在地在血海里游着。
我轻轻地划手,慢慢地打水,在这个不用浮到海面换气的怪地方,朝着被绑住的骨偎与骨摧前进。
「真的是你们!」我来到双胞胎的身边,轻轻地抚摸他们的脸,他们的体温冰到彷彿不是活着的。我摇晃他们的肩膀,双胞胎却只像玩偶般微微晃动,一点反应也没有。
他们还活着吗?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试着徒手拉扯那把双胞胎绑住,并固定在固体血海上的,很像黑色封箱胶带的玩意儿,但那玩意儿的强轫度远远超过封箱胶袋,不管我再怎么用力地拉、用力地扯,甚至用牙齿去咬,那黑色东西还是无动于衷。
我稍微退离双胞胎,飘浮在血海中,姿势很丑地在女鬼装里随便掏着,可是刚才岳霜轮给我的符纸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
「摧摧?」我边大声喊边拍着短发骨摧的脸,然后改拍他姊姊,「偎偎?」
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不管是泡在血海里那么久的骨偎跟骨摧,还是海面上大打出手的恶鬼与鬼差。我用力抓着脑袋,绞尽脑汁地想办法,并看看四周有没有什么尖锐的东西可以割断那个黑色玩意儿。
「啊!」
我惊呼一声,赶紧拆下头发上祭泠送给我的酒红色鲨鱼夹,用力捏着弹簧,让虽然被磨平过,却仍保有一点尖尖利齿的部份,慢慢地割着那个黑胶带。
但是割了老半天,我的手臂都已经发痠了,那个胶带才冒出零点零零零一公厘般的破损。
这招行不通,必须找更有效的办法……
我的眼睛飘向面前的那块冰海,我忍不住伸手摸了摸。
它的触感就跟大冰块一样,说不定我可以敲下一大块,弄成类似冰锥造型的东西?
我一边这样想一边拿起发夹敲那块固体冰海,幸好冰海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方便雕琢,而且剥落下来的小碎片硬度已经相当够了──这又是一个不符合人间界常理的东西──我静静地敲着,在冰海上敲出一个尖锐的三角形后,用尽全身力气想把它凿下来。
「啊!」
完美的冰锥突然地掉下来,并且莫名其妙地往上飘浮。
海平面明明就在下面啊!你这块冰锥干嘛往海底飘去啊!
我握着发夹,赶紧划水追着越飘越快的冰锥……幸好在血海里根本感觉不到阻力,游起泳来轻松无比,我努力伸长双手,一把将冰锥抓了回来,然后转弯打算游回双胞胎的身边……
右手边那块巨大的深红色冰海,却再一次吸引了我的注意。
暗沉的固体血海中,隐隐约约地看得见一道呈现大字形的人影。
我瞪大眼睛,身体不由自主地朝冰海靠近,脸几乎要贴在上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