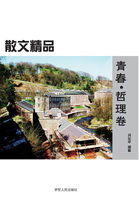开会的时间快到了。群众来得更多,把季子庙拥挤得紧紧地。周俊驼着背,满头是汗,一来一回的在主席台上跨着他的长脚踱着。他失悔这个改选大会召集得太快了,一切,一切都没有准备好,在上层统一战线方面,他如果单纯的给予杜荣秀严厉的打击,这有什么意思呢?结果杜荣秀给打垮下来之后,又是第二个杜荣秀起来代替了他,那么他就只能够在这个小派别的纷争中可怜地尽了锤子的作用。在下层群众方面,他们是起来了,可是也只是到会场里来玩一玩,看一看,在他们的眼中,周俊还不过是一个特殊的、超等的、新鲜有趣的人物吧了。
“现在好了,九里来了一个‘有权力的人’,……”
“他会拿出主张来的。”
“杜荣秀哪里去呢,这混蛋,……”
“要请他出面才对呀!”
群众平静地很能够守秩序似的,然而非常严重地保持着缄默,虽然他们之间还免不了要交头接耳。他们仿佛在作着一种欣喜的等待,他们决不使自己发生任何骚乱。在季子庙的门口徘徊着的人,兴奋地、趾高气扬地走到南街,走到东街,又回到季子庙来,带来了更多的人,把季子庙拥挤得更紧了。
他们听到说,那“有权力的人”是专为解除九里市民的痛苦而来的。
……九里的市民处在从宝堰方面开出的日本兵直接的威胁底下,而又为那些维持治安作借口,实则盘剥、抢劫、不务正业、蛆群一样生活着的人们所穿蚀。这些人把持着地方的政权和武装,自成为一个法庭,在自己的家里附设牢监,他们压迫市民,随意的把一个人拘捕,给他镣铐或者更重的蹂躏。同时他们彼此也互相弄鬼,……现在好了,九里来了一个“有权力的人”。这权力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他要对所有的混蛋执行一种惩罚,令人们欢快、满足,从而便于他自己重又无忧无虑的走进茶馆,走进澡堂,把日本人的杀戮,汉奸亲日派的横行,绅士流氓的盘剥、抢劫摆在脑后而置之不闻不问。
群众厌恶抗敌会,厌恶青年团体,——因为他们厌恶与这些抗敌会并存的许多穿蚀人民的混蛋。
在南街的一间食物馆的门口,有一个市民殴打一个青年抗敌会的会员,这就是黄荣新的哥哥,那冒失鬼,他殴打和黄荣新一道走的那个小家伙,黄荣新的友人。
那饭馆老板唱着歌,张着阔大的肩膀,把那小家伙撞倒在地上,而且野蛮地踢了他一腿。
饭馆老板昏蒙地眨着红肿的双眼,两手交叉在胸口,镇静地看着那小家伙从地上爬起来,而且等候着当他爬起来之后又要做些什么事情,同时唾骂着黄荣新:
“哦,看你这样子,快当理事长了,人家会选举你的,你这个不要面孔的东西!”
黄荣新狡猾地很快地溜到别的地方去了,可是他带来了好些个自卫队。
自卫队严重地把饭馆老板抓住了,反剪了他的两手,用鞭子鞭破他的脸孔。
黄荣新对着自卫队这样说:“你们把他带到杜荣秀先生那边去吧,杜荣秀先生今天手里还有权力,我是拥护他的。你们告诉他,这是黄荣新的兄弟,一个讨厌的疯鬼,你们要把他监禁,要把他吊在脊梁上,都可以的。”
另一个市民夺下了自卫队的步枪,而且用斧头砍坏了被缴械的自卫队的手。别的自卫队开枪了,赶走了那夺枪的市民。在纷乱中,有三颗子弹一同射中了饭馆老板的头部,整个的脑袋完全炸得粉碎。
群众骚乱起来了。
有企图的人在人群中大声地叫着“日本兵!日本兵!
……”
“不要乱跑,……同志们,静下来,要注意汉奸的捣乱!”
只有周俊一个人叫出这样的单调、生硬的语句,而且他的声音是那样微弱,谁也没有听见他。
庞大的堆叠的人群从季子庙崩陷下来,整个的会场完全陷于可怕的纷扰。从季子庙崩陷下来的人群向着东街,向着南街,小孩子和女人作着惨叫,油团子的油锅、糖果摊,……被推倒下来了,野菜、荸荠、蚕豆、鲫鱼和喂喂,在那坚实的石板上跟着人的飞奔的脚步在滚动,巷子里从大呼大喊迅速地变成了死的寂静,由于被践踏而受伤的人们的呼喊声也停止了。整个的九里镇完全在一种纷乱、愚昧、不能冲洗的恶浊中屈服地低下头来。
三周俊,那中学生在九里的短短期间的工作完全宣告了失败,他最少已经是劳而无获。他得到了什么呢?在九里那个晕黄色的池塘里,他不过天真地投下一个石块,鲁莽地、毫不经心地叫那池塘里的水翻腾了一下吧了。
但是郭元龙不能没有责任。
郭元龙不召集开会,由于对周俊怀着敌意和轻视,他是采取放任和不管的态度,他完全放弃了对周俊的领导。
另一边,他自己却弄出了许多的名堂来。
没有战争,就没有了他的事;只要日本人不来,他就空着。
他集中精神去弄表,弄手枪,弄马,……宝堰的维持会长突然不送情报来了,把关系弄断了。
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郭元龙同志没注意他的环境,要他买东西……常备队被洗刷的分队长成德铭,那个狡猾卑劣的家伙,送给郭元龙一对黑皮鞋,而且是已经穿底的、破旧的。郭元龙老老实实收下,得意洋洋的穿了起来。在延陵难民救济委员会的门口,穿着皮鞋走过去。成德铭那个坏蛋以及他的徒弟们,做了郭元龙很好的从属。
九里抗敌自卫会被杜荣秀那个鸦片烟鬼把持着,整日里不做别的,只借新四军的名义在街上乱抽捐税;但是有一支卜克手枪送给了郭元龙,郭元龙为了答谢他,用一种永远不能打破的沉默掩护着他。当改选大会的那一天,杜荣秀假说有病,实则为了逃避责任,为了捣鬼,他从九里走到延陵来了,在郭元龙的房间里躲藏着。
周俊垂头丧气的从九里回到延陵来了。他要郭元龙召集开会。郭元龙回答他:“这不关你的事。”
“为什么不关我的事呢?”
“这是一种秘密,你最好不要去过问。”
“哦!这是工作委员会的秘密吗?”
郭元龙检查周俊的入党登记表,决断地说:
“同志,请不要发脾气吧,你只有六个月的党龄,还没有资格参加工委。”
周俊问他看过了司令员的信没有,郭元龙一句话完全加以否认。
这天下午,周俊又回到司令部来,要求司令员解决他们的问题。
司令员立即派总支委书记和他们一道回到延陵,向郭元龙开展斗争。
郭元龙变得和善得多了,面孔也没有怒容,深陷的眼睛狡猾地转动着,仿佛很容易陪人家作一个笑脸,跑起来一拐一拐的,好像下了决心,抛绝了那些终久要引起人家攻击的事,既然抛绝了,也就没有什么别的牵挂了的样子。看到周俊的时候,很客气的点着头。不过这不是说他已经没有了骄傲,他正在时刻的给周俊警示着:
“请不要误会吧,我们共产党员是有礼貌的,可是这礼貌主要的是对从长远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同志,而不是对你,……”
晚上,和郭元龙作了个别谈话之后,总支委书记好像把一件事情处理完妥了似的轻松地说:
“怎么样,周俊同志,林纪勋同志,是不是要开一个会呢?我已经和郭元龙同志谈过,郭元龙同志完全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接受了党对他的批评。”
“这样说,是不是事情就算完了?”
林纪勋同志提出这样的问题。
总支书记一面看了看周俊,征求周俊的意见,一面开始作着解释。他说话很慢,北方人的牙音很重,语调拉得很长,总是在很确定、很决断的语句底下接上了疑问号。
但是他并没有答复林纪勋刚才提出的问题。
林纪勋、周俊一致提议用会议的形式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总支委书记同意了他们的提议。
郭元龙穿着自制的中央苏区时代红军的军服,双手插在衣袋里,挺着胸脯,腰带束得很紧,他不要坐凳子,喜欢在地板上一步一步的走,回转头,又走,把他的黑皮鞋的声响掩盖了总支委书记关于这会议内容的说明。
他第一个发表意见。
他首先说明自己在延陵地区工作了三个月之后,已经引起了敌人和汉奸的注意,因而他现在所住的房子是一个有着前后门的房子。接着他分析溧武路以北整个地区的敌情,连带说明了他在延陵的工作计划,关于常备队的行政工作的建立和反游击主义习气的斗争也说了。以后呢,他告诉了周俊和林纪勋目前的工作方针,顺便教训了他们一顿。
而总支委书记的关于这个会议内容的说明,在他的黑皮鞋的激昂的音响下已经变成了一点影子也没有。
“还有呢?你对他们两位的意见呢?”总支委书记问。
郭元龙的话一讲完,就坐下来,可是他又觉得在地上一步一步的走要来得好些,当大家沉默着的当儿,就让他的黑皮鞋声轰然地响着。
“有什么意见呢?这就是我的意见。”
“既然没有意见,那么就请你对自己执行自我批评吧!”总支委书记说。
郭元龙突然停了脚,凶恶地、忿怒地禁止似的说:
“什么?自我批评?是不是要我对他们两个承认错误?”
“不,是对组织,并不是对他们。”
“那么首先应该由他们执行自我批评,周俊同志你说吧,思想斗争是站在教育同志的立场上,而不是攻击一个同志,但是你不是教育而是攻击!你反对负责同志的领导!在统一战线中你做了人家的尾巴,你联合青红帮头子黄南青来攻击我!你和林纪勋同志进行小团结!”
镇静些,准备着斗争吧,为了做一个共产党员!当郭元龙雷电交加的强烈地发扬火力的时候,周俊这样对自己鼓勇着。他时常对林纪勋说:“痛苦的时候,就望着列宁和那金黄色的星!”但是他开始纷乱了,脑子胀得简直要炸裂开来,他愤恨郭元龙,像愤恨一个仇敌,他觉得自己在理论上并不是不能够把郭元龙打垮下来,但是郭元龙的骄傲把他整个的否定着。他想到好像自己这样的人是不能和郭元龙有斗争历史的同志相比拟的,这时候他就失却了斗争的勇气。郭元龙的凶恶的声音在他的耳朵边一轰过,他就慢慢的软弱下来,至于像小孩子似的要求着哭喊一场,……他坚定地、矜持地回答郭元龙,指出郭元龙骄傲,看不起新同志,对工作不负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郭元龙沉默地听着,眼睛更加深陷下去。他倚着桌子,泰然地、神采焕发地把上身微向前伸,用两只指头敲着桌子,一面计算着周俊说出的字句,一面表示自己接受或反应的程度。
当周俊在统一战线的问题上作着申辩的时候,郭元龙插嘴说:“这是尾巴呵!同志!你知道么,这是右倾机会主义——老牌的尾巴主义!”
“不!这是毁谤,这是诬蔑,这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郭元龙同志你说吧:你的表呢?你的卜克手枪呢?还有你的黑皮鞋?这些是从哪里来的呢?都是统一战线的成绩么?”
周俊逐渐的镇静起来,他已经能够在发言中整理自己的材料,而且开始用诉苦的音调盘问着郭元龙。
郭元龙暴跳起来,他咆哮着,甚至野蛮地推倒身边的桌子。他否认这个会议的意义,挺着胸脯,踏着阔步,头也不回的走他的去了。
四元龙、周俊、纪勋三同志,你们的“斗争”已经陷在无原则的纠纷泥坑中,现在决定你们停止这个“斗争”,对于你们暂时不作任何结论,因为在组织上,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都不能从这斗争中得到什么益处,而且现在没有时间可以让我们的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去进行有趣的辩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鄙弃这种胡闹的行为,立即丢开这种行为,但是你们必须把工作紧张起来,一切服从工作的利益,也就是服从党的利益。工作是太重要了,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用一切的力量去对付它吧!要注意着在那一处工作存着弱点,党就要在那一处遭到损害。日本人的扫荡就迫在眉睫,工作的成功失败要考验着全军、全党,同时考验着每一个人。战斗的胜利,将根据工作上努力的程度……决定寄托于那一种人的身上……一个大雪纷飞的早上,郭元龙的房子给许多的人:常备队、彪塘和柳茹的抗敌自卫队,以及眭巷里的冬防队的同志们挤拥着,快要把房子挤裂了。人们尽力的挤,没命的挤,也不怕把队伍弄乱,因为你是彪塘人,我是柳茹人,不管乱到怎样,他们还可以彼此区分出来。挤着,望着郭元龙住的那房子,都拉长着颈脖,雪花当着脸飘下来,只是用手一抹,鼻子都冻红了,张开着的嘴巴喷着白气。穿军服的,没有弄到军服的,穿长袍子戴军帽子打绑腿的。——郭元龙住的那房子的门口,在无数惶然、焦急、带着无限忧愁的视线的迫射之下快要冒火了,……都拉长着颈脖,都还是尽力的、没命的挤。从那门口出来的人,又茫然地望着那些在挤着的人,他们满足了,却还是茫然,于是随着人的波浪向两边分开,走向北街,走向南街,南街,北街都挤得满满的了。
郭元龙把司令员的信抓在手里,看了看,又把深陷的眼睛向着人群。
分队长彭杰,那“老木匠”,还是穿着日本大衣,把腰束得很紧,这日本大衣增加了他不少的威武,这是他亲自从日本人身上剥下来的。……他爱惜自己,爱惜战士,更爱惜郭元龙。他站在郭元龙的身边,只要郭元龙怎么说,他就服从,而且立即把郭元龙的意思用来代替自己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