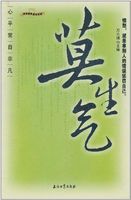王老师不是本地人。他来到这个小镇时只有十九岁,说一口很纯正的普通话。镇里人都叫他“王蛮子”。
他是“戴着帽儿”下来的。据说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下放到这里是来“改造”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这类事司空见惯。
镇里人并不觉得有什么,只是听不惯他的口音,就觉得别扭。背地里说起他,就道:“那个王蛮子……”王老师也觉得别扭。为了能“打成一片”,他就努力地学当地土话。
谁说了一句很鲜的土话,他就在小笔记本上记下,还注上拼音。
镇里有个鞋匠,当地的俏皮话说得很绝。王老师是在一次补鞋时认识他的。一来二往,俩人就成了“莫逆之交”。有事没事,王老师就往鞋匠那儿跑。跑得勤了,就认得了鞋匠的女儿大萃。大萃好听他说普通话,他一来,大萃就不远不近地站着,或搬只小板凳往近旁一坐。听他说话,就捂着嘴叽叽地笑……
后来,王老师被摘了帽儿,到镇小学教书。镇小学离鞋匠的住处不远,大萃就常给他送饭。王老师那时的本地土话已经说得很地道,学生们都听得懂。不经意冒出一句普通话,调皮的学生就会在底下捏着鼻子阴声怪调地学他: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这一学,课堂里就涨满了笑声。
大萃不知怎地知晓了这件事。待放了学,在院子里揪住那调皮学生乱凿。那学生喊着求饶,用书包遮住头飞一般跑了。
不要打他,不要打他。王老师劝大萃。
俺偏不,俺偏不!大萃道。你不能打,俺能打!
这以后,没有学生再敢和王老师“唱二簧”。王老师也很注意的,课堂上从不漏半点“蛮音”。
不几个月,大萃成了王老师的新娘。学校没有地方住,王老师就搬到鞋匠那儿。有了妻子有了家,王老师过得还是蛮舒坦的。没事的时候,他和鞋匠海天云地闲扯。一盘花生米,两根腌黄瓜,翁婿俩能下去八两老白干。
王老师三十出头才有孩子,是个干金,王老师就叫她“小萃”。小萃刚咿呀学语,大萃就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教她:爸爸——妈妈——啊——啊——老鞋匠在一旁听了直撇嘴。见老头儿这般,大萃就对王老师说:你来教,你的话好听……
王老师笑了:你比俺还强哩……
一晃眼,小萃就长大了。先在镇里上完了初中,又到县里念完了高中,接着又考上了师范学院。
小萃一走,王老师心里就空落落的,每晚由大萃陪着喝两杯——老鞋匠已不能喝酒,他瘫在床上几年了。
寒假时,小萃回来了,一张嘴竟是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王老师很不安,说:你说咱这地方的话不中吗?
小萃到外爷屋里,对老人说:外爷,您老好啊!
老鞋匠将眼皮撑开,瞧瞧外孙女,问王老师:这是谁呀,说话恁蛮!
王老师和小萃就笑。
吃晚饭时,酒又摆上。小萃从牛津包里掏出两盒高级点心。
爸,这是我的老师、您的学生捎给您的礼物。
王老师一愣:谁?
小萃就把目光移到大萃脸上。妈,就是你凿过的那个……现在已是讲师。
是二秧子呀!出息啦,出息啦!
他还记得您。他说,就是冲你那一顿拳头,也得学好……
王老师愣愣地听着,双手来回摆弄那两盒点心。等大萃娘儿俩把话头闸住,他就端起酒杯猛喝……
这一夜王老师第一次喝醉了,不住嘴地说了半宿普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