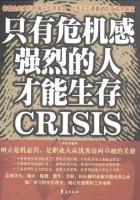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时代性和实践性的本质,调整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叙述方式
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述体系中,科学技术的功能主要是在生产力范围内阐释的。马克思于1859年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著名公式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马克思在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叙述时,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处于起始阶段,有关生产、增长、地球资源、人口负载和发展极限等问题,还完全处于被掩蔽的状态。在马克思的叙述中只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普遍规律,而没有涉及生态学和未来学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规定的,其中包括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和它在技术上的应用发展水平,生产过程的社会联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关系”。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显然是把科学技术的功能置于生产力发挥作用范围之内的。其理论前设是生产力始终起着进步的革命的作用,科学技术也始终是一种进步的革命的力量。在他看来,科学技术甚至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他在1847年的《哲学贫困》一书中写道:“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义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的第142页)然而,马克思也意识到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必然会形成的负面作用。他在研究中发现,在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中,机器已经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而工人则成了机器的附庸。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464、563页中已经暗示人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科学技术完全有可能蜕变为支配和压抑劳动者的统治形式。“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侵吞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变得空虚了的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庸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用机器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事实上晚年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的批判也始终包含着对现代科学各种负面因素的高度警惕,似乎包含着科学技术的某种意识形态潜能。然而马克思这些论述并未引起他的后继们的高度重视,习惯于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抽象地分离并对立起来。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只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把科学技术首先是历史有力扛杆的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372、375页)恩格斯主要是从正面价值的角度理解转述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及其应用的理论,他并没有充分注意到马克思对科学技术方面价值存在所发出的预警。在这种阐释和叙述方式的影响下,在这以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的著作中,对生产力组成部分的科学技术的进步的革命作用的见解几乎已成定见。于是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共产国际的领袖们,对科学技术的革命作用教条式的过度诠释,形成了科学技术本身似乎成为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重要的革命力量。在这样的阐释和叙述方式中,把科学技术和意识形态处于对立的绝缘状态,科学技术不但成为绝对的进步性和革命性的标志,也成了绝对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标志。由于教条主义束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许多方面落后于时代的进步,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甚至出现危机,迫切需要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以解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新遇到的实际问题为中心,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更鲜明地呈现出经济全球化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我革命。
在正确解读马克思文本的基础上,下力气克服新老教条主义的束缚,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和中国传统哲学丰富的思想资源,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时代性和实践性的本质,调整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叙述方式。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证明,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发展先进生产力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功能。甚至意识形态基本的核心组成部分,比起老式的意识形态显得更难以抗拒和更为宽泛。所以先进的生产力不一定决定先进的生产关系,只有以人为本的先进生产力决定先进的生产关系,先进的经济基础决定先进的上层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