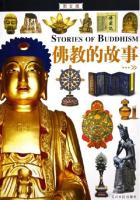天竺国语与中国语言不同,外文的佛典翻译成中文必然会受到一些限制,有时会缀华语而赋新义,如“真如”、“无明”、“法界”、“众生”、“因缘”等;另一方面外文有自己的语法词汇,为了忠实于原文,并且中文里面也找不到相对应的词,不得不保留一些异于中文的风格,或存梵音而用其音译,如“般若”、“瑜伽”、“禅那”、“刹那”等。汉魏六朝佛典翻译中吸收和创造了大量佛教词汇,为中国国语系统中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使翻译经典呈现出不同于中土的风格。从语法上看,梁启超先生指出:
吾辈读佛典,无论何人,初展卷必生一异感,觉其文体与他书迥然殊异。其最显著者:(一)普通文章中所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字,佛典殆一概不用(除支谦流之译本);(二)既不用骈文家之绮词俪句,亦不采用古文家之绳墨格调;(三)倒装句法极多;(四)提契句法极多;(五)一句中或一段落中含解释语;(六)多复牒前文语;(七)有连缀十余字乃至数十字而成之名词——一名词中,含形容格的名词无数;(八)同格的词语,铺排叙列,动至数十;(九)一篇之中,散文诗歌交错;(十)其诗歌之译本为无韵的。质言之,则外来语调之色彩甚浓厚,若与吾辈本来之“文学眼”不相习,而寻玩稍近,自感一种调和之美。
佛典翻译为中文,要求多数人能够理解,这就不能不通俗,因而不宜于完全用典雅的古文或藻丽的骈体文写。再一方面,佛教教义主要是要取得上层人士的接受和重视,因此译文又不能过于通俗,又要适当采用当时雅语的表达方式。这样,佛典就创造出一种雅俗之间的、调和中外的,既平实简练又“有天然西域之语趣”的特殊风格。而此种风格的形成实有赖于罗什及其门下诸人之功。六朝时期的汉译佛典,为数众多,单就艺术形式而言,其对六朝诗歌、志怪小说应该是有一定程度的刺激及影响。兹将六朝汉译偈颂佛典的文学手法概括为以下几种:
一、特殊句式的开展
(一)齐散结合的新形态
汉译偈颂可概分为“祇夜”与“伽陀”,祇夜是以韵语的性质重复宣说长行所言之教义,称之为重颂。长行为散文,祇夜为韵文,二者可说是一整体,这种齐散结合的形式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是首开先例,不仅丰富了既有的文体结构,亦影响了后代文学。此类齐散结合的形式,于六朝的汉译佛经中,数量众多,兹举二例于下,以见一斑。
姚秦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中,有一段经文述说舍利弗请求佛陀开示甚深微妙法之经过,经文中先以长行叙述其事,其后之偈颂复重宣其内容含义,如:
尔时舍利弗重白佛言:“世尊,唯愿说之,唯愿说之,今此会中,如我等比百千万亿,世世已曾从佛受化,如此人等必能敬信,长夜安隐多所饶益。”尔时舍利弗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无上两足尊,愿说第一法,我为佛长子,唯垂分别说,是会无量众,能敬信此法,佛已曾世世,教化如是等,皆一心合掌,欲听受佛语,我等千二百,及余求佛者,愿为此众故,唯垂分别说,是等闻此法,则生大欢喜。
由上例可看到偈颂的内容是对长行内容的重复,偈颂等于是重宣长行的含义;长行部分是以散文出之,而偈颂部分就明显地是采用齐言的诗歌形式,但这种齐言的部分并未押韵,所以,它和真正的诗歌又不尽相同。
这种长行与偈颂相间的形式对后来中国文学式样的形成有极大影响和推动作用,陈寅恪先生说:“佛典制裁长行与偈颂相间,演说经义自然仿效之,故为散文与诗歌互用之体。后世衍变既久,其散文中偶杂以诗歌者,遂成今日章回体小说。其保存原式,仍用散文诗歌合体者,则为今日之弹词。”
(二)长篇齐言的展现
在中国诗歌中,尤其是在唐前古体诗,篇幅逾百句者并不多见。但在汉译偈颂中,长达几百句甚至上千句的偈颂却有许多。例如《法句经》、《佛五百弟子自说本起经》、《文殊师利发愿经》、《佛所行赞》等经,全经皆以偈颂形式呈现,毫无长行穿杂其间,少则逾百句,多则近万句。
再例如后汉支谶所译《般舟三昧经》,其中有七言偈颂,长至188句;吴国支谦所译《菩萨本业经》,亦有一首四言偈颂,句数多达540句;西晋竺法护所译《度世品经》,更有长达888句的五言偈颂,而其《贤劫经》中,亦有三言偈颂,长达1052句;而东晋佛陀跋陀罗所译《达摩多罗禅经》,亦有长达644句的五言偈颂;姚秦鸠摩罗什所译《十住经》中,亦有五言偈颂360句;另外,北魏菩提流支所译《入楞伽经》中,亦有长达1858句的五言偈颂。由以上所举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各个时代均有长篇偈颂的翻译,无论其原典如何,然汉译之后所呈现的偈颂,并不仅止于四句一颂的基本形式,无论偈颂为几言,皆不乏篇幅较长的表现形式,此种形式或对于唐代以来长篇古体的形成有借鉴作用。
二、译文的修辞手法
(一)譬喻
佛经中譬喻类故事极多,《譬喻经》、《百喻经》就是一些譬喻故事集。譬喻系佛门权巧方便的说法手段之一,其特点在于借大家都熟知的事物来托此比彼,将佛教对宇宙人生世相的看法,化为生动的譬喻,藉由这些譬喻性的言辞或故事,引导信众理解抽象难懂的法理。印度高僧顺贤《顺正理论》曰:“言譬喻者,为令晓悟所说宗义,广引多门,比例开示。”姚秦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卷二载:“诸佛世尊,以种种因缘,譬喻言辞,方便说法,皆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是诸所说皆为化菩萨故……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我们前面讲偈颂中所引用的一些偈子就多含有譬喻,这些偈子中常用“犹”、“如”、“若”等字眼。此处举西晋竺法护所译《修行地道经》为例:
譬如明镜及虚空,霖雨已除日晴朗,有净眼人住高山,从上视下无不见,又观城郭及国邑。其修行者亦如是,睹见世间及禽兽,地狱恶鬼众生处。
此处以各种譬喻言辞说明修道者的证得神通,将修行者证得天眼,悉见诸方三恶处的情形比作仿佛明眼人住于山顶,由高处观视山下城郭郡县、聚落人民皆清楚的情形。
在《法句经》中,也存在大量采用比喻修辞手法的经文,如:
若人寿百岁,邪学志不善。不如生一日,精进受正法。觉能舍三恶,以药消众毒。健夫度生死,如蛇脱故皮。
这里的经文运用了我们熟知的事物作比喻,十分生动而深刻地说明了人生当接受正法,改恶从善的道理,实际上这也是一首含义深刻的哲理诗。汉译佛典中的譬喻不外乎援引生动事相启发对方思绪,喻体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一些演述物语的性质,尽管还称不上独立存在的叙事佳构,但文学价值却颇为人称道。据《北本涅槃经》卷二十九《狮子吼菩萨品》记载,譬喻依方法之不同可分为八种,有顺喻、逆喻、现喻、非喻、先喻、后喻、先后喻、遍喻。见之于诸经中常见的譬喻有“盲龟浮木喻”、“三兽渡河喻”等,而最著名的莫过于“法华七喻”了,它是《法华经》中七个比喻的美称。其中“火宅喻”讲一位长者(富商)家中着火,三个儿子只顾在着火的房子里玩耍而不肯出来,为让他们走出来,长者假说外面有好玩的羊、鹿、牛三车。孩子们听说有车就争先恐后地走出来。长者非常高兴,便给他们每人一辆七宝牛车。“火宅喻”的含义是引导人通向大乘佛法。“穷子喻”讲一少小离家的穷子,若干年后乞食于长者门前,长者得知为己子,乃遣家人追回,然其子恐惧而逃。长者遂用计,雇之为佣人,并逐渐重用之,最后始告以实情,且给与万贯家财。故事中之穷子比喻二乘之人,家财则比喻大乘之教;谓二乘之人无大乘功德之法财,犹如穷子之缺乏衣食资具。其他还有“药草喻”、“化城喻”、“衣珠喻”、“医子喻”、“髻珠喻”等。
(二)夸张
夸张也是佛经中常用的文学手法,佛经中对地狱、净土的描写,对天神菩萨神通的刻画极尽夸诞之态,也构成了佛经文学一大特色。佛经说法绵亘数卷,空间上言大则极如须弥,言小则极如芥子;时间上言大则曰劫、百千亿劫,言小则说一刹那。兹看一下《菩萨璎珞本业经》中对“磐石劫”的描述:
譬如一里二里乃至十里石,方广亦然,以天衣重三铢,人中日月岁数三年一拂,此石乃尽,名一小劫。若一里二里乃至四十里石,亦名小劫。又八十里石,以梵天衣重三铢,梵天日月岁数三年一拂,此石乃尽,名为中劫。又八百里石,以净居天衣重三铢,净居天日月岁数三年一拂,此石乃尽,故名一大阿僧祇劫。
再如对神通的描述,竺法护所译《普曜经》中的偈子:
手执大白象,已死身至重,掷弃于城外,离堑极大远。
这首偈子写菩萨见到被调达捏死的白象,因见象身硕大,臭烂熏城,遂发慈悲心以右手掷置于城外。以手抛大白象的轻而易举,夸饰出菩萨的威神之力。再如《维摩诘经》维摩诘居士示疾说法关于神通的描写:
尔时长者维摩诘心念,今文殊师利与大众俱来,即以神力空其室内,除去所有及诸侍者,唯置一床,以疾而卧。文殊师利即入其室,见其室空,无诸所有,独寝一床……
这一段经文描述了当文殊师利前往问疾时,维摩诘示现神通把自己住所变成一丈见方的空屋子,里面除了床之外无有一物,显示了诸法性空之理。又现神通从须弥灯王如来处借来高广狮子座,座高万丈。这一段描写夸张地表现出维摩诘的神通。与前偈一毛孔中现无量海的描写异曲同工。
再如对不可思议境界的描绘,《华严经·入法界品》中:
一一毛孔中,普现最胜海;佛处如来座,菩萨众围绕。
一一毛孔中,无量诸佛海;道场处华座,转净妙法轮。
一一毛孔中,一切刹尘等;最胜跏趺坐,演说普贤行。
其实夸张在中国文学中也是文学描写的基本手法,《逍遥游》中的大鹏即是著名的例子。《文心雕龙·通变》中说:“夫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自兹厥后,循环相因。”然而中国文学的夸张却多侧重现实描写,很少超时空、超现实的幻想。而佛经文学作为宗教文学,本着对现实经验世界的否定,对超验世界表现得更为关注。这种超验世界有两个方面:一是高于现实的,即理想的世界;一是低于现实的,即非理想的世界。前者表现为佛经中对天界的描绘,天界共有三十三天,其中欲界六天,色界二十三天,无色界七天。诸天一个比一个高,居民寿命一个比一个长,物质财产极为丰富。三十三天有三十三城,城中有城,大城围小城,重重无尽。后者则表现为对地狱的描绘,佛经中关于地狱的说法有多种,大地狱有十八地狱,三十六地狱,六十四地狱等说法,小地狱更是不计其数,据说有八万四千个。大小地狱所处的空间位置亦不相同。其中最为大家熟悉的是“阿鼻地狱”,而其中又包括了寒地狱、热地狱、刀轮地狱、剑轮地狱等种种名目。佛教从佛法无边的理念出发,把佛教竭力推向浩邈的宇宙之中,构建了凡人难以想象的宇宙空间观。诚如《后汉书》作者范晔在《西域论传》中说:“然好大不惊,奇谲无已,虽邹衍谈天之辩,庄周蜗角之论,尚未足以概其万一。”在时间观念上,佛教从缘起论和因果论出发,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于世俗经验的概念。从宏观上说,佛教的时间概念集中到“劫”这一术语,有小中大之分。一小劫约为1600万年,一中劫约为3.2亿年,一大劫约为12.8亿年。从微观上讲,佛教的时间概念集中到“刹那”,与“劫”相对,意为“极短的时间”,约为0.013秒。佛教的夸张手法集中表现出了想象的生动性和想象的奇妙性。前者表现在对维摩等形象的刻画上,各尽其态。后者表现在对稀奇境界的描绘上,新奇富丽,富于变化。
(三)象征
佛经中常出现自然意象,常见的有月、莲花等。佛经中有关月的地方很多,如:
《菩提论》:“照见本心,湛然清净,犹如满月,光遍虚空。”
《文殊师利问菩提经》:“初发心如月新生,行道心如月五日,不退转心如月十日,补处心如月十四日,如来智慧如月十五日。”
《发菩提心品》论菩提相“圆满如月轮于胸臆上明朗”。
唐朝沙门善无畏的《禅门要法》中,说禅境之月有三种譬喻:一是自性清净义,离贪欲垢;二是自性清凉义,离瞋恚忽热恼;三是自性光明义,离愚痴黑暗。由此可见佛经中的月主要象征自性的清净圆满。寒山诗:“岩前独静坐,圆月当天耀,万象影现中,一轮本无照。廓然神自清,含虚洞玄妙。因指见其月,月是心枢要”,便是圆满的禅定境界的表达。《心灯录》卷上有一则公案:
僧问曹山(本寂禅师)曰:“朗月当头时如何?”(即证悟到如月光明境界,还应怎样修行)
山曰:“仍是阶下客。”(尚未究竟)
僧曰:“请师接上阶。”(请师父指点迷津)
山曰:“月落时相见。”(不居圣境,指月双泯)
朗月当头象征自性的圆满无欠,但心中若存此种想法则是执于圣境,是尚未究竟,所以曹山以“月落”象征泯除圣境,指导山僧破除执著。
月有时和水结合成“水中月”,其象征意即发生了变化,佛经中“水中月”的例子有:
《大智度论》:“解了诸法,如幻如焰,如水中月。”
《净饭王涅槃经》:“世法无常,如幻如化,如热如焰,如水中月。”
《维摩诘所说经》:“乃至一念不住,诸法皆妄见,如梦中焰,如水中月,如镜中像。”
《金光明经》:“声闻之身,犹如虚空,焰幻响化,如水中月。”
《称扬诸佛功德经》:“为分别一切如梦如水中月幻化之法,用寤众生。”
《月上女经》:“诸三世犹如幻化,亦如阳焰,如水中月。”
《方广大庄严经》:“如水中月,如谷中响,如幻如泡。”
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佛经中常以“水中月”与梦、幻、泡、影、露、电、焰、镜中像、芭蕉心等意象并举,以喻指事物的虚妄不坚。
总之佛经中的自然意象绝少是出于对自然景物本身的描写,而是借自然意象表达深刻的佛教意蕴。
(四)排比
排比在中国文学中是常见修辞手法,然一气之下几十个排比的情况则不常见,这种情况在佛经中则是家常便饭,《妙法莲华经·普门品》中有一偈颂充分展现了排比的句型,兹撷取其中一段于下:
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
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
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
或值怨贼绕,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咸即起慈心。
或遭王难苦,临刑欲寿终,念彼观音力,刀寻段段坏。
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杻械,念彼观音力,释然得解脱。
此段偈颂主要是说明观音菩萨耳根通圆,闻声皆予相救的悲心愿行。偈颂中连用五个“或”字、五个“念彼观音力”,以排比的修辞技巧反复陈说,给人回环杂沓之感,造成一种咒语的效果。再如《佛所行赞》写求道破魔一段,描写魔军之态连用三十多个“或”字:
师子龙象首,及余禽兽类。或一身多头,或面各一目。
或复众多眼,或大腹长身。或羸瘦无腹,或长脚大膝。
……
或夺人生命,或超掷大呼。或奔走相逐,迭自相打害。
或空中旋转,或飞腾树间。或呼叫吼唤,恶声震天地。
饶宗颐先生在《马鸣〈佛所行赞〉与韩愈〈南山诗〉》中指出:“是品描写魔军之异形,千态万状,以迭句句法,连用‘或’字三十余次,乃恍然于昌黎《南山诗》用‘或’字一段,殆由此脱胎而得。”看来此种大规模的排比亦影响了中国诗人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