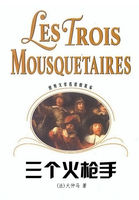星期六,葛兰走出自己的店铺。现在是下午五点半,她想。她接着想她六点整能赶到兴旺菜馆。下午五点,母亲打来电话说,一家人吃饭的地方订到了兴旺菜馆。之后,母亲又说地方是继父的儿子订的。母亲在电话里叮咛:“你桑叔叔的儿子比你大几岁,见面后,你客气一些。”葛兰有意无意地答应着。
葛兰的店铺在永昌路。这个时候的永昌路上人来人往。葛兰的店铺叫零零时装店。零是什么都不是的意思。当时,她是骑着摩托车飙车时想到这个店名的。那是在晚上,她和几个小伙子在还未通车的雁北大桥上飙车,她是飙车中唯一的女性。他们让摩托车在桥上肆意轰鸣。零,她在那个晚上脑子里冒出这个词。接着,这个词又像冒汽泡一样一直往出冒。零零……她在嘴里又念叨这个词。就这样,零零成了她时装店的名字。
兴旺菜馆在农民巷。葛兰没有像往日一样骑摩托车。这个晚上的家庭聚会说不准她会喝酒,所以她没有骑。在永昌路口,她乘上公交车。正是下班时节,公交车因为堵车走走停停。公交车到达农民巷时六点整。
葛兰走进包厢时,母亲和继父桑永胜已经到了。桑永胜是继父的名字,葛兰昨天才从母亲嘴里知道的。
“还是小兰准时。”继父桑永胜说。
葛兰笑了笑。她脱掉外衣。然后,她朝洗手间走去。她要洗洗手。
葛兰从洗手间回来时,包厢里多了一个人。葛兰看着这个人,然后,她呆住。
“这是桑瑞。”母亲指着桑瑞对葛兰说。
葛兰仍呆着。她没有听母亲的介绍。接着,她坐下来。
桑永胜对桑瑞说:“这是小兰,你比她大几岁,她是你的妹妹了。”
桑瑞也发呆。父亲桑永胜说过后,他走向葛兰。葛兰站起来。“你好。”桑瑞向葛兰伸出一只手。
葛兰看着桑瑞,她伸出自己的手与桑瑞的手握了握。
“葛兰以前是我班上的学生。”桑瑞转向他父亲和继母。
桑瑞的父亲和葛兰的母亲有些吃惊。葛兰的母亲说:“怪不得葛兰一见你就发呆,原来你是她老师。”
“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桑瑞说。
“你当班主任时好像从来没有开过家长会,不然我也会见过你。”葛兰的母亲说。
桑瑞笑了笑。他想起来他在北塔中学给葛兰当班主任时的确没有开过家长会,他这样想着坐到自己的座位上。他坐下后看着葛兰。葛兰的脸色有些发白,她目光对着桌上五颜产色的菜。桑瑞又转向站在一旁的服务员,他让服务员将红酒倒在每个人的酒杯里。
桑永胜举起了酒杯,他说:“为一家人聚在一起干一杯。”说着,他和葛兰的母亲碰了一下喝下去。
桑瑞和葛兰都喝了下去。
第二杯酒添上时,桑瑞站起来给他父亲和葛兰母亲各敬了一杯。然后,他端着酒对葛兰说:“咱们也碰一下。”
葛兰站起来与桑瑞碰了一下,然后,她一饮而尽。
“你不一定要喝完。”桑瑞对葛兰说。
葛兰没有说什么。她让服务员添上酒,接着,她像桑瑞一样给每个人敬酒。敬到桑瑞时她双手举着酒杯说:“我知道你离开那个学校了。”
桑瑞笑了笑说:“早就离开了。”桑瑞说着一口喝下。
葛兰慢慢喝下去。
桑瑞的父亲让大家动筷子。四个人共同夹起了菜。葛兰的母亲吃了几口菜后看着桑瑞说:“葛兰给你当学生时肯定给你惹过不少麻烦。”
“她就像一头不安分的小狼,”桑瑞笑着说,“不过,她那时还好,挺聪明。”
葛兰吃着菜。在桑瑞回答母亲的话时她没有任何表情。
“葛兰现在干得不错,自己开时装店。”桑永胜说。
葛兰的母亲笑了笑说:“现在还过得去吧。”她说过这句话后再没有提葛兰过去的事。
到了晚上八点钟,桑瑞的父亲和葛兰的母亲站起来,桑瑞的父亲对桑瑞和葛兰说:“你们再坐一坐,我们先走了。”说着,他们离去。
送走两个长辈,桑瑞和葛兰重新坐下来。瓶中的酒只喝了一半。桑瑞拿起酒瓶给葛兰的杯中添了一些,又给自己的杯中添了一些,他举起酒杯说:“葛兰,和我这个当哥的喝一杯。”
葛兰喝下杯中的酒。她放下酒杯拿起酒瓶给桑瑞倒酒,又给自己倒酒。她说:“我没有想到是你。”
“我也没有想到,”桑瑞说,“我只知道这个家里有一个叫小兰的人,不知道是你。”
葛兰掏出烟递给桑瑞一支,她自己也噙了一支。葛兰掏出打火机点烟时,桑瑞看着她,葛兰点烟的姿势娴熟、自然,她手中的打火机是价钱昂贵的那种。
“你的时装店在哪条街上?”桑瑞点着自己的烟说。
“在永昌路。叫零零时装店。”葛兰吐着烟说。
“我见过那个时装店,好像是专卖那种特别服装的。”桑瑞说。
“专卖几个品牌的衣服。”葛兰说。
“挺不错。”桑瑞说。
葛兰没有说什么。她倒了半杯酒自己咕咕喝下。然后,她又倒了半杯伸向桑瑞:“碰一杯。”
桑瑞看着葛兰,他拿过酒瓶给自己的杯子里添了一些。他举起酒杯跟葛兰伸过来的酒杯碰了一下,然后,他喝着。他还没有喝完时,葛兰已咕咕喝尽。
葛兰又倒酒,她还要跟桑瑞碰,桑瑞没有拒绝。到碰第四杯时,桑瑞没有动酒杯,他看着葛兰说:“是不是要往醉里喝?”
“喝不醉。”葛兰说着咕咕喝下。她没有看桑瑞。
桑瑞沉默下来。一支烟抽完后,他又接着一支。他看着葛兰。葛兰的脸已经有些发红。她的头发散乱起来。
葛兰在喝下第六杯酒后,她双手将散乱的头发向后拢去。随后,她的双手停在脑后,她的脸对着桑瑞:“你是不是一直在恨我?”
“没有,从来没有恨过你。”
葛兰笑了起来。她笑得古怪,而且有些狰狞。“你应该恨我。”她说。
“没有恨过。”桑瑞说。
“你一直是这种虚伪的样子。”葛兰双眼盯着桑瑞说。
桑瑞没有说什么。这时候,他只能以微笑来面对葛兰。
葛兰突然咕咕笑了起来。她将双手从头上放下来,她又倒了一杯酒说:“我不该这么说你,其实,恨不恨都无所谓。”说着,她将杯中的酒仰头灌下去。
桑瑞没有阻止葛兰继续喝酒,他只是看着。
葛兰喝下最后一杯酒将空杯推开。她又点燃一支烟。她向后靠在椅背上,她吐了一口烟后看着桑瑞。接着,她的目光又对着她手中的烟。
桑瑞站了起来。他去洗手间,但他没有说他要干啥去。他朝外走时想刚才葛兰看他的目光,这目光他熟悉。几年前,葛兰就以这种目光看他。在水岸酒吧里他逮住她时她是这种目光。在课堂上,在课堂外的校园里,她也是以这种目光。之后,在那件事发生后,她看他时还是这种目光。这目光是藏在一片冰冷后面的刀和剑,是要扎出某种回应的刀和剑。在洗手间,桑瑞让水不停地冲洗着他的手。水滋滋在流。他对着镜子,镜子里他的一张脸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一张虚伪的脸,他想。
返回到包厢时,葛兰已经穿好了衣服。她穿着暗绿色的厚外套,外套更像男式的。她的头发不长,一顶有沿的灰色帽子戴在头上。桑瑞还注意到她穿的裤子宽大,面料粗糙。
“该走了。”葛兰说,她手里拿着桑瑞的外衣。她将外衣递给桑瑞。
桑瑞接过外衣,他一边穿一边喊服务员结账。
“我已经结过了。”葛兰说。
“应该我来结。”桑瑞说。
“都一样。”葛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