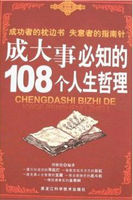叶圣陶先生在《对于国文教学的两种基本观念》(四川省教育厅《中等教育季刊》创刊号)里说:
其实国文所包的范围很宽广,文学只是其中一个较小的范围。文学之外,同样被包在国文的大范围里头的,还有非文学的文字,就是普通文字。这包括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等的应用文,以及平正地写状一件东西、载录一件事情的记叙文,条畅地阐明一个原理、发挥一个意见的论说文。中学生要应付生活,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就不能不在文学之外同时以这种普通文为对象。
这是对于现阶段的国文教学的最切要的意见,值得大家详细讨论。本篇想就叶先生的话加以引申,特别着重在写作的训练上。
这得从阅读说起。现在许多中学生乃至大学生对于国文教学有一种共同的不满意,就是教材和作文好像是不相关联的,在各走各的路。他们可只觉得文言教材如此。爱作白话文的,觉得文言文不能帮助他们的写作,原在意中。就是愿意学些应用的文言的,也觉得教材的文言五花八门的,样样有一点儿,样样也只有一点儿,没法依据。一般中学生对于教材的白话文,兴趣似乎好些。第一,容易懂,第二,可以学。他们的爱好却偏重在文学,就是教材的白话记叙文(包括描写文)、抒情文的部分。欣赏文学和写作文学似乎是一种骄傲,即使不足夸耀于人,也可以教自己满意。至于说明文和议论文,他们觉得干燥无味,多半忽略过去。再有,白话说明文和议论文适于选作教材的也不多;现在所选的往往只是凑数。这大概也是引不起学生兴趣的一个原因。
文言的教材,目的不外两个:一是给学生做写作的榜样或范本,二是使学生了解本国固有文化。这后一种也可以叫做古典的训练。我主张现在中等学校里已经无须教学生练习文言的写作,但古典的训练却是必要的。不过在现行课程标准未变更以前,中学生还得练习文言的写作。要练习文言的写作,一面得按浦江清先生的提议,初中时代从单句起手(参看附录);一面文言教材也当着重在榜样或范本上,将古典的训练放在其次,不该像现在这样五花八门的,不该像现在这样只顾课程标准的表面,将那些深的僻的文字都选进去。
浦先生还主张将白话文和文言文分为两个课程,各有教本,各有教师。这个我也赞成。我赞成,为的这样办可以教人容易明白文言是另一种语言,而且是快死的语言。不管我的意见如何,这办法训练学生写作文言,不致像现在这样毫无效果,白费教学者的工夫,是无疑的。而施行起来,只须注意教师的分配,并不要增加教师的员额,似乎也没有多少困难。——无论怎样,文言教材总得简单化,文字要经济,条理要清楚;除诗歌专为培养文学的兴趣应该另论外,初高中都该选这种文言作教材,决不能样样都来一点儿。这样才容易学习,学会了才可以应用。
浦先生主张将《古文观止》作为高中的文言教本,是很有道理的。清末民初的家庭里训练子弟写作文言,就还用《古文观止》或同性质的古文选本作教本。这些子弟同时也读《四书》、《五经》,那却纯然是古典的训练。他们读了《古文观止》,多数可以写通文言,拿来应用。一方面固然因为他们花的工夫多,教本的关系似乎也很大。不过《古文观止》现在却不大适用了,或者说不大够用了。清末民初一般应用的文言还跟《古文观止》的主要部分——唐至明,所选的文一贯的是唐宋八家的作风——差不很多。那时报纸杂志上的文字都还打起调子,可以为证。现在可不然。杂志上文言极少见,报纸虽还多用文言,但已不大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等虚字来表情,也就是不打起调子了。这从各报的文言的社论中最可见出。现在报纸上一般文言实在已经变得跟白话差不多,因为记录现代的生活,不由得要用许多新的词汇和新的表现方式;白话也还是用的这些词汇和表现方式。这种情形从一方面看,也许可称为文言的白话化。在这种情形下,用《古文观止》做应用的文言的范本,显然是不大够的。
但是《古文观止》还不失为一部可采用或依据的教本,因为现在应用的文言的基本句式还是出于唐宋八家文的多。我想再加两部书补充《古文观止》的不足:一是梁启超先生的《常识文范》(中华版),二是《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新潮社版)。这两部书里所收的都是清末和民初的杂志文字。梁先生的文字比较早些,典故多些,句式也杂些,得仔细选录。蔡先生的,简明朴素,跟现行的应用的文言差不多,初中里就可以用。这部书已经绝版,值得重印。浦先生也主张“选晚清到民国的文言文”,作为另外一种读本,给学生略读。我专举这两部书,是觉得就清末民初的文言文而论,也许这两部书里适宜于中学生的教材多些。此外自然也可以选录别的。这两部书里大部分是议论文,小部分是说明文。曾国藩说古文不宜说理;古文里的说明文和议论文有不确切的毛病。这两部书的说理比古文强得多。这也是我推荐的一个原因。
还有,叶先生所说的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文等等“普通文”,也该酌量选录。这些一向称为应用文,所谓“应用”是狭义的。我觉得无须另立应用文的名目。另立名目容易使学生误会,这些应用文之外,别的文都是不能应用的,因此不免忽略。而他们对于这些应用文也未必有兴趣,为的还用不着。再说教本里选一些这种应用文,只是示范,真用的时候还得去查专书。所以我觉得不如伙在别的教材一起,而使全部的文言教材主要的目的都为了应用——这里所谓应用是广义的。课程标准里所列举的“总理传说及遗著”直到“党国先进言论”,一部分也是所谓应用文,也可混合选入。清末民初的文言跟这些,都该有一部分列在精读教材里,和古文占同等地位。因为从训练写作一方面看,这两种教材比古文还更切用些。至于全部文言教材如何按照课程标准斟酌变通的去分配去安排,问题很多,本篇不能讨论。
白话文教材好像容易办些。古白话文不多,现代白话文历史很短,选材的问题自然简单些。不过白话文的发展还偏在文学一面,应用的白话文进步得很缓。记叙文(包括描写文)、抒情文,选起来还容易,说明文、议论文,就困难,经济而条理密的少,内容也往往嫌广嫌深,不适于中学生。现在教本里所选的有许多只是凑数。就是记叙文,也因篇幅关系只能选短些的,不无迁就的时候。至于其他应用的白话文,如书信等等,似乎刚在发展,还没有什么表现,自然更难选录。因此白话文教材主要的只是文学作品。而现代文学还在开创时期,成名比较容易,青年人多半想尝试一下。于是乎一般中学生的写作不约而同的走上创作的路。他们所爱读的也只是文学教材,就是记叙文和抒情文。但是二十多年来成功的固然有,失败的却是大多数。其中写不通白话文的姑不必论,有些写通了的也不能分辨文章的体裁,到处滥用文学的调子。叶先生文里说他“曾经接到过几个学生的白话信,景物的描绘与心情的抒写全像小说,却与写信的目的全不相干”。这种信只是些浮而不实的费话;滥用文学的调子只是费话而已。可是,如上文所说,这种情形不能全由学生负责,白话文的发展,所谓客观条件,也有决定的力量。
欣赏文学的兴趣和能力自然是该培养的。但是到处滥用文学的调子并不能算欣赏文学。这种兴趣是不正确的。这些学生既然不大能辨别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他们的欣赏能力也就靠不住。欣赏得从辨别入手,辨别词义、句式、条理、体裁,都是基本。囫囵吞枣的欣赏只是糊涂的爱好,没有什么益处。真能欣赏的人不一定要自己会创作;从现在分工的时代看,欣赏和创作尽不妨是两回事儿。施蛰存先生在《爱好文学》一文(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中央日报》昆明版)里说:
“我们欢迎多数青年人爱好文学而不欢迎多数爱好文学的青年大家都动手写作(即创作)。爱好文学是表示他对于文学有感情,但要成为一个好的创作家,仅仅靠这一点点感情是不够的。”这是很确切的话。不过欣赏文学的结果,自己的写作受些影响,带些文学的趣味,却是不难的,也是很好的,虽然不是必要的。我们可以引用梁启超先生的话,说这是“笔锋常带情感”。但是不带或少带情感的笔锋只要用得经济、有条理,也可以完成写作的大部分的使命。
不过有“创作”做目标,学生对于写作的兴趣好得多;他们觉得写作是有所为的,不止是机械的练习。固然,写作是基本的训练,是生活技术的训练——说是做人的训练也无不可。可是只这个广泛的目标是不能引起学生注意的。清末民初的家庭里注重子弟的写作,还是科举的影响。父兄希望子弟能文,可以作官。子弟或者不赞成作官这目标,或者糊里糊涂,莫名其妙,但在父兄的严切的督促之下,都只跟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