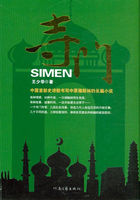美国有一位企业家,他拥有亿万家产,然而却在过节的时候一脸苦笑:“现在有了钱,我又不知道该享受些什么了!”
今天没有人再像古人那样追求“一箪食、一豆羹”的清贫生活,但天天鲍参翅肚,似乎又有暴殄天物之嫌。追求豪宅、名车、时装就和去吃鲍翅一样,属于一种不入流的情趣。赌博可以博一乐,但十赌就会有九输,再说赌博于法于理于修养都不容。去追求美色?更不可龋
“你最钟爱的是什么?充满了你的心灵,让你感到无比幸福的又是什么?”你若认真反思自己的内心需求,一定可以找出答案。
因为“自我”并非隐藏在你的内心深处,而是在你无法想像的高处,至少是在比你平日所认识的“自我”更高的层次里。真正认清你自己的内心渴望,唯有发自你的天性。唯有自己,才有资格成为自己的安慰者与解放者。
清人钱泳曾有云:“贫贱近雅,富贵近俗,雅中带俗,可以资生,俗中带雅,可以处世。”
在夜深人静的晚上,对着一幅自己的艺术作品不停地看,然后闭目,记住它并遐想。在洗心养神之际,你也许想起了一段童年的往事,也许想起了自己曾经历的最血光的商战,也许……这也算是一种雅俗之间的“资生”、“处世”之道吧。蒙田说过:“世界上最重要的事莫过于懂得让自己属于自己”,“必须阖门闭户重新拥有自己”。
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要求人们必须为奢华付出的最沉重代价,莫过于不能拥有自己。在高速度、快节奏、强耦合、多关联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失去了往日的悠闲,精神上高度紧张。万千信息奔来眼底,瞬息万变的事物需要及时处理。在眼快、手快、脚快、嘴快、反应快,五官四肢躯体综合大繁忙中,惟一闲置起来的却是一个思考的大脑。静不下来的头脑形同空置。大脑需要在宁静中工作。快节奏生活可能训练出快速机敏、准确反应的大脑,却往往失去了哲人式的恬静深思的大脑。
那种总揽全局的综合审视,大尺度联系的高阔视角,复杂脉络的仔细梳理,缠绕层面的小心剥离,以及思路不通、灵感未至时的耐心等待,找到突破点后的深入掘进,融会贯通后的乘势扩展……这一切都必须有一个从容自由的头脑,一个宽舒自主支配的生存空间,以及一个宁静无噪的平和心境。
而在嘈杂忙乱中生活的现代人大多是“失静”之人,必须属于快速的“流”。人生如萍,宛若不系之舟,在激流簇拥下,最难自持。崇尚简单生活的梭罗是持有自家生命宝券的真正富有者,能够最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生命。
他认为:“一个人越是有许多事能够放得下,他越是富有。”他悠然地说:“我最大的本领是需要极少……我爱给我的生命留有更多的余地。”生命在他手中支配得游刃有余。与此相反,一些拥有大量金钱的富翁,却被自己的黄金“焊”在某个高位上动弹不得。梭罗不无怜悯地说:“我心目中还有一种人,这种人看来阔绰,实际上却是所有阶层中贫穷得最可怕的。
他们固然已积蓄了一些闲钱,却不懂得如何利用,也不懂得如何摆脱它,因此他们给自己铸造了一副金银的镣铐。”位高自囚,富极如贫,事物常常是这样两极相通。街头警车呼啸而过,不是外国元首就是本国犯人;总统和穷光蛋口袋里都一文不名;女王和拾荒妇都不需要名片。生活中的辩证法值得深深品味。
一个人属于自己的重要标志是拥有能够独立思考的头脑,所以有些哲思未泯的人总想挣脱“失静”状态,寻觅净地,力图重新拥有自我。
历代许多著名的中外学者、思想家、文学家,他们也许生活得并不拮据,有的甚至相当富有,拥有自己的庄园城堡,但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过着“简单的生活”。梭罗更是这方面的典范,在瓦尔登湖畔,他凭借着简单而丰富多彩的生活为自己赢得了充裕的自由支配的时间。
他说:“因为我对某些事情有所偏爱,而又特别重视我的自由,因为我能吃苦,而又能获得成功,我并不希望花掉我的时间来购买富丽的地毯,或别的讲究的家具,或美味的食品,或希腊式的或哥特式的房屋。”由于挣脱了生活中的繁琐杂冗,梭罗才能够静静地阅读与思考,他说:“我的木屋,比起一个大学来,不仅更宜于思想,而且更宜于严肃的阅读。”瓦尔登湖真不愧是治学圣境。
正如蒙田所言:“我们要保留一个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由空间,建立起我们真正的自由和最重要的隐逸与清静。”正是在瓦尔登湖隐逸的自由空间里,梭罗为我们留下了如此睿智优美、充满人生哲理的圣洁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