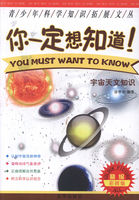“夜郎自大”这个成语来自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原文“夜郎王与汉使日:‘汉孰与我大?”’意思是说:夜郎国君对汉朝使者说:“你们汉朝大呢?还是我们夜郎国大呢?”这样,“自大”的名声二千多年以来就一直戴在了夜郎头上。然而,有关夜郎国的历史情况,知道的人却并不多。
“夜郎古国”,不管它是国家也好,或者仍然不过是一个原始部落联盟也好,但至少在战国时期至西汉河平年间,的确存在了250多年,“夜郎王”虽因说了“汉孰与我大”的话,以致贻笑两千多年。不过,从当时“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所有精兵,可得10余万”等情况看,他确实是有自大的理由的。
然而,“夜郎古国”距今毕竟有两千多年了,在中国正统史家的笔下,对这样一个化外“南夷”小国的事迹,虽有记载,却往往不是很详细。加上以后以“夜郎”为地名的,时过境迁,已经不是当年旧地。这就使后来的学者众说纷纭,连“夜郎古国”的确切位置,也没有人详细知道了。
关于“夜郎国”及其“国都”,一种看法是沿袭清人郑珍在《牂舸十六县问答》一文里提出的“今安顺府地即汉夜郎县”这一观点而稍作发挥,或说在安顺北部;或说在安顺、镇宁、六枝一带;或说在安顺县东南广顺。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夜郎国”及其中心区应在今贵州西南及六盘水地区,其东南境到贞丰、望谟、册亨一带。有人还依据《安顺府志》和《威宁县志·夜郎县考》上的论述推断:西汉成帝河平中,群牁太守陈立斩“夜郎王兴”时所到的且同亭,就是“夜郎国”的政治、军事机构所在地,它约在今贞丰、望谟一带,甚而指称“与北盘江会于贞丰之者香,即夜郎国都也。”不过,围绕古代典籍有限记载进行考订的传统方法,已经很难有新的突破,即如上述几种观点,大都只是沿袭明清学者的说法而已,且其中很多都有难以自圆之处。
新中国成立以后,贵州、云南等地的考古发现,则为探索夜郎故地打开了新的局面。众多的考古发现,不仅证实了“夜郎古国”的存在,而且还印证了“夜郎国”中心在贵州西部。尤其令人振奋的是,《史记》、《汉书》都提到过的“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中的“滇王”之印,早在1985年已从云南晋宁石寨山六号墓中发掘出来。
人们可以期待,随着贵州地方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虽然不一定能将两千年前的“夜郎王之印”和《华阳国志》上留名的“夜郎庄王墓”发掘出来,但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古夜郎遗物、遗址重见天日,并且为人们提供更多、更有说服力的相关材料。
此外,从民族学的角度切入,是解开“夜郎”古国之谜的又一突破口。因为,在夜郎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越人、濮人及少数氐羌人等,他们或是今天仍生活在贵州、云南、四川、广西一带的彝、苗、侗、布依、水、仡佬族的先民,或是与这些民族的先民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近年来,通过对数以百计的古彝文典籍和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的古歌、传说的翻译和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从而也为我们传递来不少有关古夜郎国情况的信息。
如解放后贵州毕节地区翻译的水西彝文巨著《恩布散额》及《水西制度》、《洪水泛滥史》等中,就有关于彝话六祖后裔约在战国时期迁入夜郎地区的记载。
而对于与“夜郎文化”有关的“滇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以及广西壮族西部文化(特别是桂西地区古代文化)的综合、比较研究,也有助于克服重犯“夜郎自大”、眼界狭窄的毛病,给古夜郎研究者以新的触发和启示。因此,“夜郎文化”并不是孤立地发展起来的,它和这些比邻地区的文化是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
如1957年在贵州赫章县可乐区辅初出土的西汉中期铜鼓上,其造型和鼓饰船纹、牛纹和羽人,就与云南“滇文化”的“石寨山式”铜鼓、四川西昌“邛都夷”地区的铜鼓、广西西林铜鼓葬使用的铜鼓,多有相似之处。
考古工作者们为探求夜郎古国投入了大量心血,遗憾的是,由于未能找到夜郎王族或主体臣民的墓葬群,所以一直难以获得圆满的答案。笼罩在夜郎古国身上的重重迷雾,还有待于人们进一步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