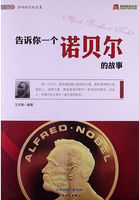中国古代有一则寓言故事,某人失羊,疑其邻人所盗,皆因先有成见,才观其言察其行,无不露贼态,数日后,所失之羊自行回栏,再观其邻人,已一切如常。
蒋介石自北伐计划遭到苏联顾问和汪精卫冷落后,就一直疑心有人要对他不利。有此成见在胸,也就无处不感怀疑反常了。
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山舰事件”是著名的司芬克斯之谜,是迄今为止尚未彻底解开谜底的悬案。
19日一清早,蒋介石已坐在汪府客厅。
汪精卫迟迟不露面,让蒋介石等得心焦。
陈璧君满脸厌烦,没好气地说:
“人生了病,都落不得清静。汪先生今天已请假不视事,谁知一早事还找上门。”
蒋介石心中冒火,他分明听出女主人已在下逐客令,但却固执地坐在那里。虽然如此也感到脸皮一阵阵发烧。
汪精卫终于出来了,他脸色苍白。昨晚,他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假广东省政府大花厅宴请各军政治主任。作陪的全军政治训练部主任陈公博席间就发现平时精力充沛的汪精卫神色倦怠。悄然一问,汪精卫无力地告诉他:
“今天在黄埔军校演讲时,就有些头晕。现在好像更严重了。”
“汪先生太辛苦了,应该休息一下吧。”陈公博体贴地建议。
“哪能够?我说给你们一段故事,有一次监狱里头一个囚犯生了病,狱医来看过之后说:最好你迁地疗养一下。话是好听,你想,一个囚犯怎能可以自由地到别处疗养?我现在就是那个囚犯。”
汪精卫说完这个譬喻,席间顿时哄然而笑。这正是汪精卫会说话之处,其实他在强调自己的地位重要,广东政府不可须臾离开他。
酷爱权力的汪精卫是不想休闲养病的,但陈璧君惜夫心切,坚决让他留在家中休息。好容易能寻得一番清静,却一大早就给蒋介石搅了,她是个心中藏不住事、喜形于色之人。因此,那怒气也荡漾在表面,让人可感可触了。
听着蒋介石的口罗嗦,汪精卫更感到头昏了,三番五次苦劝,蒋介石倒越来越上劲了,也好!眼见得他与苏联顾问越闹越僵,倒不如顺其所请,让他赴俄一趟,也少得眼前聒噪。他的口气也就松动了。
“既然介石心定如铁,愚兄也就不固执己见,惟望一路平安,来日大展鸿图。”
蒋介石心凉透了,这正是他一直想听,又最怕听的话,一切已证实了,一切已无庸再言了,他丧魂落魄地站起来,心中暗恨:
“全系权谋!全系权谋!政治斗争,毫无道德可言耶。”
依稀中,他听得汪精卫在问他今日是否回黄埔。
他机械地点点头。
蒋介石到黄埔驻省办事处,王柏龄、方鼎英、陈肇英、陈立夫都在那里,见到他,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王柏龄,时任第一军教导师长,他是江苏江都人氏,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十期生。蒋介石办黄埔时,把他招延至军校,任教授部主任,一时信任至极,被称为蒋的一条臂膀。
王柏龄为人轻浮油滑,酒色财气,四大皆全。在黄埔岛上弄得声名狼藉。蒋介石见此人实在朽木难雕,又转而着重培养何应钦。因此,王柏龄的升官速度有所滞缓,已在何应钦之下。尽管如此,由于他对蒋的忠诚,仍然被列为亲信行列。
方鼎英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八期生。回国后投身军旅,曾任湘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此人文韬武略,为蒋介石欣赏,曾花大力气将他挖至黄埔,虚身下气,甚至不惜执弟子礼。因他自称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十期生,所以称方为前辈。知遇之恩,无以复加。使方鼎英大为感动,极欲图报于万一。
陈肇英,虎门炮台司令,是蒋介石的结拜兄弟,近日来因走私案被李之龙抓住不放,十分狼狈。因此常来蒋介石这里告黑状。
陈立夫,美国匹茨堡大学毕业,采矿学硕士,1925年回国后,接受聘请,任黄埔军校英文秘书。官虽不显赫,但蒋却视之为家人。在蒋的政治生涯中,他认为受恩最重的有两人,即除了孙中山,就是陈其美了。是陈其美将他带出来的,而陈立夫就是陈其美的侄子。
蒋介石一摆手示意他们坐下,自己也无力地仰靠在沙发上,默默无语,他觉得身心俱乏,前途一片漆黑,已难以自处。
在座的人面面相觑,王柏龄倚仗他与蒋介石关系熟,试探着发问:
“校长……”
蒋介石厌烦地摆手,王柏龄吓得把话咽了回去。
就这样默坐着,直至尖锐的电话铃声才打破寂静。
陈立夫接过电话,向蒋介石说:
“校长,汪主席找您。”
蒋介石紧张地接过电话,只听他嘟噜一句,就放下了听筒。
“汪兆铭对我的行程这么关心?哼!”蒋介石气呼呼地坐下。
陈立夫小心翼翼悄声说:
“校长,昨天晚上,中山、宝璧二舰已开到黄埔,说是邓教育长的命令,经过您允许的。”
蒋介石目中精光暴长,全身紧张得发僵。
电话铃又不合时宜地响起。
陈立夫抓过话筒,稍许,回头告诉蒋介石,还是汪精卫打听今天是否回黄埔。
“不回。”蒋介石身姿一动不动。
王柏龄又凑过身子,
“校长,这是怎么回事?”
“娘希匹,这是有人要拿我开刀了。”蒋介石怒火顿时迸发出来。他转过身子问方鼎英,应如何应付?
方鼎英一直端坐不语,蒋介石问话时,他立即站了起来,身板笔直,保持着良好的职业军人风度。他沉稳地劝告说:
“校长,稍安勿躁,也许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汪主席也是随便问问。”
“唔、唔。”蒋介石无置可否,却又重新坐了下来。
终于,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这次他亲自接过电话,话筒的那边,传来的是他的学生、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的声音。
李之龙的口气十分恭敬,他告诉蒋介石,因俄国参观团来穗,欲调中山舰摆摆场面。如校长允许,可否让中山舰回广州。
蒋介石的腔调有点阴阳怪气。
“之龙,中山舰开来黄埔不是我的命令,我既没要你开去,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好了,何必问我呢?”喀嚓,不等李之龙解释,蒋介石挂断了电话。
王柏龄作恍然大悟状:
“原来汪主席的电话与李之龙这小子有关。”
陈肇英也愤愤切齿说:
“李之龙背叛师门,最近抱上了汪精卫这条粗腿,更加目中无人了。”
方鼎英皱起眉头,他知道王柏龄、陈肇英对李之龙恨之入骨,但这样的挑拨未免太阴险了。将个人的私愤引入到国家军政大事中。将遗祸至大。
果然,蒋介石将中山舰的调动与汪精卫的反常联系了起来。这就是他一再声称的“万万想不到的事情。”他摆出了怀疑的理由:
汪精卫“如此一连打了三次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当他打第二次的电话,我还不觉得什么,直到第三次来问我的时候,我觉得有些稀奇。为什么那同志今天总是急急的来问我去不去呢?如果没有缘故,他从来没有这样来问的。”
至于“中山舰到了黄埔,因为我不回黄埔,在省里,他就开回来省城,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因此,蒋介石推论说:
“季山嘉阴谋,预定待我由省城乘船回黄埔途中,想要劫我到中山舰上,强逼我去海参崴。”
接完李之龙的电话,蒋介石在屋中不停地来回踱步,中间几次有人想插言,都被他挡了回去。终于,他停了下来。
“备车,”他简短地吩咐。
“去哪里?”陈立夫问。
“去汕头。敬之在那儿,他是拥护我的。你、你,”他用手指指方鼎英、陈立夫。“有劳二位送我一程。”
“完了!”见蒋介石一走,王柏龄象被抽去脊骨般瘫倒在沙发上。
“今后广州成了共产党、汪精卫的天下了。”
陈肇英恨声说:“李之龙那小子更神气了。”
两人正在各自沮丧,门外一阵引擎声,蒋介石推门而入。
望着别人惊讶的神色,蒋介石冷静得怕人。
“立夫所劝甚有理,有枪在手,有兵在手,何惧之有。若不于此当机立断。何以救党,何以自救?此时再不决心,尚待何时。此时若不殉党,何颜立世。今日事只有败中求胜,背水一战。”
王柏龄、陈肇英早已眼睛发亮,一股气在胸中翻腾。
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就这样发生了。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中山舰的调动与汪精卫、季山嘉无关,与李之龙无关,与共产党无关。蒋介石的推理论断是站不住脚的,这只是一场“误会”。然而,蒋介石却不能向世人承认这一血腥的行动源于他的多疑。只能故布迷阵,把答案推到他那总不见公布的日记中。
然而,对于蒋介石来说,“中山舰事件”的结果对他十分有利,他不仅借此挤走了汪精卫,也打击了苏联顾问的威信,削弱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由此掌握操纵了国民党军政大权。这一事件的发生,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但唯物主义认为,必然性寓于历史的偶然之中,偶然性表现为必然的结果。这也是与蒋介石思想的右倾、权力欲望的发展分不开的。
汪精卫、蒋介石的第一次合作到此结束了,汪精卫在病榻中听到事变消息后,面色苍白,语无伦次,状似发疯却一筹莫展。3月31日,他致函蒋介石,负气地说:
“今弟既厌铭,不愿与共事,铭当引去。”
蒋介石却倒打一耙,4月9日复函云:
“譬有人欲去以为快者,或有陷弟以为得计者,而兄将如之何?”
他居然还能理直气壮地责问说:
“以弟之心推之,知兄必无负弟之意,然以上述之事实证之,其果弟为人间乎?抑兄早为人间乎?其果弟疑兄而厌兄乎?抑吾兄疑弟而厌弟乎?”
猜忌嫌恶之心,跃然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