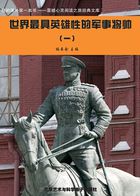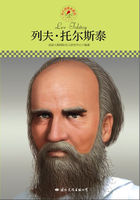张大千一生遍游中外名山大川,却从未登过庐山。他曾有一个夙愿,希望祖国统一后,能一登匡庐,在过溪亭上小憩一会儿,饱览庐山美景。但遗憾的是,这件心愿在他有生之年未能如愿。
1981年夏初,张大千刚度过83岁寿辰后,一位旅居日本的华侨巨商李海天专程飞到台北,登门拜望张大千,见老人身患多种疾病,腿伤后还需人扶,话到嘴边欲言又止。
李海天与张大千以前就相熟,更了解他的怀乡之情,正因为此,他才来找张大千的。“唉,干脆说出来试试!”他终于道出了来意:“大师,我想请您作幅画,以庐山为题材的大画。”
老人认真了,看来客人真心诚意,他说:“我从未去过庐山呀!”
“没去过?”李海天听了大吃一惊,难以相信,天下名山都看遍的张大千,怎么会没有去过大名鼎鼎的庐山呢?
“真的没去过。”张大千再次肯定,顺便说起自己没去的原因,“这与先仲兄善孖有关。以前在上海和苏州,我和先仲兄同游华山、黄山,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但就怕一点,哪一点?只要有他的朋友在,我就完全成了鼻涕横揩的小兄弟,谈诗论画,饮酒品茗,我只能站在一旁伺候,不是味儿呀!先仲兄两次游匡庐,都是他的朋友相邀,我当然不愿去,不如躲在家里称王称霸。”
李海天听了这段有趣的往事,脸上在笑,心中暗暗叫苦,这幅画没谱了!想不到,忽地柳暗花明。
张大千沉思了一会儿,忽然说:“这幅画我画。”
“真的?”李海天喜出望外。
张大千一听不高兴了:“我张大千说话无戏言。”
李海天赶紧解释:“哦,大师,真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不是说没有去过庐山吗?”
“画我心中的庐山!”张大千口气分外干脆坚决。
“形成于未画之先。”没有去过庐山的人,怎么画庐山?张大千历来认为:“我笔底下所创造的新天地,叫识者一看自然会辨认得出来。”
但要真正画出“心中的庐山”,绝非易事。更何况,这是一幅罕见的巨幅,36尺长,6尺高!它要由一个从未去过庐山、疾病缠身的老人完成,难!不少人为张大千捏了把汗。
张大千自己也不敢掉以轻心。他特地请来朋友沈苇窗,为他收集有关庐山的文字、照片资料,并将这些资料做成详细的笔记。说来也巧,沈先生收集的文字、照片资料中,有一些就是大陆出版的。
张大千还翻阅了一些古籍和有关书籍,有意识地和一些去过庐山的人摆谈。渐渐地,庐山在他心中活了:它独有的自下而上的雨,有声的云,汹涌的云海,时聚时散的佛灯,直下三千尺飞瀑……它岂止是心中的庐山,它是心中祖国的象征!
张大千要以他的笔墨,抒写对祖国的思念。他要以终生的经验和学识,绘出这幅能流传久远的巨作。
几个月来,他神游在庐山峰峦之间,日日夜夜,朝朝暮暮,和庐山交谈。老人以他几十年游历山川的心得和绘画的经验,凭借他惊人的艺术想象力,庐山真面目展现在他眼前,庐山屹立在他心间。
1981年7月7日,是张大千巨构《庐山图》的开笔吉日。
张大千装束一新,团花长袍东坡帽,白绸长裤青缎鞋,面带喜色,银髯飘拂,哈哈笑声响彻画室内外。被特邀参加开笔礼的观礼嘉宾有大名鼎鼎的“三张一王”的另外三人:张学良、张群、王新衡等。
大画案上,铺着绢织画料,儿女们已经用清水把它敷润过了。画室里挤满了人,大家的目光都投射到主人身上。
张大千终于笑呵呵地起身了,他手指轻捻银髯,目光来回扫视着画料。片刻,他回过头来,双手抱拳,向观礼嘉宾一一致意:“大千献丑了。”
他首先端起一个青花大水盘,里面盛着满满的墨汁,身体前倾,手肘自左至右,将墨汁缓缓向画料上泼去。
嗬,开笔不用笔!乌黑的墨汁在绢料上慢慢浸润。它将变成高山,长出峰峦,吞吐万象。客人们都起身站在四周,看他如何创造一个新天地。
张大千执定大帚笔,依然谈笑风生。他以淡墨破出层次,勾定大框廓,然后,又以笔蘸水濡墨,以通气韵。他不像在作画,像在打一趟极富内养功的太极拳。他运动大帚笔,头、眼、颈,乃至四肢都在动,连嘴巴也在动,有板有眼地说:
浓墨不破,便无层次;淡墨不破,便乏韵味。墨为形,水为气,气行形乃活。
在画《庐山图》前先画几幅小画,是张大千给自己订的规矩,并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加以坚持。
他说:“画我心中的庐山,整体在胸,局部却要边想边画,不可妄下一笔。”
这幅画,犹如在阿里山上修一条盘山公路,工程浩大,不能偷工减料,整整一个多月,老人才着手在画上泼洒石青、石绿等色彩。
不知怎么搞的,张大千觉得胸口越来越闷,呼吸短促起来,他明白自己的心脏病又发作了。老人张大口喘息,右手在茶几上摸索,寻找装心脏病特效药的小瓶子。
这样的事以前多次发生,徐雯波就在他常去的地方都放上这样的药瓶,以防万一。
张大千发抖的五指在几上摸呀,摸……徐雯波出现在门边,尖叫一声,脸刷地白了,她三步并作两步,奔到丈夫面前,赶紧把药片塞进老人发紫的嘴唇,轻轻揉着丈夫的胸口。
吃下药,张大千舒服多了,他仍然闭着眼,耳边只有座钟“滴答、滴答”单调重复的声音。“滴答、滴答……”好像家乡圣水寺石壁上往下滴的水声,“滴答、滴答……”好像青城山上清宫计时的水漏,敦煌石窟融化的雪水,成都四合院瓦脊上的绵绵细雨……“滴答、滴答”,多耳熟。
张大千觉得自己的心律如同那座钟,平稳,有规律,完全恢复了正常跳动。他想再歇歇,又想去画画,眼睛似睁非睁之间,猛然一个想法闪过自己心中。唉,真后悔,应该在写寄大陆老胡的那幅《荷花图》上题写那首诗:
海角天涯鬓已霜,挥毫蘸泪写沧桑。
五洲行遍犹寻胜,万里归迟总恋乡。
1982年春,张大千赠送他的老画友张采芹先生一幅花卉,图上题了一首诗:
锦绣裹城忆旧游,昌州香梦接嘉州。
卅年家国关忧乐,画里应嗟我白头。
这一天清晨,张大千正准备开始泼彩,继续他为之呕心沥血近一年的《庐山图》。这时,忽然有客人来访,原来是中国旅英钢琴家傅聪。
张大千站在客厅门口,等傅聪走近了,他笑呵呵地用手指点他:“大概有10多年没有见到你了,今日一见,真高兴!”
傅聪抢前一步,双手扶着张大千的胳膊,愉快地回答:“是啊,我们在巴西相识,美国相交,今日又在台湾重逢,真不容易啊!”
张大千一边由傅聪扶着走向客厅,一边摇摇头:“哪里是巴西相识的哟,我认识你的时候,你比钢琴高不了多少,鼻涕横揩哟!”
傅聪听了,开心地笑了起来。这个48岁的钢琴家,哪会知道这个84岁的老前辈同他父亲的交往哩!张大千早年在上海时,就与同在上海的傅雷互有往来,自然见过自小就有音乐天分的傅聪。
几十年一晃而过,再度相见已是1982年5月23日,“大胡子”老了,“小孩子”已成为闻名遐迩的钢琴大师。
上午的阳光暖融融的,傅聪和老人并坐在一对沙发上,随便聊了起来。傅聪打量着这个陈设典雅的客厅。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四壁悬挂的书画。正中一幅大立轴,是张大千二三十岁自画像。画中人一脸黑黢黢的络腮胡,乌亮的双目凝视前方,一股自信轩昂的神采飞出眼外。
右壁上,有一幅曾熙画的《梅花图》。这幅画并不高明,因为曾熙晚年才学画梅花。
左壁,是黄公望的《天池石壁》。张大千之所以舍得花重金向琉璃厂国华堂老板购买,全因为画上有张善孖的老师傅增湘题的字:
大风堂藏一峰道人天池石壁图,真迹无上神品。
张大千对傅聪说:“这些画,是几天前刚换上的。”
家人和他的知心朋友都知道,客厅和大画室四壁的作品经常更换。但是,张大千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更换的字画多少要与他常叨念的三个人有关,一个是他的二哥张善孖,另两个是他的老师曾熙和李瑞清。到了晚年,老人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是这三个他极尊重的人。
大家由书画上扯开了,从不久前在台北市展出的“宋元明清古画展”,一直谈到中国的诗词歌赋和戏剧,又兴致勃勃地谈到中国绘画艺术所表现的抽象意境和独特的抽象美。两人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国艺术这份具有千古魅力的抽象美应予保留。
徐雯波知道傅聪晚上还有演奏,悄悄扯了一下大千的衣袖。
张大千明白了夫人的用意:“哦,看我,摆起龙门阵就没有完。傅先生,我们到园内走走,要不要得?”
张大千刚陪着傅聪走出客厅,那只黑面黑耳金黄细毛的长臂小猿腾空一纵,跃上主人的右肘弯,然后老实不客气地轻舒长臂,攀着主人的肩头,舒舒服服地坐到主人的肘弯里。张大千抚摸着小猿蓬蓬软毛,笑眯眯地说:“这淘气的小家伙。”
傅聪笑而不语,他知道大师爱猿、养猿、画猿的逸事,也听人说过那个广为流传的黑猿转世的神话。
张大千陪着傅聪,兴致盎然地在园内四处走,指点着精心布置的假山、流水、亭阁、花木、盆景。
傅聪在心里赞叹:“多美呀,生活中处处有艺术,无论是诗、画,还是音乐。”他不禁想起挂在客厅内的那副对联,是张大千手书的:
种万树梅亭上下,坐千峰雨翠回环。
脚边娇嫩的小草正吐着春的气息,傅聪心里暖酥酥的,忍不住俯身下去,温柔地拨弄小草。他用手指捏起一块泥土,凑近鼻孔,黑油油的,清香、醉人。“嗬,多好,多么肥沃的泥土!”他忍不住赞叹。
张大千不言不语,好像没有一丝反响。傅聪扭头一看,老人的头微微低着,盯着脚下的泥土,脸上掠过一道阴影,转瞬即逝。傅聪看得出,老人心里隐藏着深沉、丰富、复杂的感情,它同泥土有关,或者说,是泥土激化了这种感情。
就在10多天前,一位刚从大陆来的美籍客人,不远万里送来一包泥土,一包成都平原的泥土,家乡的泥土!
张大千用颤抖的双手捧着泥土,贴到脸前,用力闻着,热泪,慢慢、慢慢地蓄满两眶。
整整40年了,从北平逃亡出来,和孩子们返内江,畅谈土地、茅封、社稷。40余年后重睹这故乡沃壤,老人像捧着最庄严最神圣的东西,一步,两步,慢慢地迈向父母遗像前,将这捧故国的泥土,伴着这数行热泪,敬供在先人遗像前。
此刻,张大千的神情感染了傅聪,整个园子静静的,无声的音乐在心中盘旋,忧郁、伤感、深沉。
张大千又领着傅聪来到他的大画室。刚走进画室,傅聪立即被一幅气势宏大的画吸引了,这是老人灌注了全部心血正在创作的《庐山图》。
这幅画了近一年还未完成的巨构,是张大千平生创作时间最长的作品。创作期间,他数次在画室里晕倒,数次被送到医院急救。每一次,他都化险为夷。
每次出院,他都要向喜笑颜开的亲友开玩笑:“阎罗王不要我。他说,你的事还没有做完,怎么就想来了?还是回去吧!”
傅聪站在这幅大画面前,从心底发出了赞叹:“嚯!庐山,真是气势非凡!大师,你上过几次庐山?”
张大千平静地说:“我没去过庐山。这张画,画的是我心中的庐山。”
傅聪的心情豁然开朗了,他抓住了始终在心中盘旋的那首无名乐曲的主旋律。他以仰慕的心情看着这位老人,同时想起了他所仰慕的另一位艺术家——肖邦。
这位客居巴黎近20年,年仅39岁就与世长辞的波兰钢琴家,在他垂危之际留下遗嘱,请求友人一定要把他的心脏送回祖国,安葬在故土的沃壤里。而眼前这位老人,他把他的思乡之情,全部寄托给了丹青。
张大千的身体每况愈下,经常进出医院,险象迭起,家里人时刻都为他捏把汗。然而,他日益固执,不愿长期住院治疗,每天要画上半个至一个小时,气势雄伟、浩瀚万千的庐山已将自己的真面目跃然纸上。
这幅画,张大千使用了多种技法。他用大泼墨渲染出主山的脉络,以漫延的重墨凝聚为厚重山岩。在浓墨染出的峰顶、幽壑、丛林处,他一反以水破墨的古法,以石青、石绿、重赭诸色代替清水破开浓墨,析出层次,使得层峦滴翠,云雾氤氲。
他以泼墨泼彩法写出的逶迤山势,云气横锁,烟笼林隙,古木森罗,庐山横侧真面目欲现又隐。
画上,有他在1982年底题写的一首七绝:
不师董巨不荆关,泼墨飞盆自笑顽。
欲起坡翁横侧看,信知胸次有庐山。
徐雯波试探着问道:“春节马上要到了,今天你就不画了吧,待过完节再说。”
张大千爽快地回答:“好,听你的,今天不画了。只题两首诗可以嘛。”
笔砚准备好了,张大千提笔思索片刻,在画上又增题了两首七绝,几十个字整整花了半个多钟头。老人颤抖着手放下笔,颓然倒在沙发上,许久说不出话来。
徐雯波一边在丈夫背上轻捶,一边细语解忧:“大千,我记得你前两年写了这样一副对联:‘踵羲皇而齐泰,体虚静以储神。’我想,你安心静养一段时间,身体更会好些的。”
张大千点点头,口气有些幽默了:“老乎哉,人老矣,心不老,管它这么多做啥!”继而,他问夫人,“林先生捎来的那幅合作画,现在该完成了吧?”
这幅合作画,是美国得州休斯顿贝勒医学院的林文杰教授往返穿梭,四处搭桥而促成的。
1982年底,林文杰随美国空中眼科医院那架被称为“奥比斯工程”的飞机来到广州探亲,他将自己画的兰花拿去向关山月请教,并说去台湾时还要向张大千先生讨教。
关山月想起了往事,于是在画的梅花贺年卡上题写了“大千前辈万福,艺术生命长青”的贺词,请林文杰去台湾时转送张大千。
林文杰在繁忙的治病和讲学之余,到了年底再次来到广州,他弄到一张质量很好的4尺宣纸,在上面画了几叶春兰。
12月30日,他直飞香港,将自己的来意告诉了岭南派画家赵少昂。赵少昂非常赞许这种笔墨姻缘,又在画上添上一竿墨竹和一支勃勃向上的笋竹,钤上齐白石生前篆刻的白文印章“少昂”。
1983年1月2日,林文杰刚抵达台北,马上驱车去拜见张大千,张大千很有兴趣地接待了这位文质彬彬、西装革履的青年。林文杰送上了关山月的贺卡,张大千连称“难得”。
随后,张大千坐在画案前,铺开林文杰带来的那幅未完成的画,看了之后自谦道:“我自己不善于画兰花,不过我可以画别的。”
张大千说罢,欣然挥毫寥寥几笔,染出一块兀立的寿石,然后在上面添加了一朵灵芝。“灵芝一定要有红叶才会补得,我得给它上点儿色。”
张大千在毫尖上蘸着朱红,染出了红叶。然后,在画的左下角题道:“八十四叟张爰大千写灵芝和寿石。”盖上老友方介堪两年前托人从大陆带来的白文印章“张爰之印”和朱文印章“大千居士”。
林文杰看到张大千确实老了,画这样的小画他竟休息了两次!
张大千钤好印章,向林文杰建议道:“灵芝寓有长寿之意,如需添配,最好请关先生画上几枝墨梅。”
林文杰持此画路经香港时,赵少昂、杨振宁得知此事,都曾在这幅画前合影。
3个月后,林文杰再度从美国来广州,在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的帮助下,请关山月画上了一枝苍劲的梅花。
3月19日,这幅画被送到北京荣宝斋,在鉴定专家侯凯的精心指导下,由有名的装裱师傅精裱。然后,林文杰持画分别拜访了吴作人、肖淑芳、董寿平、李苦禅、黄胄、范曾、胡爽盦等中国名画家,大家都为之击节赞赏。
这幅由大陆、台湾、香港以及旅居美国的中国艺术家通力完成的《梅兰竹芝图》,不仅成为艺坛的一段佳话,也是张大千与人合作的最后一幅绝笔画。
人们都没有想到,此时的张大千已卧榻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