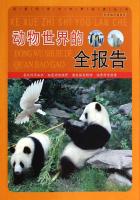大部分协奏曲都采用多段体结构的单乐章形式。例如筝协奏曲《汨罗江幻想曲》(1980年)采用古代诗人屈原这一悲剧题材,表现了诗人内心的痛苦和人民对屈原的深切悼念。作曲家“把中西不同的结构原则作了一些调和,把主题呈示、发展、再现的原则与多主题的连缀结构糅合到一起。”李焕之:《传统音乐和我的创作》。载《音乐研究》1988年第2期。在挖掘和发展筝的表现性能方面,在运用和声、复调、配器等作曲技巧方面,《汨罗江幻想曲》显得比较成熟。又如二胡与乐队《新婚别》(1980年)以杜甫的同名诗篇为内容,通过“迎新”、“惊变”、“送别”三段音乐,贯穿着对比和再现的原则,揭示了一位古代新婚少妇在与丈夫生离死别时的悲痛、复杂的心情。
部分协奏曲采用规模更大的多乐章结构,来展示丰富的乐思。乐章的多少、乐章内部的构成都采取比较自由的安排。
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1981年)通过“关山行”、“烽火操”、“忠魂祭”、“遥望篇”四个乐章,来抒发当代人们对古老长城的感受,讴歌中华民族光辉的历史和未来。乐曲序奏中出现的“长城特性音调”成为贯穿于整部作品的音乐主题。第一乐章独奏二胡的音调深沉、舒展,旋律的展开采用了民族曲调连绵不断的发展手段,作曲家特别注意旋律展开的民族特点,使这部作品带有更深的民族音乐意蕴。《长城随想》在独奏乐器与协奏乐队这两方面都发挥得比较充分,所体现的“史诗性”和“交响性”都显得比较成熟。它成为本时期民族管弦乐创作的重要收获,也是我国民族管弦乐创作走向成熟的一座里程碑。
管乐协奏曲《神曲》(1987年)是根据屈原《九歌》的诗意而创作的,全曲通过“天帝、河神”、“山怪、地鬼”、“礼魂”三个乐章,来体现《九歌》的神话色彩和民间气息。这首乐曲要求一位演奏家能够吹奏排箫、篪、埙、曲笛、梆笛、巴乌、葫芦丝等多种管乐器,这对演奏家是一个严格的考验。为了表现神秘、空灵的意境,作曲家采用了创作、演奏上的一些新技法,较完美地体现了屈原《九歌》的深刻内涵。
中阮协奏曲《云南回忆》(1987年)是第一首为中阮创作的大型作品,它的出现标志着中阮这件乐器在演奏技巧上的重大飞跃。作曲家通过艺术对比的三个乐章,表现梦幻般的云南风情、青年人蓬勃的生气与甜蜜的回忆。中阮大胆借鉴了吉它的演奏技法,并充分发挥了自身特有的淳厚的音色。优美动听,韵味浓郁,通俗易懂,使这首协奏曲很快就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还有一类民族乐器协奏曲是由西洋管弦乐队协奏的,如双筝(一位演奏家弹两台筝)与交响乐队的《回旋协奏曲》(王树曲),马头琴协奏曲《草原音诗》(辛沪光曲),唢呐协奏曲《大得胜》(戴宏威曲),琵琶与管弦乐协奏的音诗《夕阳箫鼓》(吴祖强改编),琵琶与乐队《乌江恨》(杨立青曲),唢呐协奏曲《天乐》(朱践耳曲),二胡协奏曲《惜别》(戴宏威曲)等。这类与西洋管弦乐队结合的协奏曲,始自1956年的唢呐协奏曲《欢庆胜利》(刘守义、杨继武曲)和1973年的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吴祖强、王燕樵、刘德海曲)。参看本书第七章中的论述。这类作品由于在国外有较多演奏的机会,因而在国外的反响往往比国内更为强烈。双筝与交响乐队的《回旋协奏曲》是一部单乐章的大型作品,作曲家取材于琵琶古曲《海青拿天鹅》,但又完全不受原素材的束缚。筝在交响乐队丰富的复调、和声的衬托之下,更好地发挥了它的独特的色彩。作曲家在研究了“双筝”的特殊表现力后,尽可能地利用了筝的按、滑、揉、颤及“摇指”、“扫弦”等演奏技巧,使筝的表现力及与交响乐队合作的能力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新时期协奏曲创作的丰收是空前的,这是八十年代民族管弦乐发展的重大成果,一些优秀作品,将留下深深的历史足迹。
“协奏曲”是一种外来器乐体裁,民族音乐中缺少这一方面的传统。为民族乐器写协奏曲本身就是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我们的民乐协奏曲作品大部分都在协奏曲体裁的民族化上作了努力并取得了成绩,它很快已成为民族器乐创作的一个新的、十分具有发展前途的体裁。但西方协奏曲的思维模式还严重地束缚着我们的作曲家。一些民族乐器本身发展的程度尚未达到能与大乐队竞奏的条件。某些独奏乐器在与大型民族乐队合作时,它们的音—量、音律、演奏技巧等方面尚未得到完满的解决。因而,有些名为“协奏曲”的作品显得简陋和牵强,大多数民乐协奏曲的“华彩乐段”都写得单调而千篇一律,既缺乏深刻的音乐内涵,又缺少辉煌的炫技。
3大型民乐合奏曲的蓬勃发展
协奏曲之外的大型民族管弦乐合奏创作,在1976年以来,特别是在八十年代以来也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大大超过了五六十年代的水平,内容和形式上极大地丰富了。
1976年以来的大型民族器乐合奏曲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深入挖掘传统音乐以发展民族乐队艺术的,第二类是努力借鉴西方经验以完美民族乐队艺术的。这两类作品在实际上无法绝然分开,因为大多数作品都是在挖掘传统和借鉴国外这两方面寻找沟通点。分类只是大体上的。
第一类作品大多采用古代题材或民间生活题材,音调素材上往往与传统音乐和民间音乐存在着比较直接的联系。以合奏音诗《流水操》(彭修文曲)、合奏《蜀宫夜宴》(朱舟、俞抒、高为杰曲)、合奏《长安社火》(赵秀平、鲁日融曲)、幻想曲《秦·兵马俑》(彭修文曲)等为代表。
合奏音诗《流水操》(1979年)的音乐素材取自古琴曲《流水》,乐曲描绘由涓涓细流汇成涛涛大河的过程,表现了人们对山河的热爱之情。作品既有传统音乐的韵味,又溶进了现代人对自然景色的感受。
民族管弦乐合奏《蜀宫夜宴》(1981年)表现了我国五代十国时期(公元十世纪)前蜀宫廷夜宴的歌舞场面。“其素材的运用、曲体的构成、乐队的编制与配器,乃至音乐的格调、情趣等方面,则皆大体依据一些有关的文物与文献资料予以创意铺陈,试图使作品具有一定历史的风貌。”朱舟、俞抒、高为杰:《〈蜀宫夜宴〉创作札记》。载《人民音乐》1982年第5期。作品的中间部分采用了宋代姜白石传谱的《霓裳中序第一》的旋律素材,奏出了作曲家想象中的唐乐音响。在表现古代题材和拟作古代音乐这一方面,《蜀宫夜宴》作了十分认真、严肃的探索。
合奏《长安社火》(1982年)是一首通俗易懂、充满民间情调的乐曲,作曲家以秦腔音乐为素材,表现了陕西农民新春佳节“闹社火”“社火”是陕西民间的群众性艺术活动,类似其他地区的民间“秧歌”、“灯会”活动。的欢乐场面。乐队中突出了具有陕西地方特点的板胡、唢呐、笛子、三弦和打击乐器,渲染了红火欢腾的秦川民间气氛。
属于第一类的影响较大的作品还有民族管弦乐合奏《飞天》(徐景新、陈大伟曲)、音诗《骊山吟》(饶余燕曲)、合奏《昭君别》(王惠然曲)等。这类作品深入挖掘了民族音乐中抒情性、戏剧性以至“交响性”的因素,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实现民族乐队的迅速发展。
第二类民族乐队作品大多采用现实生活题材,音乐素材上与传统音乐、民间音乐的联系往往比较间接,并大胆借鉴异体文化来获得民族乐队的升华。可以合奏曲《达勃河随想曲》(何训田曲)、交响音画《大江东去》(徐景新、陈大伟、陈新光曲)、交响音画《塔克拉玛干掠影》(金湘曲)、合奏《两乐章音乐》(瞿小松曲)等为代表。
民族交响音画《大江东去》(1980年)以宏大的气势表现了一泻千里、惊涛拍岸、江河奔流的画卷,以富于哲理性的含义歌颂了中华民族雄强的力量。作曲者将古琴与民族乐队相结合,使古琴处于领奏的地位,为民族乐队增添了新鲜的音色和深沉的因素。《大江东去》在和声、配器、乐队织体上考虑得非常细致,曲式方面,它将奏鸣曲式与唐大曲结构相结合,实现了两种音乐发展思维的交融。
《达勃河随想曲》(1983年)描绘了达勃河畔神奇迷人的风光和当地藏族同胞刚强、豪放的性格。在大型民族乐队中,加进了女高音(8人)、男高音(6人)哼唱的两个特殊声部,使之与民族乐器交织在一起。《达勃河随想曲》中运用了一些藏族古老民歌的素材,并采用比较新颖的创作技法加以自由的发展,乐曲的调性变化频繁,音乐织体比较复杂,音响效果新鲜而动听,塑造了鲜明、独特的音乐形象。
《塔克拉玛干掠影》(1987年)是一部多乐章的民族交响音画,由《漠原》、《漠楼》、《漠舟》、《漠洲》四个乐章构成。旋律建立在新疆南部的民间音调基础之上,变化多端的节奏、变幻莫测的色彩,构成了一幅幅神秘而迷人的沙漠风光,现代作曲技巧的引入使音乐色彩更富于变化,尤其是在第二乐章《漠楼》中,无调性、多调性、微分音手法构成了神奇梦幻的海市蜃楼的景象。
属于这一类的民族管弦乐曲还有合奏《水之声》(阎惠昌曲)、《第二民族交响乐》(刘星曲)等。这类作品以开放的姿态努力借鉴国外器乐音乐的经验,大胆参考现代音乐观念和创作技巧,并努力使这些经验和技巧与民族的音乐思维相激荡和交汇,从而丰富了民族乐队的表现力。
八十年代以来的民族管弦乐创作,与以前的发展状况相比较,带有许多明显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从思想观念到创作技法都体现了一种多元化的特点,因而作品的面貌表现出丰富多样的形态。
第二,作曲家在创作中努力追求着体现民族乐队的独特风格和特有魅力,努力按民族管弦乐创作的特殊艺术规律来办事。例如,不再一意去追求“规范化”的民族乐队编制,也不去一意追寻民族音乐的“交响化”。
第三,广大的专业作曲家已认识到民族器乐创作的重要意义和丰富的表现力,因而老、中、青几代作曲家均以巨大的热情投身于民族管弦乐曲的创作。指挥家、演奏家的创作亦具有了一定的专业水平。
第四,随着演奏水平和创作水平的提高,“曲高和寡”的问题突现出来了。民族器乐创作已开始出现脱离广大群众的现象。一些“新潮”民乐作品,更是远远地脱离了音乐爱好者和专业音乐工作者。原本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族器乐,与群众间的沟壑越来越大。这种状况加深了民族器乐发展的危机。让民族器乐重新贴近广大人民,重新成为群众音乐生活的一部分,这是一个新的、重要的任务。
小结
我国当代民族管弦乐队建设经历了四十年的历程,其发展的轨迹大体上是这样一个曲线:五十年代主要成就是中、小型的合奏作品,以《翻身的日子》和《喜洋洋》等为代表;六七十年代在左倾文艺思潮和“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与摧残之下,民族乐队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大断层;民族乐队在长期沉寂之后,迎来了八十年代的飞速崛起,其主要的成就是大型合奏作品和民族打击乐艺术的振兴,代表作品是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和打击乐小合奏《老虎磨牙》等。
经过四十年的艰苦创业,与世界各民族和地区的民族乐队相比,中国的民族管弦乐队已成为一种具有独特乐器、独特音色、独特表现力和独特风格的独特乐队。它体现着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特殊品格。保持、发扬这些可贵的艺术特点,应当是今后建设中国民族乐队的基本着眼点。进一步向西方交响乐队和各国民族乐队的优秀经验学习,同时进一步摆脱交响乐队模式的影响;进一步借鉴西方的作曲技法和音乐观念,同时进一步突破西方音乐思维对民族音乐的制约,这双向的任务应该同等受到注重。
民族管弦乐——这是一片广袤而神奇的音乐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