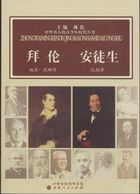2002年春节过后不久,我收到了奇·朝鲁同志于3月12日写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我现在即将退休,从今年已离岗坐休待到退休年龄时办手续。近期我们鄂尔多斯的一些老同志议论着要创立一个“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将社会上对鄂尔多斯有研究、有造诣的人士组织联络起来,对鄂尔多斯进行全方位、广角度、宽领域、多学科、高水平的研究活动,将其创立为一门学说。这个想法一经提出,得到了自治区、市级领导的重视、支持。现正在广泛联络方方面面的人士,探讨为什么要创立鄂尔多斯学,鄂尔多斯学应包括哪些学科等问题,已有了一些初步的内容。
今写此信,意在请你指点。你对鄂尔多斯研究有很高的水平,你对鄂尔多斯有深厚的感情,我们有意聘请你为高级顾问。请你不赐教,谈谈你的看法,如创立鄂尔多斯学的必要性、可行性,应设置的研究课题,研究方向定位,研究会的组织机构等方面。
这封来信,一下子激起了我心中的波澜。我在内蒙古工作近20年,是从鄂尔多斯起步的;我的学术研究活动,是从鄂尔多斯开始的;我的青春,我的事业,我的朋友,我的感情,都和鄂尔多斯紧紧相连。1987年,我调到了宁夏工作,但对鄂尔多斯依然保留着割舍不断的情怀。我没有放弃对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的研究,总是找机会奔向草原,去探究,去调查,去和老友相会。奇·朝鲁同志是我的老朋友,当年我们一见如故,相知相交20多年。我想,这是缘于我们有着相似的经历,有着共同的对事业的执著,有着那个时代我们对人生的共同追求。多少年来,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岗位,但总是相互关注着。终于等到了他的这封来信,这不是一般的问候,而是谋划一件两人早已在心中共同默默思考但又未挑明的大事。在奇·朝鲁同志的倡导下,10天之后,即3月22日,我将自己的思考写成了《关于建立鄂尔多斯学的初步建议》发给了奇·朝鲁同志。信中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闻之十分兴奋,似乎将心中久久蕴藏的模糊想法一下子挑明了。”从此,共同创建鄂尔多斯学的事业,又把我俩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我在2002年9月鄂尔多斯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说,奇·朝鲁同志虽然退居二线,但却干了一件“一线”的大事,必然会取得“前线”的成果。6年时间过去了,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在奇·朝鲁同志的领导下,围绕着鄂尔多斯学的创立,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创办刊物,出版文集,为决策咨询,搞得有声有色,鄂尔多斯学这门新兴的地方学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社会认可。地方党委和政府也把鄂尔多斯学和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当作鄂尔多斯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平台,给予支持,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一成立,我就被聘为专家委员会主任。6年来,尽管我担任着宁夏大学的领导职务,本职工作十分繁忙,但受奇·朝鲁同志和鄂尔多斯学研究会各位朋友的信任、委托,积极支持奇·朝鲁同志和研究会的工作,尽最大努力,参与并指导鄂尔多斯学的创建活动,完成了研究会交给的任务,尽力参加相关的学术活动,进行了对新时期鄂尔多斯建设发展的考察。同时,整理出版了《鄂尔多斯史论集》等著作,主编了《成吉思汗文化论集》,撰写了一些论文和文章。取得这些学术成果,使我对鄂尔多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研究也更深入了一步。
人的一生中,会有许多机遇,抓住了,就会有进步、有发展、有贡献。我虽然离开鄂尔多斯多年,但有经历的铺垫,有朋友的信任,有情感的驱使,使我又一次抓住了重新学习和认识鄂尔多斯的机会,这是我的幸运和收获。现在,我把几年来关于创立鄂尔多斯学的一些有关建议和研究文章汇集起来,编成《我与鄂尔多斯学》,作为6年来我参与创建鄂尔多斯学及研究会工作的一份学术记录,也作为与鄂尔多斯的朋友们交流的一份学习心得。我相信,鄂尔多斯学及鄂尔多斯学研究会一定会有广阔的前景,一定会越办越好。
感谢鄂尔多斯,祝福鄂尔多斯!
2008年5月
又及:当这本书稿基本汇编起来后,我应邀于2008年7月赴兰州西北师范大学参加庆贺蔡美彪先生80华诞暨“元代民族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蔡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范文澜先生编著前4册《中国通史》的基础上,主持并续编完成了5~12册《中国通史》,使之成为一部影响深远的史学巨著,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蔡先生专精辽、金、元历史,研究涉及契丹、女真、蒙古、八思巴等古文字和民族学、文字学、语言学等领域。在改革开放初期,曾担任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和中国元史学会会长,至今仍然是中国元史学会名誉会长。我在这次大会上发言,介绍了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领导我们进行的学会活动和学术活动(我当时在内蒙古社科院工作,担任中国蒙古史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以及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崇高的人品对我们的影响,表达了我们崇敬的感情。因为身体原因,蔡先生未能亲自到会。会后,我给蔡先生写信表示祝贺,同时汇报了这几年参与鄂尔多斯历史文化研究及鄂尔多斯学建设的情况,并恳请先生为《我与鄂尔多斯学》一书题写书名。时隔不久,先生复信并寄来了题写的书名,先生的毛笔字依然洒脱而奔放,似乎与这本研究草原民族的著作有着内在的风格上的默契。先生在复信中说:“近日白内障扰人,老眼昏花,书写颇不能如意,如不合用,弃置可也。”我既为因此而打扰了先生有所内疚,又为先生这种一贯的提携和帮助后学的作风而深深感动。我想,先生为这本书题写书名,不仅是对我个人的帮助,也是对鄂尔多斯学的理解和支持。
200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