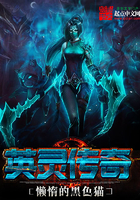《水浒传》中提到的第一个人物是宋太祖赵匡胤,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是宋仁宗赵祯,但真正作为其开篇人物的却是奸臣高俅。
金圣叹在评批《水浒传》时曾做出这样的论断:“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乱自下生出;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此言一针见血,入木三分,极有见地,但是,施公耐庵为什么选择高俅而不是蔡京或者童贯作为开篇人物呢?难道他早在七百年前就预见到了和中国足球有关的某些人会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唾弃的对象。
若论名气(当然是臭名)和地位,蔡京和童贯其实更有资格代表奸臣来充当《水浒传》的开篇人物。
就名气而言,人家老童老蔡是当时流行民谣“打了筒(童),泼了菜(蔡),便是人间好世界”的主人公,还是臭名昭著、人人喊打的“六贼”(另外四个家伙是王黼、梁师成、朱勔和李邦彦)中的首要人物,而且在《宋史》中都单独有传,相比之下,高俅则差得远,不但没有在民谣中挨骂的份,也没有得以跻身“六贼”之列,不但没有自己的传记,就是在《宋史》的《奸臣传》、《佞臣传》里也没有他的影儿,关于他的资料只能到《三朝北盟汇编》和《挥麈后录》等历史边角料里去找。
就地位而言,蔡京先后四次入相,徽宗在位的二十五年中,他竟然窃据相位长达十七年;童贯则更是了不得,虽出身宦官,却领枢密院事,任枢密使掌兵权达二十年,权倾内外,时称蔡京为“公相”,称他为“媪相”,后更因镇压方腊起义有功而被封为太师,再后来又荣升广阳郡王,成了中国历史上获得爵位最高的宦官,也是唯一一个被册封为王的宦官。而高俅虽然也是高官,位居三公之一的太尉,掌握守卫京城的几十万禁军,但毕竟只是正二品。比一品的宰相和枢密使要低。
但是,施耐庵最终却选择了让高俅以“乱自上作”的代表身份来充当《水浒传》的开篇人物,原因何在呢?窃以为,有两个理由值得考虑。
其一,高俅的发迹史颇富传奇色彩,更适于写入小说。
《水浒传》中关于高俅发迹前的描写基本上和笔记体历史《挥麈后录》的记载基本一致,只是在小细节上有些出入。《挥麈后录》是南宋时人王明清的作品,而他的外祖父曾纡的父亲就是《水浒传》中的曾布(他的妻子就是和李清照齐名的女词人魏夫人),所以,这段记载应该是非常可信的。
据王明清所言,高俅原是苏轼的小史(也就是小秘书一类的角色,《水浒传》中说是书童),他为人乖巧,擅长于抄抄写写。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从翰林侍读学士外调到中山府,临行前想把高俅送给曾布(虽然苏轼与曾布分属新旧两派,二人在元祐年间是有所交往的,而且还有着一定的交情),但是曾布婉拒了苏轼的好意,于是苏轼又把高俅推荐给了他的朋友小王都太尉王诜(即王晋卿)。
王诜是宋神宗的妹夫,端王(徽宗)的姑夫(《水浒传》中是端王的姐夫或妹夫),《宋史》中说,王诜虽然是堂堂驸马,但却是一个招蜂引蝶之辈,冷落蜀国长公主,公主后来郁郁而死,气得神宗在公主葬后立刻将王诜贬谪。不过王诜却是一个丹青书法的好手,徽宗在潜邸(以非太子身份继位的皇帝登基之前的住所)时,就常与之切磋,关系很好。
元符三年(1100年),王诜与赵佶在等候上朝时相遇,赵佶忘了带篦子刀,于是向王诜借了一个,修理了一下鬓角。赵佶用后对王诜说:“这篦子刀的样式非常新颖可爱。”王诜回道:“我最近做了两个,还有一个没用过,稍后就派人给你送去。”晚上,王诜就派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水浒传》中是玉龙笔架和镇纸玉狮子,更有文化韵味),碰巧赵佶正在园中踢毬,高俅便站在一旁看,露出不以为然之色,或许是赵佶注意到了这个小厮的神情,便问道:“你也会踢吗?”高俅倒也年轻气盛,回答说能。于是二人对踢,高俅拿出全身本领,将毬踢得如鳔胶粘在身上一般,甚合赵佶的口味,赵佶大喜,当即派人传话给王诜:“谢谢你给的篦刀,连同派来的人,我一起收下了。”高俅于是变成了端王赵佶的亲信。
更为凑巧的是,不久哲宗皇帝驾崩,作为皇弟的端王赵佶幸运地被太后选中继位,成了大宋皇帝,而高俅这个搭上末班车的潜邸“旧臣”,也鸿运当头麻雀变凤凰,一下子从一个闲散王爷的玩伴儿,一跃进入了大宋王朝的官场,并且在官场中青云直上,很快坐到了殿帅府太尉的位子上。
选择高俅作为“乱自上作”代表的第二个原因和北宋的灭亡有着密切关系。
北宋王朝走到徽宗当政时,虽然贪污漫天,腐败遍地,民不聊生,但还维持着表面上的繁华热闹,特别是在像东京汴梁这样的大城市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就是在此时创作完成的。尽管北边有宋江为盗,南方有方腊起义,实际上他们只算得上小打小闹,根本动摇不了赵宋江山的根基,如果没有女真人的悍然入侵,宋徽宗还可以继续当他的风流天子、太平皇帝;退一步讲,即使女真铁蹄打破了大宋的安宁,如果黄河以北的宋军战斗力够强,金军也过不了黄河;再退一步讲,即使黄河防线崩了盘,如果京城禁军经得起考验,北宋王朝也不会那么的不堪一击,立马玩完,那么是谁把几十万禁军彻底搞垮了呢?答案就是——高俅。
据《靖康要录》记载:“高俅……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艺工匠,既供私役,复借军伴。军人能出钱贴助军匠者,与免校阅。凡私家修造砖瓦、泥土之类,尽出军营诸军。请给既不以时,而俅率敛又多,无以存活,往往别营他业。虽然禁军,亦皆僦力取直以苟衣食,全废校阅,曾不顾恤。夫出钱者既私令免教,无钱者又营生废教,所以前日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朝廷不免屈已夷狄,实俅恃宠营私所致。”翻译成现代话,大意就是——高俅把军营的地皮建成私宅,而且很少进行训练,经常把禁军当作私役使用。如果你有手艺,就直接给高俅修建楼堂馆舍、亭台阁榭,如果你没手艺,那么只能花钱雇用工匠为高俅服务。不但如此,高俅还挪用军款,扣压禁军工资,导致家庭条件差的军士只能再找营生赚钱,这样就更没法操练了。于是,京城禁军“纪律废弛”、“军政不修”,成为“人不知兵,无一可用”的摆设,以至当国家危急,面临虎狼之师金军的进攻时,开封城内几十万的禁军很快土崩瓦解。
实事求是地说,人家高俅也不是一点训练都不搞。为了迎合徽宗皇帝志大才疏、好大喜功的心理,高俅在军队训练上玩了不少花架子,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高俅主持的军队争标竞赛是相当精彩的:(竞赛现场)“横列四彩舟,上有诸军百戏,如大旗、狮豹、棹刀、蛮牌、神鬼、杂剧之类。又列两船,皆乐部”,争标之前,先来一通吹吹打打,后面的争标竞赛,也要搞出“旋罗”、“海眼”、“交头”等各种花样,颇为热闹。徽宗看了龙颜大悦,十分满意。彼时彼刻,打死他也不会相信正是这个搞得他特爽的高俅若干年后断送了他的大宋王朝,同时也把他和他的皇子皇孙推上了去往五国城的啼泪泣血的漫漫风雪路。
从某种意义上说,北宋亡于禁军,而禁军毁于高俅,这一点和他那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发迹史一起把他捆在了“乱自上作”代表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