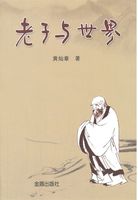快乐并不是挣扎一番、追逐一番才能得刭的东西,它就在身边,就在你脚边。快乐和善恶无关,它是超越了善恶的东西,不是善恶的结果,而是蕴含在善恶之中。有人企图以“为善”来作为快乐的途径,其实是把“善”当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正因为此,这些人也不知道什么是快乐。
十字路口的赫拉克里斯
幸福不是美德的报酬,而是美德本身。
——斯宾诺莎
古希腊的智者普罗狄库斯在他的名著《季节》中曾经讲过一个关于“美德女神”和“邪恶女神”的故事。
据说英雄赫拉克里斯长成一个青年,已经到了选择善恶的年龄。他到野外思考应该走哪条路。这时候,走来两个女人。
其中一个长的浓妆艳抹,肌肉丰盈而柔软,穿着最足以使青春光彩焕发的袍子,走路时女性体态的特征显得格外突出。用现代的话说,她生得颇富性感,一副懂得享用生命的样子。这个女人就是邪恶。
另外一个女人与邪恶不同。她长得端庄典雅,眼神谦和,气质剔透,质朴、恬美,身上装饰纯净,身穿白袍。她的眼睛天生带有湿润的忧伤,总好像刚刚哭过三天三夜似的。这个女人就是美德。
邪恶对赫拉克里斯说,她愿意向他提供各种快乐,并保证他终生不受辛劳。美德女神则对他说:如果你走我指出的这条路,将会成为人类的造福者,我将给你名望。但要知道:神不会赐予人类不经过辛劳和焦虑而得到的礼品。你只能得到自己给予的东西。
邪恶引诱赫拉克里斯说:美德除了艰难时光之外没有许诺给你任何东西。美德反驳说:你在人们满足之前给予欲望,你引诱人们奢侈、懒惰和睡眠,因为你自己也没有正事可做。你也许是不朽的,但神已经把你逐出了他们的行列。人类鄙视你,无人信赖你。受你迷惑的人贪得无厌,下场悲惨。相反,我是工匠和善行的赞助者,家庭关系的维护者,战争和和平时期的忠实同盟者。在我的庇护下,人们除了平稳地睡眠之外,还要履行义务,享受工作的乐趣。即使死了,人们也会记住他们光荣的名字。
最终,赫拉克里斯听从了美德女神的教诲,结果成为了举世闻名的大英雄。
“延伸阅读”
在哲学家眼里,幸福具有终极性,它是人生最后的目的。比如,我们就不能问:“我们追求幸福是为了什么。”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那样:“既然目的是多样的,而其中有一些我们为了其他目的而选择的,例如钱财、长笛,总而言之是工具,那么显然,并非所有目的都是最后的目的。只有最高的善才是某种最后的东西……总而言之,只有那种永远因自身而被选择,而绝不为它物的目的,才是绝对最后的。看起来,只有幸福才有资格作绝对最后的,我们永远只是为了它本身而选取它,而绝不是因为其他别的什么。”
在上面那个故事中,邪恶女神与美德女神的“幸福”都以美为本。但是,“美德”以美的心灵作底,“邪恶”却以美的身体为基。享乐和美好尽管都是幸福,质地却完全不同。幸福与幸福也是有区别的——一个是邪恶的幸福,一个是美德的幸福。肉体对于这两种幸福的感觉也不同——邪恶的幸福感觉是轻逸,美好的幸福感觉是沉重。这无疑是在说明:幸福不是毫无重量的享乐,而是沉甸甸的承担。
斯宾诺莎说:“幸福不是美德的报酬,而是美德本身。”幸福本身就是美德,而不是美德的附属品;美德不是成就幸福的手段,如果为了所谓的美德而牺牲了幸福,那将是颠倒本末的愚蠢做法。人类历史中有很多幸福的灵魂,他们之所以最终获得了幸福,是因为他们对责任的坚决承担。这一点可以说是毫无例外。当我们背负着沉重及其担当走向幸福的灵山时,沉重即成为孙猴子头上的紧箍咒,拥有幸福的一刹那,沉重和幸福突然变得并不矛盾,并不陌生,枷锁突然解脱,幸福竟是如此轻盈,原来,沉重不是必然,幸福才是沉重的必然,我们寻寻觅觅的终南捷径从来就未存在,我们的担当竟然通向了幸福!
吾与点也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孔子
孔子让他的弟子们谈谈自己的志向,只有曾皙的回答最让他满意。曾皙是这样说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场景好像今天我们所说的春游:在春天快要结束的时候,穿上春季的服装,几个大人,领着几个孩子,沐浴在大自然的美好风光和新鲜的空气里,在“吹面不寒杨柳风”中翩翩起舞,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然后唱着歌走在回家的路上。你看,何等的惬意!而孔子之所以夸奖曾皙,正是认为做人就是如此地轻松简单,而非要摆出一幅很沉重的模样来。
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快乐并不是挣扎一番、追逐一番才能得到的东西,它就在身边,就在你脚边。快乐和善恶无关,它是超越了善恶的东西,不是善恶的结果,而是蕴含在善恶之中。有人企图以“为善”来作为快乐的途径,其实这种观点是苍白的,它仅仅是把“善”当成了手段,而不是目的!正因为此,这些人也不知道什么是快乐。
据《荀子·宥坐》记载:有一次,孔夫子与众弟子们在陈、蔡的地方被围困,连续困了七天,没有食物可以吃。弟子们都饿红了眼,尤其是子路,还闹起了情绪。他质问老师:“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是老师您一辈子累德、积义、怀美,为什么却总是遭遇厄运呢?”听了子路的牢骚,孔子狠狠地批评了他:一个人是否成就外在的事业,并不是品德、学识、努力就能见效的。具备这些条件之外,要成功还需要“时”,即机会。而事实上,怀才不遇的人总是占大多数的。君子需要的只能是“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情况可能根本就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些做了恶事的人可能更有了好的结果,相反,那些积德行善的人命运可能却是很糟糕。面对这种情况,难道我们就不去行善了吗?难道我们就要去作恶吗?这个结论显然是荒谬的。孔子一再告诫我们:仁义并不是手段,它本身就蕴含着幸福,那些做了错事的人,那些不施仁义的人,我们之所以批评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做了错事,而是因为他们在这种恶的行为中并没有感觉到幸福。
“延伸阅读”
“吾与点也”,孔子通过他的志向向世人表明:他并不是一个死板的哲人,终生也在寻求快乐。而他与子路的对话则是在告诉我们:个人应该在自己的努力和奉献中体悟担当感带来的乐趣,而非要为了得到外在的福祉。如果你没有得到福祉,那仅仅是“遇”或者说“命”,而不能由此而放弃努力,否则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而孔子也正是践行了自己的这一理念。他一生对成败看得很淡,虽说在老时也有“梁木摧乎?泰山颓乎?哲人萎乎”这样深重的叹息,但孔子未曾绝望过。他并没有把仁爱的实现留给后人就完事,而是生前就积极地行仁义。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则更表现了其在过程中获得的快乐远远要胜于其对结果的关注。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整天瞻前顾后、费尽心机、左顾右盼、焦虑成性的人哪里会有幸福可言呢?所以,至高的境界并不是强迫着自己去行善,而是要在行善的过程中感到幸福。唯有此,才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孔子说“求仁则得仁”、“观过则知仁”,正是表达了这种“快乐”的至高境界。这种“快乐”不是解决了一些矛盾之间的对立,而是将这些矛盾化为乌有。
人何以如此轻松自在呢?那就是进入到快乐之中,而非把快乐当作一种结果来追求。所以孔子说:“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这里的“乐”就是快乐,而快乐已经超越了认知、逻辑和善恶,进入了一种审美的境地。就好比我们在玩一个网络游戏,我们已经进入到游戏之中了,而非外在地去观摩这个游戏。爱因斯坦曾经有过一个形象地比喻:“鱼儿对于其终生游泳于其中的水又知道多少呢?”快乐也是如此,真正感到快乐的人不会去追问快乐的意义,更不会知道快乐有什么用,正像鱼儿不知道水对它意味着什么一样。佛家有语说:“日用而不知。”那些我们不知道的,恰恰是对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正如鱼儿对水一无所知一样。
搁浅的旅行
并不是因为我们克制情欲,我们才享有幸福,反之,乃是因为我们享有幸福,所以我们能够克制情欲。
——斯宾诺莎
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艘船在航行途中遇到了强烈的暴风雨,偏离了航向。到了次日早晨,风平浪静了,人们才发现船的位置不对,同时,大家也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一个美丽的岛屿。于是,船便驶进海湾,拋下锚,作暂时的休息。
从甲板上望过去,岛上鲜花盛开,树上挂满了令人垂涎的果实,从美丽的绿荫中,传来小鸟无比动听的歌声。于是,船上的旅客自然而然地分成了五组:
第一组旅客认为,如果上岛游玩时,正好出现顺风顺水,那就会错过起航的时机。所以,不管岛上如何美丽好玩,他们坚持不登陆,守候在船上。
第二组旅客急急忙忙地登上小岛,走马观花地闻闻花香,在绿荫下尝过水果,恢复精神之后,便立刻回到船上来。
第三组旅客也登陆游玩,但由于停留的时间过长,在刚好吹起顺风之时,以为船要开走而慌里慌张赶回船上。结果,有的丢了东西,有的失去了好不容易才占下的理想位置。
第四组的旅客虽然看到船员在起锚,但没看到船帆也在扬起,而且以为船长不可能扔下他们把船开走,所以,一直停留在岛上。直到船要起航时,他们才急急忙忙地游到船边爬上船来。其中有些人为此受了伤,直到航行结束,也没有痊愈。
第五组游客由于在岛上陶醉过度,没有听到起航的钟声,也没有看见扬起的船帆,都被留在了岛上。结果,有的被树林里的野兽吃掉,有的误吃了有毒的果实,有的因饥饿因恐惧而衰竭,最后全部死在岛上。
“延伸阅读”
上面我们看到的这个小故事,具有很强烈的象征意义。故事中的船,象征着人生旅途中的善行,岛则象征着快乐,各组的旅客象征对善行和快乐持不同态度的世人。
第一组战战兢兢,行为谨慎,对人生的快乐一点儿不去体会;第二组的人既享受了少许的快乐,又没有忘记自己必须坐船前往目的地的义务,可以说是最具有智慧的一组;第三组的人虽然享受了快乐也赶回到了船上,但还是吃了些苦头;第四组的人也勉强赶回船上,但伤口到目的地还没有愈合;人类最容易陷入的是第五组的处境,即为了一时的快乐,为了瞬间的陶醉,为了感官的刺激,为了欲望的满足,忘乎所以、放纵无度但还执迷不返。就像船上第五组的那些旅客,为了一时的快乐而忘记旅途,忘记了大海,忘记了生存,忘记了未来,他们的结局是可想而知的。
幸福是什么?斯宾诺莎曾告诉我们:幸福就是人通过认识真理把握自然和人的关系,而后用理性去战胜、控制情感,做情感的主人。正如他所说,理性强、智慧高的人,都能够从爱和幸福出发,通过对欲望的适当克制,再回到爱和幸福。正如我们上面所看到的第二组旅客。而那些离开幸福去盲目克制欲望或对欲望不加任何克制的人,都不是最明智的人,他们根本不可能得到幸福。正如我们上面看到的第一组和第五组的旅客。
善行与享乐常常是难以两全的。与其想用坚强的毅力战胜和克服享乐的“毒瘤”,倒不如发现、挖掘一些高尚的兴趣,并用它占据心灵。正如斯宾诺莎所说:“幸福不是德行的报酬,他就是德行本身;并不是因为我们克制情欲,我们才享有幸福,反之,乃是因为我们享有幸福,所以我们能够克制情欲。”
所以,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这样说,克制享乐,是为了获得更大的享乐。人是为了享有幸福才自觉克制情欲的。而克制情欲的本身,就是为了享受幸福。这就是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一个成熟的人与一个愚昧的人的区别,是一个高尚的人与一个卑劣的人的区别。
孔颜乐处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知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孔子
孔子号称弟子三千,但他最喜欢、最欣赏的是颜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颜回将孔子的“乐道”思想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出来。《论语·述而》载: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说,吃着粗粮,饮着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这也充满乐趣。用不义的手段得到富贵,对于我好像浮云那样转瞬即逝而无足轻重。又载孔子对自己的描述是:“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发愤学习和教学,是最大快乐,自觉年轻多了,忘了自己渐渐地老了。
这里的“安贫乐道”,不是打肿了脸充胖子,更不是为了平衡的阿Q精神,而是一种因为摆脱了外在欲求而在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快乐。因为摆脱了外在的限制,这种快乐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而不是强颜欢笑,更不是皮笑肉不笑。在孔子看来,在他的弟子当中,只有颜回体验到了这种快乐。孔子这样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知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意思是说:颜回用非常简陋的竹器吃饭,用瓢饮水,住在陋巷,别人受不了这种困苦,颜回却不改变乐观态度。
颜回在生活贫困不堪的情况下,仍能快乐地一心向道,得到了孔子的称赞。这就是被历代儒家哲人所津津乐道的“孔颜乐处”。对于孔子、颜回这样品德高尚的人来说,快乐已经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精神情操的追求。这种由孔子开创的乐道思想,也并不是简单地以道为乐,而是指人达到与道为一的境界所自然享有的精神快乐。这种快乐因为超越了物质的欲求,因而不再受外在物欲的羁绊,从而实现了一种更高层面的精神快乐。这种快乐不是对物质欲望的满足,而是对其的超越和消解。
孔颜乐道的精髓,正在于此。
“延伸阅读”
人是天使和魔鬼的结合体,一面是肉体,要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另一面是精神,自由飞翔,无拘无束。一方面,人的自然本质决定了人在物质贫困中要遭受痛苦。另一方面,人的精神又引导人对物质贫困造成的苦痛进行超越。于是,这两种张力共同作用造就出来的审美境界——“孔颜乐处”,就成了衡量现实生活中人的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的分水岭。
能够满足生理性的感官欲望固然可以获得快乐,但是这种依靠感性欲望或者目的驱使而取得的快乐是“乐在其外”,“乐不归己”,它是不自由的,是转瞬即逝的,它的实现是建立在功利性根源上的,一旦功利性被满足或无法实现,都会造成更大的痛苦,因此只是一种低级的庸俗快乐。只有如孔子、颜回那样超越感官性欲望追求,进入崇高审美境界的主体内在之乐、自由之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快乐。因为没有功利性的源泉,这种快乐当然可以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境界。
孔颜乐处,乐在何处?对这个问题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许多参悟,到了现代才有人对此做了总结。冯友兰先生说,人生可以有四种不同的境界: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是人的一种本能反应;功利境界则多了一些算计、规则;道德境界在功利之上,又加上了许多道德要求;天地境界是人生的一种最高境界,天人合一,“浑然与物同体”。孔老夫子与颜回之所以快乐,就在于他们达到了天地境界,并且对这一境界有高度的自觉。每一位想有“孔颜之乐”的人,都应努力使自己的人生达到天地境界。
有报道说,根据有关方面的调查,财富的增加与人们的幸福感并不成比例,在人们追逐财富的过程中,获得幸福的能力已逐渐被弱化,一个现代人可以自豪地对古人说:“我比你富有多了。”但他却不敢肯定地说:“我比你幸福多了。”这就是现代人的可悲之处,因为现代人只是在自然境界与功利境界之间徘徊,偶尔有一次忽发善心迈进道德境界的门槛,自己都会被自己所感动。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不能自拔,不知“孔颜之乐”为何物,这已成为人类生活的一大难题。
伊壁鸠鲁的快乐
幸福就是肉体无痛苦,灵魂无纷扰。
——伊壁鸠鲁
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将快乐与道德结合在一起的是哲学家伊壁鸠鲁。
伊壁鸠鲁的哲学以获得人生的快乐和幸福为目的,对于他来说,哲学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根本性的心灵医治术。他坚持认为快乐与痛苦的感觉是人们衡量善恶的尺度。凡是能带来快乐的东西就是善的,凡是给人带来痛苦的东西就是恶的。既然生物都有趋善避恶的习惯,那么人类当然也不例外。一个渴望幸福的人,必须培养正确选择快乐的才能,只有那些能够增进个人快乐的行为,才是具有道德意义的。
伊壁鸠鲁认为,真正的快乐更多地来源于心灵,而不是肉体;主要依赖的是心理,而不是生理。因为在肉体上,“痛苦并不会持续太久,相反,极度痛苦的出现都是为时甚短的,仅仅超过肉体快乐的痛苦也不会持续多少天。即使是久卧病榻,其肉体上的快乐也超过痛苦。”
伊壁鸠鲁并没有否定肉体上的快乐和痛苦。他说,肉体上的快乐无可非议,但是,如果单纯追求肉体的享受而极力追求它,是不会带来幸福的,因为“肉体把有限的快乐当作无限,提供它则需要无限的时间。但心灵认识到肉体的终极界限,排除了对未来的畏惧,保证了圆满和完美的生活……即令遇到不幸而丧生时,心灵也不欠缺对最好生活的享受”。肉体上的感受都不会长久,无论是痛苦还是快乐。所以,真正的、永恒的快乐只能到心灵中去寻找。正如伊壁鸠鲁所说,心灵的快乐超越于肉体上的快乐。人生的真正目的不是把强烈的肉体快乐刺激永恒继续下去,而是达到一种宁静之态。
“延伸阅读”
伊壁鸠鲁的“快乐清单”超越了时空,对今天的我们仍然不乏醍醐灌顶的启发和警示。因为在这个物质利益压倒一切的时代,人们已经不自觉地将快乐与金钱等同起来,把金钱看作了快乐的代名词。人们往往以为,钱越多快乐就越多。这真是天大的误会。不错,拥有了财富和金钱,我们可以吃尽山珍海味,游遍大好河山,但心灵的空虚在外在追逐中已无暇填充,它就像一颗定时炸弹,往往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袭击我们。
曾经读到过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说在隆冬来临之前,在深秋的田埂上,有三只小田鼠忙忙碌碌地为过冬做准备。第一只田鼠就拼命地去找粮食,把各种谷穗、稻穗一趟一趟地搬进田鼠洞;第二只田鼠就拼命地去找御寒的东西,把很多的稻草棉絮都拖到它的洞里;而第三只田鼠呢?就一直在田埂上悠悠荡荡,一会儿抬头看看天,一会儿抬头看看地,一会儿躺一会,弄得它的那两个伙伴一边在忙活,一边在指责它,说你看你这么懒惰,你也不为我们的御寒过冬做准备,那真到了冬天怎么办呢?你看看你这么游手好闲!这只田鼠也不辩解。
后来冬天真的来了,三只小田鼠挤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小耗子洞里面,在过冬的时候,发现吃的东西不愁了,御寒的东西也都齐备了,然后每天在这里无所事事,大家终于变得百无聊赖了。当大家开始难受得要命的时候,第三只田鼠开始给那两只田鼠讲故事,它说,就在那样一个秋天的下午,我在田埂上遇到了一个孩子,他在做什么;又在那样一个秋天的早晨,我在水池边看到一个老人,他在做什么;我曾经听到人们的对话,我曾经听到鸟儿在唱什么样的一种歌谣,所有的这些我当时都记录下来了。其实到这个时候,那两个伙伴才知道,这只田鼠为大家储备了过冬的阳光。也就是说,这种表面看起来毫无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在这个时候会给人心一个淡定的支点。
原来,精神的需求对人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原来,越是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越是决定我们的生存,尤其是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可现代人好像遗忘了这一点,他们拼命地追逐物质利益,但却放逐了自己的心灵。当他们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寄托在吃、穿、住、行这些物质享受方面的时候,唯独放弃了思的权利,忘记了真正的愉悅总是来自人的心灵;他们不知为何而来,也不知为何而去;他们只知道索取,却从不想想究竟在向谁索取;他们只接受所谓道德的非人桎梏,却放任自身的神性渐渐地丧失;他们只看到别人的可笑,却不感到自己灵魂的猥琐;他们只盯住一点点立竿见影的蝇头小利,却阉割了活泼得犹如孩童般的精神;他们只在意眼前一点点的得失,却从不肯留心听一听远方的召唤……他们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可是,当这些物质利益都得到满足以后,他们心灵上所产生的空缺就会马上显露出来。就像上面的那两个小田鼠,虽然过冬的一切“有形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但却要忍受没有“精神食粮”的煎熬。试问,在今天这样一个物质高度发达的时代,又有谁在为了吃不饱、穿不暖而忧心忡忡呢?孤独、寂寞、忧郁这些像瘟疫一样的情绪时刻袭击着我们,好像都和物质无关。
专家们早就指出:“今天,人类已经从传染病时代,身体病症时代进入了精神病时代。”一个健康的人、成功的人,首先应该是一个能意识到自我,但又不执着于自我的人。喧嚣的都市,繁忙的生活,人们在日复一日的紧张忙碌中逐渐淡忘了自我,只有在寂静的深夜,心绪才会偶尔伴着微凉的夜风飘进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空间。既然我们已经意识到,为什么不行动起来呢?关注自己的精神世界,经常性地清理一下自己的私密空间。也许,只有通过心灵的按摩之后,人们才能去面对那早已久违的自我。
生无所息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孔子
《列子》中曾记载着孔子和他的弟子子贡关于“学习”和“生命”之间关系的一段对话:
子贡倦于学,告仲尼曰:愿有所息。仲尼曰:生无所息。
意思是说,子贡学习累了,想休息一下。但他的老师却告诉他,生命本身就不停息,何谈停止学习呢?只要你的生命在延续,你就需要“学习”。在人的本根处,学习是一个持续终生的“修身”和“社会化”的过程。既然“生无所息”,学习也永远不会停止。因为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这个不断学习、不断追求的过程之中。
由此,孔子说:学无所固。学习没有固定必须要学的东西,因为学习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什么目的的手段。孔子反对学习的异己化和功利化,强调真正的学习是“为已之学”,所谓学习为己,而非为人,正是这个意思。学习没有专业之分,没有门派之别,没有地点的限制,没有时间的阻碍,人生处处皆学问,人能弘道,道也能弘人。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有人说,这是孔子谦虚、好学,不耻下问。其实,孔子已经把学习看作了内在于生命的东西,看作了生命的愉悦和人生意义的展现,所以才把学习看作发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事情。如果非要把此于今天我们所谓的“谦虚”、“好学”这些字眼联系起来,就太小看了孔子了。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而又经常复习,为什么会感到快乐呢?今天的我们在翻译这句话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们在复习旧知识的时候,感到的却是索然无味,而没有感觉到快乐呢?原因很简单,你没有把学习看作生命,没有把学习看作“成人之道”,总是想着学完知识以后去干点别的,自然不会有快乐了。
“延伸阅读”
孔子说:生无所息。亚里士多德也说:人的本性在于求知。这两位伟大的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洞察了生命的本质,即在一种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中获得生命的愉悅。正因为此,孔子70岁才达到了“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所谓70岁,其实只是一个形象的表达,对人生至高境界的一种表达。因为孔子本人活到72岁就去世了。如果孔子能活到80岁,他在70岁以后就不需要学习了吗?非也。假使天假孔子之年,让孔子更为长寿,他依然还会继续不懈地自我完善,以致其生命更为丰富和多姿多彩。17世纪儒者孙奇逢的例子是发人深省的。他长期不断的自我反省,使得他在90大寿时能够察知自己89岁时在言行上的失误。他甚至略带幽默地在自己的弟子们面前谈论说:只有在他过了80岁之后才意识到自己70岁时的年幼无知。
这种学习,这种反省,因为超越了伦理,超越了逻辑,超越了善恶,因此是唯一隶属于人的生命自身的。而从中获得的愉悅,也才是本真的。孔子对“人性”是闭而不谈的,他不像后来的孟子和荀子一样把人性描绘成善的或者恶的。因为无论说人性善,还是人性恶,都是一种认知态度,都是一种外在的观看,而非进入人的生命本身。用佛家的术语说,这叫“执著心”,而“执著心”是不会有快乐的。因为你执著的东西无论得到还是得不到,你都在快乐之外了。
正是这种对生命本质的深刻洞察,孔子才能进入“三月不知肉味”的快乐境地。正如我们在大剧院里看一部著名的歌剧,被里面的情节所感染,周围的一切都已经变得模糊,完全融入到歌剧的情节中了,打成了一片,哪里还有善恶和是非?著名美学家宗白华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大剧院正在上演一幕悲剧,所有的人都被里面的情节所感动,不同程度地发出了抽泣声。其中有一个人竟然嚎啕大哭,当大家都把目光朝向这个人时,惊呆了:原来这是一个多年被通缉的江洋大盗!
这也许才是生命的真谛。今天我们的知识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在人生意义的追求方面却遗忘了古人的教诲。放眼望去,在这个超级急功近利的年代,我们又有多少行为没有一个功利的目的?我们又把什么看作了视之为生命的东西?我们的目的性太强了,以至于离目的越来越远。佛语不说吗?无心恰恰用,有心恰恰无。可惜,今天的我们,“无心”的太少,“有心”的又实在太多。
逝者如斯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周易》
孔子去郊游,站在桥头看到下面的流水说:“过去的就像这下面的流水一样,白天晚上都在流。”
这两句话的文学气息非常重,全部《论语》中,最富于哲学意味的,也就是这两句话。从这里,有几个要点可以了解。
第一,道家思想方面,老子也和孔子这个观念一样,经常用水代表人生哲学。老子教我们效法水,中国有一句老话“人往高处爬,水向低处流。”老子教我们学下流——不是普通所指不高尚的下流,是指水的下流——大海。天下的水都向下流汇归成大海。所谓下流,就是谦下,站在最下面,“人之所弃,我则取之。”人要有容量,像大海一样包罗万象。老子又教我们“上善若水”,最高的品德像水一样。道家形容水很妙,水是绝对干净的,脏的东西到水里,都被水沖洗干净了。让我们的心境,以及人品的修养,效法水一样,冰清玉洁,不受一点尘埃。虽然容纳了许多废物、污垢,但仍然是水,水的性质没有变,而且永远自强不息。
第二,佛家也说过水,我们看到流水,永远只是一股流水而已。照佛学的分析,人的心理就和流水一样,如说“滚滚长江东逝水”,永远在流,真的吗?错了。等于看到电灯光,说它一直亮着,也错了。当我们看到一个浪头的时候,事实上这个浪头已经过去了,是接上来的另一个新浪头,当在看到这新的第二个浪头时,它又已经过去了。灯光也是一样,当我们刚一打开开关时,所发出的光波已经消失了。
我们的思想、感觉、年龄、身体,当一个钟头乃至一分钟前坐在这里的我,与此刻坐在这里的我,已经不知道经过多少变化了。所以“今我非故我”,现在的我已经不是前一分钟的我了。都过去了,像流水一样,不断地向前去。
所谓“江水东流去不回”,历史永远不会回头,时间永远不会回头。人生永远像浪头一样,一波又一波地过去了,要想拉回来是做不到的。这些都是另一面的说法,也可以说是消极的人生,许多宗教家、哲学家,都从这一面看,花落了再不会开了。
“延伸阅读”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听起来非常悲观,它在不留情面地告诉我们:所有的终将成为过去,而且是一去不复返。“林黛玉葬花”是《红楼梦》中著名的一个故事。这位小姐病兮兮的,花落了还要去收回来,还要葬下去,情调非常美,文章也作得很好,葬花词名句:“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这么样子的林黛玉!怎能不生肺病?怎么不那么痴迷的死?你管他谁葬你,死了就死了。说到这里,龚定庵的诗就比林黛玉高明多了,他的诗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但孔子并没有以悲观的态度来说这句话,而是看到了其中乐观、积极的一面:人生如流水一样,不断的向前涌进。
人生像流水。我们可以想象:孔子所以站在上流告诉学生们:“注意呀!你们看这水,过去的都像这样,向前面去!向前面去!而且是昼夜不断地向前去。”
他这话的意义,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人生也是这样,要不断求进步。静是缓慢的动态,没有真正绝对的静。譬如人坐在椅子上好像很静,其实并不静,身上的血液正在分秒不停地循环,各个器官也都各司其职地工作着。
“天行健”是永远强健地运行。“君子以自强不息”是教我们效法宇宙一样,即如孔子所说“逝者如斯”,要效法水不断前进,也就是《大学》这部书中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道理。人生思想、观念,都要不断的进步。满足于今日的成就,即是落伍。所以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句话,包括很多意义,可以说孔子的哲学,尤其人生哲学的精华,都集中在这两句话中,它可以从消极的、积极的看,看宇宙、看人生、看一切。我们自己多多去体验它,应该了解很多的东西。
历史是不能停留的,时代是向前迈进的,宇宙如此,人生也是如此。
斯芬克斯之谜
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被判了死刑,但是都有一个不定期的缓刑期;我们只有一个短暂的期间,然后我们所呆的这块地方就不再会有我们了。
——雨果
在希腊神话故事里,有一个狮身人面的怪兽,名叫斯芬克斯。它有一个谜语,询问每一个路过的人,谜面是:“早晨用四只脚走路,中午用两只脚走路,傍晚用三只脚走路。”据说,这便是当时天下最难解的斯芬克斯之谜。如果你回答不出,就会被它吃掉。它吃掉了很多人,直到英雄的少年俄狄浦斯给出谜底。
俄狄浦斯的谜底是“人”。他解释说:“在生命的早晨,人是一个娇嫩的婴儿,用四肢爬行。到了中午,也就是人的青壮年时期,他用两只脚走路。到了晚年,他是那样老迈无力,以至于他不得不借助拐杖的扶持,作为第三只脚”。
斯芬克斯听了答案,就大叫了一声,从悬崖上跳下去摔死了。俄狄浦斯猜中了斯芬克斯之谜,其实就是人的谜、人的生命之谜。
这正是西方人对于生命的理解:无论是刚刚出生的婴儿,还是身强力壮的青年,还是进入垂暮之年的老人,他都要行走,尽管行动的方式有所差别,但行动本身却成了人的存在方式。
人总是通过不断重复的行动来诠释生命意义。但是,人的行动又是毫无意义的。正如我们上面提及的西西弗斯,他命中注定要永远推着一块巨石上山,当石块靠近山顶时又滚下来,于是重新再推,如此循环不息……
公元前342年,亚历山大率领一支军队东征到达埃及。他们在雄伟壮丽的金字塔前面,赫然发现了一座巍然耸立的狮身人面像。这些希腊人被惊得目瞪口呆,他们立即把这座狮身人面像命名为斯芬克斯。
据说,古代埃及的法老们之所以建造金字塔,是因为他们需要一座上天的梯子。他们以为,金字塔就是一座上天的梯子。马斯洛也说,你也应该建造一座金字塔,像法老们一样登上天去。
但是,人真的能够通过金字塔登上天去吗?斯芬克斯蹲在那里,似笑非笑地看着你,像是一个永恒的谜。
“延伸阅读”
“斯芬克斯之谜”和西西弗斯的神话故事,并没有给西方人带来悲观。正如“逝者如斯”的生命之流没有给中国人带来悲观一样。孔子说,生命就像一去不复返的流水一样,不舍昼夜。所以,我们每个人就要像流水一样,不断地超越自己,自强不息。而对于俄狄浦斯的故事,西方人照样从近乎消极的悲观中解读出了积极乐观的结论。1824年1月27日,风烛残年的歌德在同爱克曼交谈的时候回顾了自己的一生,期间就提到了这个西西弗斯的故事。他说:
“人们通常把我看成是一个最幸运的人,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对我这一生所经历的路程也并不挑剔。我这一生基本上只是辛苦地工作。我可以说,我活了75岁,没有哪一个月过的是真正舒服的生活。就好像推一块石头上山,石头不停地滚下来又推上去。我的年表将是这番话的清楚说明。”
同样劳累、忙碌但又幸福无比的还有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这位堪称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是这样来描述“人”的:
我们吃别人种的粮食,穿别人缝的衣服,住别人造的房子。我们的大部分知识和信仰都是通过别人所创造的语言由别人传授给我们的……个人之所以成其为个人,以及他的生存之所以有意义,与其说是靠他个人的力量,不如说是由于他是伟大人类社会的一个成员,从生到死,社会都在支配着他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爱因斯坦逝世前不久,他对友人说:“只要有一天你得到了一件合理的事情去做,从此你的工作和生活都会有点奇异的色彩。”的确,爱因斯坦一生之所以能朝气蓬勃,光霁日明,都是因为他总是在做一件件合理的事情。对于他,生与死的区别仅仅在于是不是在研究物理学问题,是不是在思索大自然的统一结构,是不是在不断地接近“他”,即接近斯宾诺莎的上帝——自然。正是这种“追求”,而不是“占有”成就了一个伟人,也成就了一个幸福的人。
天籁之音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庄子
康德曾经对“美”有过精辟地定义:“美是没有目的性的合目的性。”这话听起来绕口,其实很简单。意思是说,所谓美,是没有目的的,你不能把美当成一个目标去追求。你可以追求功名,你可以追求金钱,但你千万别去追求美。你越追求,它反而越不美了。美就是“可遇不可求”,美就是想象力的驰骋,美就是无拘无束的自由。一旦没有功利的目的,也就成全了美自身,有了美的目的。所以说,美是没有目的的合目的性。
在《齐物论》中,庄子曾通过“天籁”、“地籁”、“人籁”的比较生动地佐证了康德的这一定义。所谓“天籁”,就是自然界自身发出的各种声响,比如风声、水声、鸟声……属于“天籁”的声音千奇百怪,五花八门,有的像人的鼾声,有的像动物的吼声,有的声音根本无法比拟,原始而丰富,无论多么高明的乐官,多么精巧的乐器,都演奏不出来。它们之所以如此精妙,就在于它们都是无目的地发出来的声音,完全来自于天工造化。庄子说:“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耶?”天籁虽有万般不同,但使它发生和停止的都是它自身,发动者还能是什么呢?没有人强迫这种声音发出,背后没有人工的痕迹,没有人为的修饰,它们的出现毫无目的,完全出于自然和偶然,完全是自由的化身。
“地籁”就不行了,它是大地上各种孔洞发出的声音,内容虽然仍然很丰富,但却再也不是“天地相参”的产物了。“人籁”就更退化了,它是演奏者通过乐器演奏出来的,是人为强迫地发出的声音,不仅单调,而且贫乏。“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比如,我们无法用乐器演奏人的哭声、狂笑、叫嚣……我们也无法演奏社会行为之声,比如兵刃相交的叮当声、战机的轰鸣声、炸弹的爆裂声……正是有了乐官,有了六律,有了人为,有了目的,丰富的“天籁”才变成了“人籁”。
“延伸阅读”
庄子笔下的“天籁”,完全来自自然,没有经过加工,没有经由乐器,是“无为”之物。但正是这种“无为”,使得“天籁”异常丰富。庄子所说的天籁,“似鼻、似口、似耳、似笄、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者、叱者、吸者、叫者,者,者、咬者”,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我们能感觉到的,仅仅是九牛一毛而已。
对于风声,庄子的《齐物论》、宋玉的《风赋》、欧阳修的《秋声赋》已经描写得很精彩。“天地之气,溥畅而至,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焉。”(宋玉《风赋》)风的声音,哪里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哪里会嫌贫爱富、嫉贤妒能?“初淅沥以潇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纵纵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欧阳修《秋风赋》)什么样的乐器,什么样的乐手,能演奏出如此奇妙的声音?风在地球上刮了亿万年,只有大文豪、哲学宗师才能捕捉到风的意境,进而把它和宇宙之理,和人事之理联系起来。
天籁一旦进入他们的大脑,就与情感掺合起来,使天籁获得了生命,得以提升。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外在世界尽管五彩缤纷,但对我毫无意义可言。唯有一个自由的心灵,一份豁达的心情,一种虚静的状态,世界的美感才会向你迸发,目不暇给地出现在面前。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天上”的靡靡之音又是来自哪里呢?是乐手演奏出来的吗?是乐器发出的声响吗?不是,绝对不是,其实很简单,就是放下你人为的负担,竖起耳朵来就可以了。你静坐休息,属于你的“靡靡之音”就会不期而遇。只可惜现代人心浮气躁,不良“人籁”窒息了人的心灵,远离了自然的天籁,更别说去领会乐圣们阐发的天籁了。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德彪西的《海》,雷斯皮基的《罗马的松树》……又有几人愿意去倾听呢?
每次读庄子,总能令人兴奋。因为他的理想是回归“天地之大美”,而“天地之大美”是“不称”的、“不言”的,它契合的是人的无限可能性和世界的无限丰富性。也许,只有远离乐器、远离人工、远离机械的古人,才能真正体会什么才是真正的“天籁之音”,也才能作出流传千古的诗句。而今天的我们,也许只能到练歌房去麻木于“人籁”,已经无暇去聆听“天籁”了。即使听到了,麻木的感官也无法发现真正的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