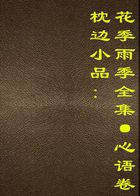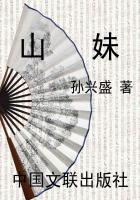曾几何时,围绕着《读书》杂志和《读书》“换帅”问题,文界产生了不少争论,讨论先是关注于近十年来《读书》的办刊思想,对此存在着很大争议,争议还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现任主编汪晖。到了“换帅”尘埃落定,讨论进一步升华为对体制官僚化的讨伐和对汪晖的同情,对所谓的“新左派”和“自由派”分裂进行冷静分析,这其中不乏理性声音。但总起来看,围绕着《读书》和《读书》“换帅”事件,不少人表现出了过度焦虑。他们一方面忙于表态,给予汪晖道义上的支持,在近日上海召开的“《读书》十年(1996—2005)文选座谈会”上,与会学者力挺汪晖时代的《读书》,为现在的《读书》进行辩护。华东师范大学王晓明教授、倪文尖教授、复旦大学张汝伦教授、上海大学蔡翔教授等都有此类支持言论。
而在北京由乌有之乡书社主持召开的“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学术和《读书》座谈会”上,北京诸高校的著名学者们把《读书》“换帅”的矛头指向了三联当局以及官方,以此来表达对三联当局突然采取措施操控《读书》“换帅”的忧虑。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则将《读书》“换帅”和去年的“冰点事件”以及今年的“禁书事件”相联系,提出“这次撤换主编就是要排除它(《读书》)的民间性,挤压思想的自由空间,将其变成一个由文化官僚直接掌控的名副其实的体制内的刊物,正是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收编”。孔庆东、韩德强对此也作了进一步的阐发。
忙于表态的同时,在另一方面,不少人还顺带着打击了一下“自由派”。
其实,《读书》以及《读书》的“换帅”根本不是什么派别的问题,而是体制内办刊思路调整的需要。当然我们也可以由此引申到体制对自由的挤压,但最能说明问题的恐怕还是“将来”《读书》的表现。如果“将来”的《读书》
还能够继续保持着“从前”和“现在”的风格,那眼前的争论将成为毫无意义的“一腔废话”。至于“将来”的《读书》会不会保持以前的风格,也许我们可以从《读书》的“前世”“今生”和它的办刊规律中看出端倪。
一、《读书》的“前世”
《读书》杂志1979年4月创刊于北京。
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不久,思想界、出版界异常活跃,于是,一些屡经沧桑的老人陈翰伯、陈原、范用、冯亦代、史枚、倪子明、丁聪等集合在一起,办起了《读书》这本思想评论杂志。他们在杂志创刊伊始就突破书评杂志定位,决意要把《读书》办成“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
在当年的环境中,这个想法遭到多方阻拦。一位党内的宣传老干部曾经对沈昌文说过这样的话:谁叫你们办思想评论杂志,思想评论我们已经有了《红旗》杂志嘛。其实,对于《读书》杂志的创办方三联书店而言,办读书类杂志一直是他们的传统。早在1934年,艾思奇、李公朴曾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后遭国民党查禁。三四十年代,范用先后在重庆和上海参与编辑《读书与出版》、《读书月报》和《读书生活》,《读书》杂志的几位发起人——陈原、陈翰伯、倪子明,都或多或少地参与过这几本杂志的相关工作。
《读书》杂志一直被学术界认为是最先锋的一本杂志,沈昌文主事期间的《读书》杂志更是被标举为思想阵线上的新锐。在沈昌文接任《读书》主编的十年里,《读书》介绍过许多新思潮、新视点,其中不乏“触碰雷区”的文章。过去二十多年中,《读书》被誉为国内最有影响的思想文化公共刊物,有一句曾经流传很广的话:可以不读书,但不可不读《读书》,就是一个佐证。过去的《读书》与其说是一个学者的大讲堂,或高举旗帜的阵地,倒不如说是知识分子聚会的沙龙、茶馆。
这一切,都和这一时期的《读书》办刊思想有关。考察从前(1996年以前)的《读书》,其办刊特色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六点:(一)“三无”办刊论沈昌文自己总结《读书》杂志的办刊思想时提出办刊“三无”论,即无能、无为、无我。此“三无”论一出,叫好声一片。王蒙对此作了很好的发挥,他说:“出版家编辑家只有进入兼收并蓄的“无”的状态,既无先入为主,无偏见,无过分的派别倾向,无过分的圈子山头(有意或无意的),无过多的自以为是与过小的鼠目寸光,无太厉害的排他性,无过热的趁机提升自己即为个人的名利积累的动机,才能兼收并蓄来好稿子,也才能真正团结住各不相同的作者……”。
王蒙的话就很好地指出了沈昌文“三无”办刊论的内涵。正是这种大“无”的思想办出了《读书》的“大有”。这种大无以无限作为参照,有极大的胸怀;同时有极大的弹性,不是刚体的不可入性;是一种无我状态,无欲则刚,有容乃大。“三无”办刊论为《读书》成为知识分子的公共俱乐部创造了这样一个前提:不管是科学还是人文、启蒙抑或后现代、自由主义与“西马”,《读书》都能够一概笑脸相迎,兼容并蓄。这也使《读书》杂志的作者、编者、读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买卖,而是知识分子内部的知识交往和心灵沟通。
沈昌文自己在多种场合下一再强调:“把一个思想评论杂志《读书》长期坚持下来,读者越来越多(从两三万到十三四万),靠的无非是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和无能。”《读书》为一代人提供思想食粮,“三无”办刊论功不可没。
(二)通往‘精英文化’的桥
《读书》从创刊以来,一直注意介绍学者、文人、作家的生平和成就,为此发表了不少文章。沈昌文在1987年第4期《读书》杂志上提出《读书》杂志要做“通往‘精英文化’的桥”:《读书》的任务只在介绍、引导、汲取,它主要工作不是在学术上进行创立和建树。如果还可另立一个名词来表达《读书》的性质,也许可以勉强称它为桥梁文化,即人们也许能通过它而到达“精英文化”之彼岸,但它本身并不是彼岸。
正是基于如此办刊理念,《读书》一直密切关注文化的命运和现状,决不一味消极地淡泊和超脱。和其他同类刊物相比较,《读书》显然要有更多对文化的“终极的关怀”,使自己更加具有深度——一种明白晓畅而非深奥费解的深度。《读书》所在做的,是尽力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继续探索、反映、认识中国的种种事情,为他们提供有用的精神资源。这使1980年代的《读书》文章,不像今日那些快餐式随笔,是为白领先生、时尚小姐解闷的。《读书》的文章都是知识分子个人思考的结晶,内中自有一种“精神贵族”的傲气,或沈昌文所自我理解的“人文关怀”。
(三)提倡“旧学新知”
《读书》杂志创刊以来,痛感过去闭关锁国的害处,因此竭力介绍国外文化界、读书界的情况,帮助读者开阔视野,扩大选择余地。为《读书》撰文介绍海外情况的作者首先来自海外学人,其次是国内的学者、教授,以自己研究国外新理论、新思潮的心得,发而为文章,启迪后进。尤其是后期留学生写作队伍的加入,对《读书》有很大的意义。沈昌文认识到:中国需要有益于现代化的新知,单靠翻译、出版、介绍还不够,必须有人去亲知亲炙,共同做好这个工作。所以重视国外的理论新知,“在于《读书》认为文化学术领域必须对外开放,只有广泛了解、汲取、分析国外的新成就,才能走出中国人自己的路子”。
在提倡海外新知的同时,沈昌文更注重学术文化工作者去做“旧学”新知的工作,“我们不摒弃传统学术,也不认为全部‘西学’即为新知,更不主张‘全盘西化’,然而旧学应当贯以新知,新知应当用于旧学,这是明显的”。基于这样的办刊理念,海外学人的学子新论逐渐成为沈昌文主持《读书》的一大特色。当时的一流海内外学者几乎都给《读书》撰写过此类文章。
(四)“不伦不类”
沈昌文在1986年第4期《读书》杂志上提到这样一件事:有位评论家喜欢给《读书》写稿,有一次偶然说起,因为他的评论文章常给评论杂志以“不合论文体例”打回来,于是想到《读书》——它不是专爱发表“不伦不类”的文章的吗?这“不伦不类”的确是《读书》办刊的一大特色。
《读书》的“不伦不类”迥异于现代的学术评价体系——它们从来只是对于那些“正襟危坐”的长篇大论感兴趣:无论是在高等院校还是在科研院所,评职称时所提交的材料大体都要求是文章要三千字以上,三千字以下者不算严格意义上的论文,不能作为评价学术能力的依据。所以,沈昌文认为现在的刊物组稿难约的稿件不是洋洋洒洒的学术论文,而是一则寥寥千字的“品书录”。倒不是作者不帮忙,实在也为难:这些文字,写起来不易,可是它们能帮助作者评学位评职称吗?《读书》的“不伦不类”能做到的只是“脑力操练”。
沈昌文说:“脑力操练”四字绝妙,可以说点明了《读书》的一贯意向……要通过《读书》观察“那一部分人”之动向,也就仅此而已。无论所动所想为何,无非只是“脑力操练”……要通过《读书》经世济民办不到,连博个“教授”职称也难!”基于这样的一个定位,《读书》并没有把自身看作学术性杂志,而是把文章的可读与否,作为自己的生命线。说到底,他是知识分子的高级休闲刊物,是可供他们“卧读”的。正是这种“卧读”,团结了千百万的知识分子,《读书》由此在他们的心目中树立了一种牢不可破的风向标。
(五)从无禁区到解放编辑
《读书》创刊以来,力倡读书无禁区,这也是谈论《读书》时不能不一再被提起的话题,用沈昌文的话说就是“每隔几年总要被提到一次”。有人批判,有人称道。这个在当时中国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的口号是在《读书》创刊号上提出来的,文章作者是李洪林,原来的标题是《读书也要破除禁区》,发表时由《读书》改为《读书无禁区》。可以说,这是代表《读书》的一个大胆的想法,《读书》的一个大胆地提议,得到的回应也是越来越高涨。
在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有一个呼声:清除“左”的危害。
《读书》一贯反对在读书问题上持禁锢的态度,希望读书界、理论界、文化界有一个开放的气氛。《读书》十周年的时候,沈昌文特地对此作了一个小小的总结:十年来,《读书》倡导了“读书无禁区”,传播了“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讨论了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是不是一个学派……同时,沈昌文还提到了舆论的宽容,“感谢对知识分子议论的这种宽容度,虽然觉得它应当还更多一些”。
“宽容”是沈昌文主持《读书》时一再强调的,也是《读书》的一大特色。沈昌文认识到,在不宽容的思想统治下,无数人类精英的人头落地,千万思想成果被束之高阁,并且坚信:在这之后产生的宽容,将不会是一种单纯的“宽大为怀”的善举,而是由于“察觉事物的实在价值”而产生的真实信念。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读书》提出“解放编辑”的口号,只有编辑生产力解放了,才更可能解放其他学术理论的生产力。“解放编辑”的前提是文化环境的宽松,只有编辑得到解放了,编辑才能实现首要的社会责任——解放知识的生产力。
(六)设立读者服务日
《读书》开办之初,老一辈的领导就十分注意向社会请教,1985年在沈昌文的倡议下开始设立读者服务日,这是从前《读书》的又一特色,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杂志的办刊思路和一个时期的畅销与《读书》提出的“没主题、没主持、没开始、没结束”四个服务日口号大有关系。
《读书》杂志读者服务日每月至少一次,地点就在咖啡馆,当时的做法是请《读书》的作者、读者随意坐下来,随便喝咖啡聊天,编辑们周旋其间,借机了解信息,讨教主意。通过这样的方式,《读书》有了源源不断的选题,根据这些选题编辑再去深入组稿。
在读者服务日刚开始设立时,杂志还请出版社提供最近相关样书,让参与的作者讨论,著作界、读书界、出版界对此高度评价并热烈响应,服务日办得有声有色。《读书》编辑吴彬在评价读者服务日的设立时认为,读者服务日为杂志的编辑出版提高了效率:“这一下非常集中,我们就那天,一个下午的时间,我们可以不停嘴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其实对我们来说的话,是一个很大的充实。”
后来,沈昌文感觉服务日活动范围太窄,只是编辑部少数人在做,于是决定在《读书》杂志开辟“《读书》服务日之页”。每期约用十来面篇幅,介绍这方面的活动,反映出版界提供的新书,介绍其中一部分内容,发表与会者的意见和要求。
《读书》杂志创刊至今,到2007年7月截止,刊物先后经历了三代主编的更替:1979——1986年,陈原;1986——1996年,沈昌文;1996——2007年,汪晖(1997年至2007年,汪晖、黄平)。三代主编的更替,可以作为《读书》二十余年的时间分野。1996年,沈昌文退休,汪晖接任主编,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汪晖主持《读书》学术化倾向似乎已经命中注定。
近年来,人们对《读书》之变谈论最多的,除了学术化倾向以外,是对它思想兼容性的质疑。
二、《读书》的“今生”
不知道是不是出于总结其办刊成就的目的,《读书》杂志最近推出了1996——2005十年间《读书》文选6卷本,由三联书店出版。这个6卷本的文选可以作为考察汪晖《读书》办刊思想的最好文本,6卷本文选基本上涵盖了十年来《读书》杂志的精华。在文选的序言里面,汪晖和黄平对编选的目的作了说明,也对现在《读书》的办刊特色进行了总结。
(一)介入“现实”
1996年以后的《读书》自觉地介入了九十年代至今的“大转变”,在若干问题上成为触发重要论争的思想论坛。从1996年年起,《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讨论,诸如大众民主与宪法问题、全球化与亚洲问题、二十世纪的战争与革命、三农问题、医疗改革与社会保障问题、新左翼与新自由主义之争等。
汪晖说“我们的方针是渐进的调整,是因为即使介入这些现实性的问题时,《读书》的主要策略还是从思想的、知识的和理论的角度出发,而不是进行直接的公众讨论或政策性辩论,它致力创造的是一个立足于反思和批评的建设性的思想氛围”。
对于《读书》的这一姿态,不少人是给予肯定的,也为汪晖他们赢得了一些掌声。但正如汪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这些“介入”现实问题时,他没有采取大众讨论的方式,而“专注”于理论和知识的“启蒙”(启发)。
(二)保持平衡
汪晖在接受《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谈到,《读书》创刊至今风格是不断发生变化的,每一个变化都跟社会变化紧密相关。比较过去十年的《读书》,现在《读书》提供的社会关怀似乎更加广泛,“我们不希望《读书》只是少数精英的杂志”。
关于《读书》的学术倾向与大众化问题,汪晖表示,《读书》的文章希望保持一种平衡。《读书》不会退回到学术里面去,也不会完全采取大众化。考虑到1996年前的《读书》和此后文化环境的不同,不能说汪晖的策略没有道理。汪晖认为,80年代初期,《读书》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刊物,跟它相对的是大量的学报,跟这些学报相比,《读书》肯定是好读的。但90年代,《读书》面对的不仅是这个系统,它面对的是更多的大众文化刊物,和大众文化刊物相比,它当然是更难读的。
(三)知识分子论坛
1996年以后的《读书》,和知识分子走得更近了,汪晖希望《读书》成为知识分子讨论问题的论坛,一个宽广的、开放的、自由的平台。对此,有人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人说1996年后的《读书》是新左派的论坛,失去了从前的兼容并包和不伦不类。不管这种声音是否偏执,从《读书》这次编选的6卷本精选文集中,可以看出《读书》杂志是在有意避免这一倾向的。
从文集选入作者看,代表左中右、老中青的作者的文章都有。如果考察《读书》杂志在一个时期内发表的大量的所谓新左派文章,汪晖的“左派倾向”似乎也不好否定。但一本杂志并不能决定中国知识界的图景,一本刊物有自己的学术倾向本也无可厚非。毕竟,一个杂志,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立场是一件好事。只不过和从前的《读书》相比较,现在的《读书》其学术性与可读性要把握的分寸可能还需要拿捏。(四)两个变化比较从前的《读书》和现在的《读书》,可以看出两个变化:第一,杂志中有关社会问题、国际问题的讨论和来自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作者明显增多了;
第二,杂志仍以中国大陆作者(包括海外留学生和海外华人学者)为主,但韩国、日本、欧洲、美国、东南亚、印度、拉丁美洲各国和台湾、香港地区的学者也成为《读书》的作者。
汪晖认为,《读书》应该成为一个跨越国界的公共空间。十年来的《读书》的确在实践着他这一办刊思想。在全球化的视野中,《读书》力图超越西方中心论,展开对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讨论,从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各个方面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6卷本《读书》精选之一即命名为《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突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创造的种种历史幻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前的《读书》和现在的《读书》的确在办刊思想上出现了一些不同,比如从前的“三无”办刊论和现在的“介入现实”、从前“通往精英的桥”和现在的“保持平衡”,从前的“不伦不类”和现在的“知识分子论坛”等等。但仔细考察前一个十年和后一个十年的《读书》杂志,至少有一点没有改变,那就是《读书》的人间关怀和思想锋芒,杂志一直保持着对人与书的关注、对文学和艺术的关注、对历史和生活的关注。
其实,不管是沈昌文还是汪晖,他们都在主政《读书》期间保持了《读书》的传统,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即便是“将来”的主政者潘振平和吴彬,以他们的能力水平和对杂志的熟悉和了解(一个是《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一个是《读书》的资深编辑),相信他们也会在对《读书》继承中有所发展。
现代社会讲究“和而不同”,我们应该允许后来者搞一下“试验”,哪怕这试验并不成功。当然,《读书》作为一份公共杂志,是学术公器,学术公器不能私用,更不能成为专制的“传声筒”,这是常识。公众所能忍受的最后界限,大概也是这个原则。再退一步讲,《读书》主编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还拥有一份不可不读的《读书》。我们应该珍视《读书》的思想空间,理解它的存在价值,而不是总拿一些吓人的说辞,对一本刊物炒来炒去。
三联书店的一位负责人通过《中华读书报》提出对“将来”的《读书》
三点原则意见:首先,《读书》是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类杂志,这一办刊宗旨和定位不能变。其次,《读书》要一以贯之地坚持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独立思考、兼容并包的办刊理念和品格,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和读者讨论研究问题的园地。第三,《读书》既要“固本”也要“求变”。有此三原则,乐观一点看,《读书》的将来或许还会再现“晖黄”时代。所以,我们对此次《读书》“换帅”不必过度焦虑。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且看将来的《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