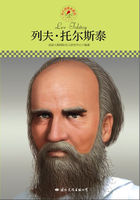1836年夏,马克思从波恩大学回到故乡特利尔度假,与童年时的女友燕妮秘密地订了婚。
燕妮出身于普鲁士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男爵,1816年作为普鲁士政府的枢密顾问官被派到特利尔,他到特利尔之后,很快就结识了亨利希·马克思,并成为好朋友。
燕妮于1814年2月21日诞生在易北省的萨尔茨维德尔,后来随父亲到了特利尔。燕妮的家在罗马大街,离马克思的家不远,两家的孩子们自幼在一起玩耍,马克思的姐姐索菲亚是燕妮中学时的同学,而燕妮的弟弟埃德加尔又是马克思的同学。燕妮的父亲威斯特华伦的藏书室是马克思常去的地方。威斯特华伦十分喜爱马克思的求学精神,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子弟,马克思也对这位老人敬如慈父。在幽静的庭院里,在摩塞河边的草地上,在马尔库斯山的丛林中,这位鬓发斑白的老人时常带着马克思、燕妮等一起散步,给他们讲述莎士比亚的戏剧故事,朗诵荷马史诗。
燕妮比马克思大4岁,她从小就聪颖好学,能写一手文笔秀丽的文章。少年时代的马克思就十分钦佩这位好学深思、没有贵族习气的姑娘。韶华流逝,友情日增。马克思决心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崇高志向、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发人深省的真知灼见,把燕妮的思想引到了一个新的境地。马克思也发现燕妮不仅长得更加美丽动人,而且变得更加聪慧、纯洁和正直了。少年时代淳朴、天真的友谊,随着年岁的增长、了解的加深,逐步发展成为纯真、炽烈的爱情。共同的理想、高尚的情操,把这一对奋发有为的青年紧紧地结合在一起。1836年暑假,这一对青年人互相倾吐了蕴藏在心中很久的相思之情。燕妮接受了马克思的求婚,秘密约定了终身。
马克思与燕妮的订婚,是对当时社会的传统观念和市侩习俗的大胆挑战。燕妮出身于贵族之家,才华出众,是特利尔城最美丽的姑娘,多少官僚贵族子弟在追求她。按当时社会的通例,燕妮这样的贵族小姐只能在上流社会阶层中联姻。马克思的父亲虽然是个律师,但终究属于市民阶层,经济虽然宽裕但并不十分富足,何况马克思还只是一个前程未卜的大学生。这桩婚事能否得到燕妮双亲的赞同,亲戚朋友将怎样议论,对他们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燕妮的父亲虽然也喜欢马克思,但总希望女儿在上流社会里找到一个门当户对的姻亲。燕妮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斐迪南,更是竭力反对。斐迪南是个十足的名利之徒,当时在政府里任枢密官,后来在普鲁士政府里任内政大臣。在他看来,像燕妮这样出身名门贵族的小姐,怎么能嫁给一个普普通通律师的儿子呢?何况马克思当时既没有固定的职业,也没有优厚的收入和高贵的社会地位。所以,当他得知燕妮和马克思的婚事后,简直暴跳如雷,竭力反对,横加阻挠,但是燕妮是个性格坚强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理想的爱情,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
当时,燕妮在家里的处境是很困难的,家里人甚至宣布不再养育她,由她自己去决定今后的命运。燕妮常常因此弄得心神不安,最后终于病倒。但是燕妮即使在疗养地养病,也始终怀着对马克思的挚爱深情。
后来,马克思向自己的父亲吐露了心头的秘密,这位性情宽厚的老人,虽然开始有些疑虑,认为两家门第相差很大,但他看到燕妮是那样全心全意地依恋着自己的儿子,最后还是表示同意。并且在马克思上学过程中,这位父亲不断地写信告诫马克思:“目前你必须自己拿出行动来,你必须做到使人深信,尽管你年轻,但你是始终如一,有远大抱负而值得依赖的人。”
1836年10月中旬,马克思在父亲的督促下,从特利尔启程到了柏林大学,他心里既高兴又担忧,高兴的是他和燕妮的爱情终于开诚布公地互相倾诉,担忧的是燕妮的父母能不能同意他们的亲事。
那时候,马克思正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写了许多诗篇,他把火一般的感情倾泻在诗行间。爱情的热流在他的血管里奔腾,任何力量也压抑不住他对燕妮的思慕和眷恋,他渴望着未婚妻的来信。但是燕妮事先已经向他表明,在他们的婚约没有得到双亲同意以前,她不能跟他通信。由于得不到燕妮的来信,马克思常常夜不能寐,就用诗句寄托对远方恋人的热烈爱情和无限思念:
燕妮,即使天地翻覆迷茫,
你比天空晴朗,比太阳明亮,
即使天下人把我淋漓诅咒,
只要你属于我,我都能忍受。
思念比天上宫殿还高,
比永恒的天地更长久,
比理想国更美妙,
忧心似海,深胜海洋。
思念无穷无尽永无止境,
像上帝亲自塑造的一样,
你留给我的形象,
我永远无限向往。
你就是思念的化身,
思念两字犹未能表达深情,
可以说这是一团火,
永远不断燃烧我激荡的心。
由于这种“不停地沸腾”的爱情生活持续了几个月,致使马克思一时无法收住他那抒发爱情的笔迹。接着马克思又向燕妮写了一些倾诉相思之情的诗歌。特别是在《人的自豪》这首诗歌里,马克思怀着对燕妮的纯真爱情,表现出了勇于横扫爱情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的信心和决心。来自家庭和社会上的阻力,使马克思的情绪激愤,他在诗中写道:
燕妮,如果我可以大胆地直言:
我们的心已为同一火苗点燃,
两颗炽热的心已在一起搏跳,
激流已把我们俩汇合在一道。
面对着整个奸诈的世界,
我会毫不留情地把战挑,
让世界这庞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扑灭不了这火苗。
那时我就会像上帝一样,
在这宇宙的废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话都是行动,
我是尘世生活的造物主。
马克思和燕妮之间的真挚感情,使这位刚开始品尝人间生活味道的堂堂男子,表现出了一种可贵的忠贞品格。马克思暗自下定了始终不渝的决心:“只要我还没有离开人间,就对你——燕妮的思念永不消逝。”因此这个时候,在马克思的面前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热情澎湃的爱的世界,以至他对热闹的柏林市区和那风景如画的柏林郊区也无动于衷;而马克思举目所见的高山岩石,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也“并不比我的感情更倔强、更骄傲,广大的城市并不比我的血液更有生气,旅馆的饮食并不比我所抱的一连串幻想更丰富、更经得消化,最后,艺术也不如燕妮那样美”。
由于马克思对燕妮的爱情是如此的真诚和强烈,使他这一阶段在诗歌创作方面进入了高潮。他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总共写了三本诗集,一本叫《歌之书》,另外两本叫《爱之书》。马克思在扉页上写着:“献给亲爱的、永远爱着的燕妮·冯·威斯特华伦。”
当马克思把这三本抒发爱情的诗歌集寄到他的未婚妻手里的时候,燕妮捧着她的未婚夫用真挚的爱写出的这些深情的诗歌,几乎是一口气就把它们读完了,并且精心把诗集珍藏起来,不让任何人看到。燕妮这时和马克思一样,完全沉浸在热烈的爱情之中,并且下决心要为自己心爱的未婚夫的幸福和未来献出自己的一切,默默发誓要排除来自各方面的阻力,成为马克思的终身伴侣。
由于燕妮在当时不能公开和马克思通信,无法直接向未婚夫表达自己的热烈的感情,只好把它深深地埋在心底。直到1841年9月30日,燕妮才有机会把自己对马克思的忠贞爱情表露出来。她一往情深地写道:
今天我无法向你诉说我满腹的心事。我的整个身心、理想和信念,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一切,都已溶合为一个音符、一个声音和一个调。假如她能发出声音,那就只能听到:我对你的爱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是无止境的,永恒的和无法衡量的,其余的一切全被它吞没了……你的爱情的终结,同时也是我的生命的尽头。这个终结一旦来临,我就不会复活了,因为只有在这个爱情里才有我继续生存的信心,……再见吧,天使!我是多么爱你——我的整个心灵、生命和思想都系于此。
从这里可以看出,燕妮对马克思的感情,是何等的真挚而又深厚啊!
不过,这两位年轻的恋人,并没有完全陷入情网之中。首先是马克思,他很快就自觉地反省了曾经在自己身上存在过的那种不正常的情绪,自觉地克制对燕妮的强烈思念之情,采取冷静的态度,正确处理恋爱问题,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自己所追求的事业中去。
在马克思离开故乡以后,燕妮的心情一直不安。一方面她深切怀念着马克思,不知他在柏林的生活、学习安排得怎么样;另一方面,又担心家里人要阻止自己的婚事,顾虑别人会说自己的闲话。1836年12月28日,马克思的父亲给儿子写了一封长信,把燕妮不安的心情告诉了马克思,并且指点儿子说,要完全消除燕妮不安心情的唯一办法,就是要用自己学业上的迅速而辉煌的成就来证明自己是配得上这样一个未婚妻的。父亲特别嘱咐说:“我重说一遍,你已经承担了一项重大的义务,纵使这也许会伤你的自尊心,亲爱的卡尔,我还是要有点令人厌烦地按照自己的方式把我的意见告诉你:你用诗人所特有的那种在爱情上的夸张和狂热的感情,是不能使你所献身的那个人得到平静的,相反,你倒有破坏她平静的危险。只有用模范的品行、用能够使你赢得人们好感和同情的大丈夫式的坚定的努力,才能使情况好转,才能使她得到安慰,才能提高她在别人和自己心目中的地位。”
马克思接受了父亲的忠告。后来也感到不能终日沉湎于爱情的遐想之中,意识到作为燕妮的未婚夫所应尽的义务,应该从爱情中吸取力量来加强自己的学习,确立自己的事业。马克思在写给燕妮的爱情诗中,充分地表达了他的这一心愿:
我要勇敢地占有——
一切最美好的神赐;
我要大胆地去钻研——
科学、音乐和艺术。
我们共同地勇往直前,
永不休息,永不偷闲。
切莫呆呆地沉默不语,
无所希求,无所事事!
马克思明确了自己的志向,意识到了自己的义务,认识到必须建立起一个新的世界观,于是就以巨大的热情开始学习起来,并且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和非凡的工作能力。
在第一个学期里,马克思到当时办得最好的柏林大学法律系听了两位著名的教授——弗里德里希·萨维尼讲的优帝法典课和爱德华·甘斯讲授的刑法课,不仅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而且特别是通过甘斯教授的引导,他还自学了著名的黑格尔哲学,并且力求把书本学习和科学研究结合起来,投身到新时代的斗争中去。
马克思在刻苦学习法学、文学特别是广泛地自学了黑格尔的大量哲学著作的基础上,拟定了写作法哲学方面的一部巨著的计划,打算以此来确立合乎内心愿望的思想体系。尽管这一设想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但马克思仍然没有气馁,继续以顽强的毅力在学习上奋斗不已。因为在这之前,马克思在写给燕妮的爱情诗中,已经向自己的未婚妻表示要大胆地钻研科学,建立自己的法哲学体系,并且以此和燕妮共勉,做到“永不休息、永不偷闲”。言行一致的马克思说到做到,在这一阶段的学习中除了继续钻研法学和哲学外,还自学了文学、历史、舞蹈、音乐以及英语和意大利语,加强自己在各方面的修养。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清醒自己的思想,他常常做深入的自我剖析,一边写一边思索,他的非凡的工作能力使他能够一下子做好几件事。他能够同时阅读和分析许多著作、作摘记,把脑子里随时出现的思想和计划记下来。
马克思在柏林大学的第一个学期里,熬过了许多不眠之夜,经历了许多斗争,体验了许多内心的和外部的刺激,身心健康受到了损害,他太劳累了。
尽管如此,这位年轻人还是无法达到忘掉一切的程度。在余暇时间里,甚至是在走路和吃饭的时候,燕妮的形象总是要在马克思的脑际浮现出来,使他处于对往事的回忆中,感到非常幸福。此时,马克思多么想回到燕妮的身边,同她一起谈谈自己的学习和生活,畅谈在柏林大学一年多的感受和收获。为此,马克思请求父亲允许他回家。马克思在信中写道:“我希望,甚至必须立即回到你们那里,如果不是我担心你会不同意,不赞成的话,我已经回去了。”
马克思的顾虑果然如此,父亲在回信中不仅表示不同意他回家,而且还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责备。父亲指责马克思那种漫无边际的涉猎各门学科、在昏暗的灯光下杜撰自己的思想体系的做法,还抱怨儿子花费过大的账单,并且怀疑马克思可能在极其混乱的精神状态中“把燕妮的情书和父亲含泪写成的手谕,漫不经心地都当成卷烟纸使用了”。并说:“这些放肆行为,即使对一个学者来说也是不能原谅的,更不用说对一个实践中的‘法学家’了。”
父亲的这封回信,就像一桶冷水,一下子浇到了马克思那发热的头上,使他那颗思念燕妮的火热之心渐渐地冷静了下来,并且打消了回家的念头。马克思在这时为了能做到如燕妮给他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无所顾忌地去履行自己的神圣义务,决心进一步全面加强自己的学习,坚持不懈地向知识的海洋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勇敢顽强地向旧世界的思想堡垒冲击。
当马克思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留在家乡的未婚妻——燕妮,心情始终抑郁不安。她一方面深深思念着她的心上人——卡尔;另一方面又要为这种爱情忍受着来自家庭和社会上的冷嘲热讽。特别是当她们的恋爱还没有公开的时候,一些与燕妮同龄的女友们都已经订婚或结婚,燕妮却拒绝不少向她求婚的阔少爷。燕妮的这一行动,引起那些好事多嘴的女眷们的私下嚼舌议论,同时,燕妮还要承受着来自家庭的日益加强的敌视情绪。这使燕妮感到非常痛苦。
当马克思的父亲了解到燕妮坚定不移的态度后,就写信告诉马克思:“即使有一个王子也不能把她从你手中夺走。她全心全意地依恋着你,你永远不应忘记,以她的才华,她为你所做的牺牲,绝不是寻常女子所能办得到的。”当马克思知道了燕妮的这种处境时,非常着急,再也按捺不住了。为了尽快地结束这种无法忍受的局面,马克思鼓足勇气在1837年3月27日写信给燕妮的父母,正式向他们提出了和燕妮订婚的要求。事情果然不出所料,燕妮的父母接到马克思的信后,立即发生了一场争论,大多数人都反对这门亲事,特别是燕妮的异母长兄菲迪南·冯·威斯特华伦更是百般阻拦,只是燕妮的父亲,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这位开明的男爵、可敬的老人最后表示了肯定性的意见,马克思的请求才算是被接受下来了。随后,男女双方的家庭经过磋商,决定等到1837年底,再正式向外界宣布卡尔和燕妮已经订婚一事。
双方家庭同意马克思和燕妮订婚后,并没有完全消除他们在爱情上所遭受的折磨,因为外界并不知道。特别是燕妮,由于过分地害羞和忧虑,已使她的健康受到了很大的损害。而马克思呢,由于对燕妮病情的担心,再加上他在法学、哲学、历史、艺术、文学等方面的极其紧张的学习,以及使他不得不把写过的那部关于法哲学著作的草稿全部抛掉的严格自我批判精神,都极大地刺激了他的神经。结果,马克思病倒了,不得不到柏林的郊区农村去休养。关于这些情况马克思写信告诉了父母,而这两位心疼孩子的老人,又把马克思的这些情况告诉了燕妮,并且请求她去信安慰马克思。
当然,燕妮更是心疼马克思,只是迫于家庭和社会上的习惯势力,才不敢公开地给她那心爱的卡尔写信。可是到了这个时候,燕妮顾不得这些了,她大胆地冲破旧思想的束缚,拿起那饱醮深情的笔,第一次直接给马克思写去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来抒发思念马克思的心情。在这之前,马克思和燕妮之间的书信,都是通过马克思的父亲、姐姐,还有燕妮的弟弟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秘密传递的。她写道:
亲爱的卡尔,如果你现在能和我在一起,如果我能偎依在你胸前,和你一起眺望那令人开怀的亲切的谷地、美丽的牧场、森林密布的山岭,那该多好啊!可是,啊,你是那么遥远,那么远不可及。我的目光徒然把你寻觅,我的双手徒然向你张开,我以最柔情蜜意的话语徒然把你呼唤。我只得在你的爱情的无声的信物上印上热烈的吻,把它们代替你紧贴在心房,用我的泪水浇灌他们。
马克思接到这封信后,真是欢喜若狂。虽然他没有立即给燕妮写回信,但他在给父亲的家信中,表达了自己对燕妮的深厚感情:“请向我的亲爱的好燕妮致意!她的来信我已经看了十二遍,每一遍我都发现引人入胜的新东西,这是一封在一切方面包括文体在内我所能想象的出自一位妇女之手的最好的信。”
1837年底,双方家庭正式宣布卡尔与燕妮订婚,从此以后,他们的心事解决了。马克思的思想情绪稳定了下来,逐渐地走出了浪漫主义的旋涡,面对现实进行学习和科学研究。在马克思和燕妮正式宣布订婚一年多以后,1838年5月10日,马克思的父亲与世长辞了,他的逝世,使马克思和燕妮的婚事又面临着一场考验。这样一来,就中断了和威斯特华伦家的密切联系,使燕妮失去了那迫切需要的友好支持。因为,在燕妮思想苦闷的时候,马克思的父亲曾多次找她谈话,给她以安慰和温暖。父亲的逝世,也使马克思与家庭的联系日渐疏远了。一方面马克思开始按照自己的志向去行动,摆脱父母所期望的那种舒适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勇敢地投入到社会政治斗争中去,并且成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著名领袖;另一方面,马克思的母亲责备马克思无益地耗费了许多钱,距离家庭的要求越来越远。同时,又给儿子写信埋怨燕妮,说她四五个星期才来一次,就是来一次也不说一句话安慰的话。而燕妮也为这件事深感痛苦。尤其是因为她家的某些人仍然不能原谅她和马克思订婚这件事,那些女眷甚至乘机挑拨离间,极力在她面前谈什么将由“高不可攀的上流社会”,“而堕入底层的前景”,劝她和马克思解除婚约,再找一位有钱有势的配偶,这一切使燕妮产生了新的精神负担。为了帮助未婚妻解决思想负担,使她尽快摆脱家庭的压力,马克思打算在大学毕业后尽快谋求一个职业,使他能够有条件和燕妮结婚,去过那种独立的小家庭生活。
马克思取得博士学位以后,为了寻找一个合适的工作岗位,四处奔波。期间家里又连续发生了几件不愉快的事情,使马克思不得不回到特利尔。一个是弟弟海尔曼死后,为了父亲的遗产发生了无休止的争吵,使得马克思不得不与这个家庭彻底决裂;另一个是燕妮的父亲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男爵的病势日见严重,1842年3月3日去世了。燕妮父亲的去世,对马克思和燕妮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燕妮成了她家人不断挑剔的对象,她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为了安慰燕妮,马克思一直陪伴着她。1842年7月9日马克思在写给卢格的信中提到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从他说到这些事情时所用的词,可以看出他绝对坚强,决不愿意为任何不愉快的事情而对任何人,首先是对他自己,表示同情,因为这些事同人类的苦难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他写道:
从4月以来直到今天,我总计起来大约最多只工作了4个星期,而且还是断断续续的。由于最近的丧事,我不得不在特利尔待了6个星期,而余下的时间都被不愉快的家庭纠纷分散和浪费了。我的家庭给我设置了重重障碍,使我目前陷入极其窘迫的境地,尽管我的家庭情况不坏。我绝不是用谈论这些私人生活中的琐事来麻烦您,社会的肮脏使一个坚强的人不可能为私事而烦恼,这是真正的幸事。
后来,马克思从特利尔来到了科隆,在《莱茵报》编辑部担任了主编的职务。半年以后,由于普鲁士反动政府的迫害,使《莱茵报》无法再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的方向,迫使马克思不得不考虑出国从事著述活动。为此,马克思很快就辞去了《莱茵报》编辑部的职务,准备离开德国。但是,他不能同燕妮分手而离开德国,因为这时他与燕妮订婚已经7年多了。马克思决定同燕妮结婚。他在给卢格的信中说:“我订婚已经7年多,我的未婚妻为了我而进行了极其激烈的、几乎损害了她的健康的斗争,一方面是反抗她的虔诚主义的贵族亲属,这些人把‘天上的君王’和‘柏林的君主’同样看成是崇拜的对象,一方面是反抗我自己的家族,那里盘踞着几个牧师和我的其他敌人。”
马克思把先完婚再出国的打算写信告诉了未婚妻,燕妮清醒地看到,今后他们共同生活的道路,在经济上是毫无保障的,在政治上是布满险恶的,但是,她相信马克思的事业是正确的。她写信给马克思说:“这颗心担忧地到处追随着你,不论你到帕斯里蒂尔,或是到金色的默滕,不论你去找卢格老人,或是去找潘泽,我到处陪伴着你,时而在前,时而在后地追随着你!唉,可是,我们眼下还未能抓住命运的轮子。”“我们的命运就是等待、期望、忍耐和受难。”他们面前的道路是充满着障碍的,他们要共同清除路上的一切障碍。
马克思和燕妮向往着幸福的爱情,向往着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漫长的7年,他们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写下了多少满含泪水的信件和诗篇。他们的爱情的历程艰辛而又豪迈,在共同的革命理想中找到了归宿,他们培育的爱情之花伴随着革命理想盛开了。
那是1843年,在克罗茨纳赫。那时燕妮正和她的母亲住在这里。
6月的骄阳,在克罗茨纳赫的尼柯克教堂的上空闪烁着光辉。在浮士德博士房子的前面站着一对盛装的男女。男子满头整齐的乌发,淡青色的胡须闪闪发亮,手挽着一个娴雅、美丽的姑娘。他们在几个小时以前刚刚举行过婚礼。教堂登记簿上写着:1843年6月13日举行婚礼。卡尔·马克思先生,哲学博士,住在科隆;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小姐,无职业,住在克罗茨纳赫。
马克思和燕妮克服一切阻力最终结成了夫妻。坎坷曲折的7年恋爱之路,如果没有崇高的理想,如果没有远大的生活目标,他们的结合是根本不可能的。
他们坚毅地手携着手去迎接生活,他们度过了幸福的蜜月。之后没过多久就到了法国,开始了政治流亡的生活。从此,不论在幸福的时刻或是在困苦的日子里,爱情和友谊始终联系着他们,他们从未有过动摇和疑虑,他们相互真诚相爱直到最后一刻,甚至死亡也未能使他们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