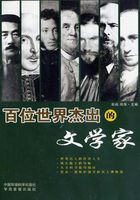1841年3月底,恩格斯结束了不来梅自由城的商行实习生的生活,回到巴门。岁月流逝,故乡却依然如故,这里的一切并不使他感到亲切,反而感到比过去更加单调和沉闷。他除了偶尔与弟弟们练习击剑、访问同学之外,整天埋头读书。
为了调剂枯燥的生活,还为了忘却一次失恋的悲伤,恩格斯于同年5月到瑞士和意大利旅游,漫游了伦巴底。一路上,他漫步于山林溪谷之间,饱赏了大自然的秀丽风光。途经瑞士的苏黎世城,他浏览了市容,登上了禹特利贝克峰,眺望了苏黎世的湖光山色,情不自禁道:“大自然,你是多么的美丽!”他向大自然默默地倾诉内心失恋的隐痛,大自然的瑰丽景色驱散了他心头的惆怅,心胸为之开阔,使他重新振作起精神来。他来到苏黎世湖中心的乌福瑙岛,凭吊了骑士胡登的陵墓,听到湖水的波浪拍打英雄的陵墓时,犹如听到远处传来的兵戈相击声和战斗的呐喊声。后来他在游记《伦巴底之行》中,写下了自己的感慨:“英雄墓地的四周,绿色的湖浪哗哗作响,犹如遥远战场上的呐喊,而担任守卫的就是那冰封雪裹,青春常在的巨人——阿尔卑斯山。英雄们当初如此为自由思想而斗争,现在又如此地在战斗的辛劳之后安息——得到这种荣誉的人是幸福的!”
恩格斯登上巍峨的阿尔卑斯山峰,一派雄伟壮观的景色展现在眼前:群山起伏,林海苍茫;天高云淡,云雾缭绕;瀑布轰鸣,飞泻直下,在阳光的照射下放出耀眼的光芒。翻过阿尔卑斯山麓,积雪融化,泉水淙淙,到处是绿草红花,青枝嫩叶。他漫游了伦巴底城,寻访了古罗马的遗迹,踏遍了孕育过“文艺复兴”巨人的古老而美丽的乡土。在美丽的文化古城米兰,他在斯加拉广场的达·芬奇的雕像下流连往返。
从伦巴底旅游回来。恩格斯在巴门度过整个夏天。由于恩格斯和父亲的政治观点不同,与父亲的关系更紧张了。在他面前摆着两条路,或者是屈从父亲的安排,当一个工厂主,或者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献身于争取自由与进步的事业,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1841年9月初,征兵工作就要开始了,根据法律规定,恩格斯要服一年兵役。尽管他不喜欢充塞着黩武主义气氛的军旅生活,而且像他这样有钱人家的子弟,花一笔钱就可以免服兵役,但是,这样做与他的性格是格格不入的,他决定应征去当兵。当时服役地点可以自由选择,他选中了柏林,那里是普鲁士的首都和政治文化中心。
1841年9月下旬,21岁的恩格斯动身前往普鲁士首府柏林服兵役。在服兵役期间,使他感到安慰的是,他在兵营里学到了一些实际的军事知识,这对他后来在1848年德国革命中军事才能的发挥,并成为无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奠基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除了参加军事训练外,每月还要去教堂一次,听牧师讲道。当士兵来到教堂的时候,首先要戴上沉重的带羽毛的高筒军帽,进入教堂的院子后,要在院里站上整整一个钟头,然后进入阴森森的教堂。恩格斯对这种无聊的活动很厌恶,他只去过一次,以后遇到这种活动,他都设法溜掉。
恩格斯在柏林的这一年中,主要活动场所并不在兵营,而是在柏林大学的校园里。按照规定,作为一个服役一年的志愿兵,在训练期后,可以找一个私人住所。于是,他在服役的第六周,就在离兵营不远的窦绿苔街56号租了一个房间,这个房间在二楼,房间正面墙上有三个窗户,房间里很明亮,可以透过窗户看到晴朗而蔚蓝的天空,当然,从房间里还可以看得见部队的营房和训练场。在这里,恩格斯把业余时间和晚间的时间利用起来,努力钻研德国哲学,写了批判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的著作。
柏林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城市,恩格斯利用空隙时间,认真地了解和认识柏林众多的名胜古迹和文化设施,了解它的历史变迁。柏林又是普鲁士的首都,集中着各种政治派别、政治观点的代表人物,思想政治领域的斗争尖锐复杂,这为恩格斯仔细观察和参加争夺德国舆论统治权和政治统治权的斗争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柏林的思想文化中心是柏林大学,恩格斯当时对柏林大学的评价很高,那里有很多的教堂,有机智的和迂腐的教授、活泼的和严肃的大学生等等多层次的人。他认为柏林大学生的荣誉在于:任何大学都没有像它那样屹立在当时的思想运动之中,并且像它那样使自己成为思想斗争的舞台。因为德国的其他大学都回避思想斗争,并陷入专搞学术的冷漠态度,这种冷漠态度长久以来正是德国学术界的不幸。相反,在柏林大学教师中却有各种派别的代表人物,从而造成活跃的辩论气氛,这种辩论使学生能够容易地、明确地对当代的各种倾向进行比较。
柏林大学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到讲堂听讲,许多人从四面八方前来旁听自己感兴趣的课程,一些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学者聚集在这里。
恩格斯自学哲学,早就想了解各个派别的政治和学术观点,对当代的各种倾向进行比较,所以,21岁的志愿兵恩格斯以旁听生身份走进柏林大学的讲堂,听一些著名教授讲授哲学。
那时,正值著名哲学家、柏林大学教授谢林讲授《哲学启示》。谢林是德国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的早期的政治观点是反封建主义的,但后来日趋反动,随着封建势力复辟得逞之后,他却愈来愈和基督教正统思想接近,并在哲学上为这种正统思想辩护,因而基督教正统思想的代表人物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谢林身上,他们希望通过谢林在哲学领域内给青年黑格尔派以打击,使无神论者哑口无言。为了这个目的,普鲁士国王于1841年邀请谢林来到柏林大学,让他主持哲学讲座。
1841年11月15日,柏林大学第六讲堂里挤得水泄不通,熙熙攘攘,人声嘈杂。人们都想听一听这位大哲学家的讲座。恩格斯身穿蓝色军装,也和其他人一样等待着主讲人的出场。
一阵铃响,讲堂里立即安静下来,一个60多岁的老头出现在讲台上。此人中等身材、身躯肥胖,一对浅蓝色的眼睛里露出傲慢、狡黠的神情。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哲学教授谢林。
谢林以哲学“权威”的架势,首先讲了一通半个世纪以来德国哲学的发展史。他以轻蔑的口吻谈到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甘斯和施特劳斯,骂他们是“魔鬼的奴仆”。接着,他又大言不惭地把黑格尔的许多精辟见解宣称是自己发现的,然后转入正题,他煞有介事地宣讲他的伟大发现——世上万物以上帝为本源,最终以上帝为归宿,“启示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证明上帝的存在,科学和理性要服从于宗教的信条……
恩格斯听着听着,脸上感到火辣辣的,心在剧烈地跳动。恩格斯对谢林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竟极力贬低黑格尔哲学的重要意义,十分愤慨。他竭力克制住自己的愤怒,迅速地把谢林讲的内容记了下来,并把自己的笔记和其他人的笔记作了校对,就匆匆赶回了自己的住处。
恩格斯还听了黑格尔的学生马尔海纳凯教授反对谢林的讲演。马尔海纳凯态度冷静而又略带讽刺地指出:“不错,现在谁也不会自认为如此才疏不浅,以致不能反驳黑格尔及其哲学……可是所期望的这种反驳还没有,而且,只要不是平心静气地对黑格尔进行科学探讨,而是采取激怒、仇视、忌妒,总而言之采取狂热的态度,只要有人认为有了某种幻想就可以把黑格尔从他的哲学思想宝座上推下来,所期望的这种反驳就不会有。这种反驳的首要条件当然是正确地理解对手,看来,黑格尔的在这里的某些论敌好像在同巨人搏斗的侏儒。”恩格斯对马尔海纳凯的讲演报以热烈的欢呼,并且十分赞赏这位身材结实、相貌严肃的教授的讲课艺术。恩格斯写道,马尔海纳凯讲课时,“举止落落大方,没有那种埋头念讲稿的学究气,也没有戏剧性的、故作姿态的手势;他的态度像年轻人那样豪爽,目光专注地望着观众;他讲得很平静,庄重、慢条斯理而又流畅通达,平铺直叙又极富有深刻的思想,这些思想一个接着一个涌出来,后一个比前一个更能准确地击中目标。马尔海纳凯在讲台上以其充满信心,坚定不移,尊严庄重,同时也以自己的整个气质所焕发的自由思想而令人肃然起敬”。
夜深人静,窦绿苔街56号二楼的房间里,还亮着烛光。窗外寒风呼啸,一片漆黑。恩格斯怎么也无法入睡。他在默默地思索:威廉四世把谢林召到柏林,让他在柏林大学的讲坛上放肆地攻击黑格尔及其学生,显然,谢林的矛头并不是对着黑格尔一个人,而是对着青年黑格尔派,也对着德国的进步力量,他的“启示哲学”就是为普鲁士封建专制统治效劳的御用哲学。谢林对黑格尔的攻击,不是一场纯粹的学术之争,而是争夺德国舆论的统治权的斗争,归根到底是一场争夺德国统治权的斗争。对谢林这样肆无忌惮地歪曲历史,把污秽的脏水泼在黑格尔及其弟子们身上的卑劣行径,难道能保持沉默吗?不,既然对方挑起了这场论战,就应该迎上前去,接受挑战。
但是,站在自己前面的对手是一位颇有名声的大人物。谢林是黑格尔青年时代的好友,杜宾根神学院的同学,黑格尔死后,他成了德国资格最老的哲学权威。况且,在谢林的背后,给他撑腰的是以普鲁士国王为代表的整个反动势力。而自己呢,20岁刚出头,中学也未学完,更没上过大学,只是靠自学才懂得一些哲学知识。同这样一个大人物论战,意味着什么,恩格斯是十分清楚的。
但是,恩格斯坚信,尽管谢林来势猛,后台硬,真理并不在他手里。他的那一套说教,不过是用哲学的语句伪装起来的神学呓语。理性必将战胜迷信,真理终将驳倒谬误。早在不来梅时,他就认为谁也不能垄断科学研究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科学讨论,只要他具备这方面必要的知识。想到这里,他勇气倍增,奋然提笔,像一个初上战场的炮手,向自命不凡的谢林开火了。
谢林要求我们把这个世纪40年的劳动和创造性活动,把40年的思想——为了这种思想曾经牺牲了最大的利益和最神圣的传统——当做白费的时间和全盘的错误而一笔勾销。而这样做不过是为了让谢林显得在这40年当中并不是一个多余的人,——但是,这未免做得太过分了。……谢林把他从黑格尔那里看到的一切正确的东西统统宣布为自己的东西,甚至说成是和他自己血肉相关的。这岂不是一种思想上的贪污行为吗?
恩格斯继续奋笔疾书:
我们的任务是遵循伟大导师的思想的道路,保卫他的陵墓不受凌辱。我们不怕斗争。……凡是正确的东西,都经得起火的考验;一切谬误的东西,我们则甘愿和它一刀两断。……
恩格斯深深懂得保卫大师陵墓的重大意义。普鲁士是一个基督教君主专制的国家,基督教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思想支柱。德国革命派人士,以黑格尔哲学为武器,从批判基督教出发,矛头指向封建专制制度。青年黑格尔派的许多著作,如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施特劳斯的《耶稣传》、布·鲍威尔的《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审判的号声》等,对宗教进行了批判。基督教的全部原则以及凡是被称为宗教的东西,都在理性的无情批判下崩溃了,以基督教为思想支柱的普鲁士专制制度动摇了。预感到了人民风暴即将来临的普鲁士王朝,在加强对人民的暴力压制的同时,把制止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救世主谢林身上,确信他是铲除黑格尔哲学、战胜青年黑格尔派的最适合人物,幻想通过他的“救世的力量”、“革除不信神的咒语”维护根基动摇的反动统治。谢林“启示哲学”的反动本质就在于此。为了维护真理,恩格斯夜以继日在不到半个月时间,一篇《谢林论黑格尔》的文章出现在1841年12月出版的《德意志电讯报》上,作者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紧接着恩格斯又写了两个小册子:《谢林——基督教的哲学家》、《谢林和启示——对绞杀自由的最新反动派的批判》,分别在柏林和莱比锡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在这些小册子里,恩格斯彻底揭穿了这位“哲学权威”的反动面目。他尖锐地指出,谢林的“启示哲学”是为普鲁士王国服务的,它是一根思想的锁链,使人们屈从封建专制统治。于是,柏林的反动报刊蜂拥而上,对文章和小册子的作者(由于文章是用笔名发表的,小册子是用匿名发表的,所以社会上并不知道它们的真正作者是恩格斯)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们惊呼,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最新的雅各宾派的明目张胆的目标”,是想在德国煽起一场革命。谢林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刚一登上讲坛就会遭到如此沉重的打击,他更想不到自己的对手竟是一个连中学也没有上完的年轻炮手,而且就坐在他的讲坛下面。
恩格斯和柏林进步思想界的批判使谢林声名狼藉,原形毕露,他只得草草收场,提前结束他的讲座。1842年3月18日晚上,也就是谢林结束讲课的当天,柏林大学的进步学生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学生们要求谢林滚出柏林。谢林无可奈何地辞去了柏林大学的教职,灰溜溜地离开了柏林。
恩格斯的作品得到了国内外进步思想界的重视和欢迎。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德意志年鉴》的主编卢格开始也不知道“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是谁,以为一定是个“哲学博士”。他在评论《谢林和启示》时说,作者的风格和观点充分地表现了青年人的锐气,作品语气声动,富于战斗力,对谢林的批判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明确的立场。1842年11月,波兰的进步刊物《科学瞭望》刊载了这本小册子的部分译文,把小册子的作者称为“当代杰出的哲学家”。1843年1月,俄国彼得堡出版的《祖国纪事》杂志也刊登了译文片断。
恩格斯在1842年3月至9月在《莱茵报》上共发表了12篇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坚决主张改革现存社会制度,维护言论、出版自由,反对保守思想。他强烈地反对统治者践踏人民主权,禁止出版自由,干涉司法独立等做法,他历史地分析了官僚集权同专制国家的联系,说明了集权和自由的关系。
恩格斯除了在《莱茵报》上发表政论方面的文章外,还在《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和《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张》等期刊和文集上发表文章。
这样,恩格斯赢得了柏林的青年黑格尔团体——“自由派”小组成员的信任,他们邀请恩格斯参加他们的活动。常常聚在邮局大街的老邮局酒店,在那里讨论哲学上的各种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恩格斯在这里第一次听到不少关于马克思的情况介绍。
在国内外一片赞扬声中,恩格斯着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表现得十分谦虚。1842年6月,他在给卢格的信中说:“我绝不是博士,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博士;我只是一个商人和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炮兵;因此,请您不要对我用这样的头衔。”7月,他还表示:“我决定在一段时间里完全放弃写作活动,而更多地进行学习,原因十分明显,我还年轻,又是个哲学的自学者。为了使自己有一个信念,我所学的已经够了;但是要在必要时捍卫它,并且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却是不够的。人们将会对我提出更多的要求。……现在我认为我自己的义务是,通过研究(我要以更大的兴趣继续进行研究)去越来越多地掌握那些不是先赋予一个人的东西。”
此后,恩格斯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去柏林大学听黑格尔子弟们讲授神学和哲学专业课和文学课,晚上在自己的房间里系统地研究黑格尔的著作。黑格尔哲学体系包罗万象,逻辑学、形而上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等等,同时这一切都融合成一个体系——唯心辩证法。恩格斯透彻地研究了这一切,同时还研究了费尔巴哈的著作《论基督教的本质》。
恩格斯在柏林的一年时间里,深入地研究了德国古典哲学,从黑格尔那里获得了内容丰富的辩证法,从费尔巴哈那里获得了唯物主义,他靠自学获得了渊博的知识,为以后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引导和推进无产阶级革命掌握了锐利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