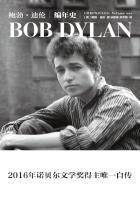罗特的父亲是位建筑师,家住在格马克区最北边的一个僻静地方。恩格斯来找罗特,他俩现在是好朋友了。恩格斯认为罗特是个诚实善良的人,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朋友。恩格斯在罗特家门前拉响了门铃,不一会儿,罗特的脑袋从楼上的窗口伸了出来,接着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了院门口。“你终于出来了。”罗特说道。
恩格斯并没有想领罗特参观恩格斯家水车房的意思,但在罗特的一再请求下,他还是答应了。当两个朋友走完水车房的小路,踏上返回格马克的归途时,天色已近黄昏。罗特沉默了一会,开始用一种惋惜的语调说道:“你们的水车房真棒。从这里一直到里特尔豪森的所有水车房,我几乎全都去过。尽管如此,恩格斯——要是我说出来,你不要生我的气——水车房应该拆掉,或者应当停止使用,这是我从我父亲那儿知道的,他早就忙着制订你们家的水车房的改造计划了。”
恩格斯站住了,他真想狠狠地回敬他几句。可是,话到了嘴边,又收了回去。为什么要争议这个问题呢?干吗要把罗特带到水车房呢?他们俩在市政厅桥边分手了。恩格斯往回走,边走边想,难道水车房都该拆掉,真是无法想象,得去问问父亲。
父亲听了他的提问,吃惊地看着他。“你小小的年纪就对这些事情感兴趣,这很好。可是,这不是一句话就能讲清楚的。明天午饭后,你到厂里来找我。”
第二天放学后,恩格斯非常自豪地穿过厂区,他这是第一次来到父亲的办公楼。父亲把他带到窗前,指了指那边的水车房,说:“它忠实地为我们服务了很多年,可是现在,它开始使我们走上破产的道路。尽管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但却是肯定无疑的。”他不再继续说下去,让迪霍尔特先生给他一本厚厚的账簿。父亲把它放在桌子上。“这是一本总账本,”他郑重地说,“是每个商人、每个厂主、每个企业家真正的良心。”
恩格斯惊愕地看着这本账本,它又厚又大,但是已经很破旧了,总之,给人一种相当可怜的印象。“这本账簿记载了公司里的一切业务情况,从大宗交易到最不显眼的细枝末节的事情。但是,它们并不是以你在这里所见到的活生生的、看得见的形式出现的,而是存在于钱——这个共同的分母之上的,它反映了成本、收入、利润和亏损。”
父亲打开账本,尽是些密麻麻的数字,蓝的、红的和绿的数字,排成一行行一列列。虽然写得很好看,但恩格斯什么也看不懂。
“这些数字无情地指挥着我们,去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如果我们违背它们的命令,我们就会吃苦头,公司就会倒霉!”父亲接着说,“水车房给我们提供的动力太贵了,经常性的维修耗费太大。在乌培河水太少的干旱季节,水车停止运行,我们不得不依靠河谷上游上百个水车房——这就是我们必须寻找一种新的、可靠的动力的原因。”
“要造一个新的水车房吗?”恩格斯问。
父亲摇摇头:“水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那么,应当用什么东西来带动机器呢?”
父亲斩钉截铁地答道:“用蒸汽作动力。”恩格斯说:“是用蒸汽机吧。”
父亲点点头,他合上账簿,又从保险柜里慢慢拿出一份卷宗:“你可以看看,我早就把希望寄托在蒸汽机上了。这是一本有数平方英里土地的登记册。有朝一日,如果要造巴门火车站的话,埃尔伯弗尔德公路边的黏土坑,那是个最好的地好。我几乎没花什么钱,就从维希林豪森的地产管理处那里把这块地方买下来了。这是契约。”
“黏土坑?”恩格斯吃惊地问。
“是的,10年或20年,我的儿子,如果要测量埃尔伯弗尔德—巴门铁路线,我们就得为此花一小笔钱。”这位商人又十分得意地说:“敢于超越时空的限制,把眼光放远一点,并能对未来的发展做到心中有数,是有利可图的。”
恩格斯感到十分高兴,这倒不是由于父亲的那套经商之道,而是他想到将来巴门会有一条通往杜塞尔多夫的铁路。
一个月后,恩格斯家里来了一位英国工程师。他住在三楼的一间房间里,每天默默地和他们一家共进午餐。他只是按父亲的要求行事。厂区在建设,恩格斯很快就发现,围墙的背后有一座巨大的烟囱拔地而起。
父亲吃午饭时,同那个英国人开玩笑。但是,两人的神色慢慢变得严肃起来,话也更多了。
一天晚上,父亲怒气冲冲地回到家。他让母亲看了一张公文,气愤地说:“这些官僚主义者,鼠目寸光,没见过世面的不学无术之辈!好一个行政长官先生,让他见鬼去吧!看来他终于等到了向敌方营垒进攻的机会。”
恩格斯听到行政长官这个词时,浑身为之一震,父亲用目光扫了他一下。
“怎么办?”母亲问。
父亲茫然地耸耸肩:“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说完就回书房了。
恩格斯跟着母亲走进了厨房,他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糟糕的事情。妈妈起初摇了摇头,接着又注视着他:“他们向行政公署长官递了一份请愿书,要求禁止安装蒸汽机。”
“谁?”恩格斯问。
“很多人,”母亲说,“行政区长官已经下令,禁止蒸汽机投产。”
恩格斯这时感到父亲的工作也不容易,他有些自怨不能帮助父亲,还给父亲添了麻烦。傍晚,他胆怯地敲了敲门,轻轻地走进父亲的书房。父亲坐在写字台边,像在考虑什么,头也没有抬。
“父亲,是我。我只想说,我支持你的意见,我们必胜。”他想给父亲讲几句特别鼓舞人心的话,以便给父亲消消气。“这些该死的官僚主义者和不学无术的家伙,别理他们?”他继续说道。
父亲拉着他的手,向他点点头:“去睡觉吧,孩子!”可是他脸上还是没有笑容。
第二天,建筑工人离开了工厂,父亲乘车去了杜塞尔多夫好几趟,每次回来都一言不发。
不久,全班同学都知道了这件事,有些人竟朝他发出幸灾乐祸般恶意的讥笑。特别是卡佩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不怀好意地问道:“你们家的那座漂亮的烟囱什么时候拆?”这次攻击来得突然,恩格斯自尊的心又一次受到伤害。休息时,忠实的朋友们打算安慰他:“别再搞什么蒸汽机了。”“要蒸汽机干什么用?”
“蒸汽机会安装好的!一定会的。”恩格斯冲着他的忠实伙伴们喊,“总有一天会从烟囱里冒出烟来,冉冉上升到高高的蓝天!”
就在这一个星期里,他两次和别人打架,并被当场抓住。
“只剩下去柏林这最后一条路了。”父亲对母亲说。停了一会,父亲怀着一种极其烦恼的心情,说出了下面一段使恩格斯十分震惊的话:“讨饭,简直像乞丐挨门挨户讨饭一样,虽然你只想得到迫切需要的东西,除此之外并不需要别的。可是,你必须在板着面孔的官老爷面前阿谀奉承,卑躬屈膝。进衙门简直像入地狱!”
“去看看我父亲。”母亲建议,“他和行政长官封·马森先生是至交,他现在在财政部主管海关,也许会给你写一封引荐信。”
恩格斯听完,轻轻地溜进了自己的房间,两只小手紧紧地攥成拳头。这时,他想起了万能的、至高无上的主,他真心诚意地祈求上帝,助父亲一臂之力。
两天后,父亲从柏林回来,显得疲惫不堪。但是,从他的言谈中可以听出来,事情有了希望,工程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重新开始。他热情地赞扬政府顾问马森先生,说他如何破例接见了自己,并且怀着极大的兴趣,仔细地听取了自己的申述。
8月1日是星期天,又是暑假,恩格斯觉得这寂静的清晨多么让人眷恋呀。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了他的遐思。莫里茨姑夫来找父亲。
莫里茨姑夫用颤抖的声音说:“革命,内兄,巴黎发生流血的巷战,波旁王朝被推翻了。”
“我的上帝,莫里茨,快进来。”
门打开,接着又关上了。
恩格斯感觉到心在咚咚地敲打着胸壁。革命,他反复琢磨着这个词的含义,这是一个听了使人感到震颤和带有神秘色彩的字眼。男人们在说这个词时都压低了声音,妇女的眼睛里则露出惊恐的神色。这个词来自法国,这他知道。断头台上的铡刀哗啦啦落了下来,国王的脑袋滚落尘埃,他知道的就这些。有一次,他想从亨里埃特小姐那里打听更详细的情况,“小孩子家不要为这些事去伤脑筋!”他被挡了回来。
中午祷告时,恩格斯从家里溜了出来,他到水车房,得问问罗斯坦德老爹。
“你上了市立学校,将来会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人。难道你真的不知道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吗?”
“不知道,罗斯坦德老爹。”恩格斯小声地说。他觉得问革命这个词的含义,说明自己的知识相当贫乏。
“当人民愤怒地起来反对折磨他们的人的时候……”
“人民?”
“我、你、你的父亲、工厂里的人、手工业者、妇女、整个城市以及乡村里的农民,乃至整个国家。”
“反对国王?”
“还反对政府、教士中的败类和诸如此类的一切东西。”
“跟我来!”罗斯坦德老爹从一个旧箱子里,费劲地找出一本厚书。他打开一页,上面有一张画,“这儿,你瞧!巴黎大革命,那时候我才15岁。”
恩格斯看见画上画着一条长长的狭窄的街道,看见许多戴着尖顶帽,拿着老式步枪、斧子、锤子的男人,手里拿着石头的小伙子以及赤手空拳的妇女。他们朝着排列成行的国王的步兵们开枪射击时组成的火墙挺进,许多人中弹倒地,血从伤口中汩汩地流出来,流得满地,他们一动不动地躺着。一张令人胆战心惊的画,它使恩格斯感到异常激动和愤怒。他永远忘不了这幅画!
1830年,埃尔伯费尔德—巴门商会,德国第二个最早的商会正式建立了。父亲的名字被列入经普鲁士国王恩准的第一任商会创始人的名单。有一天,恩格斯被允许同母亲一起到厂子里去,参观已经安装完毕的机器,但是结果却使他感到非常失望。在他的想象当中,机器房应当是既高大又华丽,而实际上却只是一间既破旧又可怜的小工棚。至于机器本身,那就更不显眼了,它的锅炉要比洗澡房里的圈桶小得多,铁的传动轮并不比车轮大。难道这些不起眼的小玩意儿能取代恩格斯水车房的巨大动力吗?
“我想看看它是怎样工作的!”恩格斯直截了当地表示自己的怀疑。
“今天还不行,”父亲回答,“锅炉里会产生巨大的蒸汽压力,谁也难以事先确切知道,这种材料是否能经住这种压力。政府只是在有限制的条件下才批准安装这台机器的。”
母亲有点害怕,紧紧地搂着自己的儿子,很快带着他离开了工厂,好像这只尚未点火的锅炉要爆炸似的。当锅炉升火,烟囱里冒出第一股浓烟时,她不安地靠着窗子,谛听着外面的声音,任何一点响声都使她吓得发抖。直到父亲深夜归来,母亲才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
从现在起,大烟囱里天天冒出滚滚的浓烟,周围地区的厂主们都赶来参观这件吸引人的新鲜玩意儿。在学校里,恩格斯兴致勃勃地向同学们讲述蒸汽机的模样、巨大的工作动力,尽管他知道的还十分粗浅。
就要过恩格斯10岁的生日了,他一定会得到许多人的祝福和礼物的,但是恩格斯只想再到工厂里看看蒸汽机,可自从布吕宁工厂发生事故以后,恩格斯工厂也严密防守,不许人员随便进入厂里。这时恩格斯想起了小时候玩耍时在马厩角落里发现的一个活门,直通墙外的工厂。
他走进马厩,闪到一辆破旧马车的后面,使劲推开那扇积满灰尘的活门。于是,他发现这里离带烟囱的新工棚最多有50米远,一眼就可看见蒸汽机,蒸汽机在那个工棚里嗒嗒嗒地响着。马厩的山墙紧挨着原来的发货处,这里可以轻易地爬上发货处的屋顶。突然,恩格斯惊呆了。通过门上向上翻开着的气窗,他看见了屋子里的情形。往日的回忆又历历在目地浮现在他的眼前。在像山一样高的棉花堆旁,坐着一排孩子,不仅有大孩子,而且还有年纪很小的儿童。听不见他们的欢声笑语,只见他们弓着背,默默地手脚不停地工作着。
恩格斯真想跳到屋顶上,打开天窗,让光线射进去,让孩子们出来又唱又跳。可是他做不到。他忘了蒸汽机,忘了刚才的兴致,从原路回来,在雨水中跑着。
过了几天,一个孩子在蒸汽机旁死了。恩格斯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现在是祷告的时刻,巴门教区教堂的钟声开始敲响了,它召唤人们去教堂做礼拜。恩格斯站在教堂中央,孩子的棺材停放在走廊里。布道台上响起了莫里茨姑夫颤抖的声音:“我们在世界上无论遭遇到什么事情,无论对我们进行什么样的残酷考验,我们都必须逆来顺受,因为所有这一切,我的兄弟姐妹们,都是上帝的意志!”
恩格斯对周围发生的一切再也不想听,再也不想看,萦绕在他脑际的只有:上帝的意志,上帝的意志,……
两个小时后,当恩格斯家族的成员都聚集在他家客厅时,他跳了起来。“不!这不可能是上帝的意志!”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父亲、卡斯帕尔叔叔和奥古斯特叔叔。“是谁让孩子们到工厂干活的?是谁?”大家都瞠目结舌地看着他。母亲赶紧过来,把抽泣着的全身发抖的他拉出客厅。
在他的房间里,母亲反复地劝了他很长时间。
“这事你父亲和叔叔们都感到非常非常痛苦。他们并不想让孩子们到厂里干活,我知道这一点。在你祖父还在世的时候,他们就进行过种种尝试。可是,开支一年比一年大!名目繁多的税收,各种各样的关税、过境税,无一不在增加。接着,又是来自英国的竞争!他们必须生产出更便宜的东西,这样才能把工厂维持下去。懂吗?我们没有别的办法!”
“太可怕了!”恩格斯喃喃地说,“像玛丽和安娜那样的女孩,像赫尔曼和埃米尔那样的男孩,硬让他们坐在长桌边干活,不准笑,不准唱,甚至连话都不许讲。”
“这的确可怕。”妈妈痛苦地承认,“可是,如果工厂关了门,这些孩子就得挨饿。”
“那么,在工厂里又怎么样呢?”
“你要知道,这是一场灾祸!那个可怜的孩子是未经允许擅自溜进机器房里去的。”
恩格斯沉默了。母亲接着说:“是的,在工厂里也有坏人。他们让孩子们干活,每天干14到16个钟头,累得他们筋疲力尽。有一些人拿烧酒来抵工资。可你父亲和叔叔,他们是好心人,他们给工人们足够的休息时间,用现款付给他们应得的工钱。你祖父在工厂里办了一所学校,孩子们每天可以在那学习三个小时。你可以到附近找任何一个人打听打听,这样你就会知道,能够在恩格斯兄弟工厂里干活是感到幸运的。”
“这我相信你,母亲,不是父亲的过错,可为什么没有人起来反对这种罪恶?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你可不能这么说,恩格斯。”
“是的,我知道说真话是很危险的。”
“我们只能信奉上帝,我们只能向他敞开自己的心扉。”
“我知道人们为什么必须保持沉默。可是请你,至少请你别把上帝牵扯进来!上帝是不愿这么干的,上帝永远不会同意掩盖事实,迫使人们去弄虚作假,撒谎骗人的。如果这是上帝的主意,那我一定仇视他,是的,仇恨他!”
“安静点,别再说了!”母亲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摇晃了几下。这时,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乌尔丽克说道:“那个死去的孩子可是再也救不活了,死者自有自己的安身之处,我们得为活着的人着想。”
欺骗,全是欺骗!恩格斯的内心竭尽全力地呐喊着,他仿佛明白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