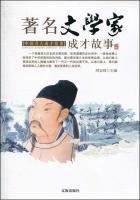海底墓葬那感人的一幕,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更激发了我对尼摩船长的兴趣,他到底是什么人?我不敢再苟同老实人康塞尔的说法,他把船长分在被埋没的学者那一类,认为他是个傲视世人的科学家,后来他又将其归入不为人所知的天才那一类,因为厌倦人类的欺诈和世态的炎凉才躲到这个只有他能自由行动而别人却无法到达的海底世界来。但在我看来,尼摩船长却绝非为了逃避人类。制造如此强大的机械设备不仅是为了提供行动自由所需,恐怕后面还有大的行动。
表面看来,尼摩船长并没太多干涉我们的自由。这是因为他对我们的逃跑很有把握。所以,实际上我们还是俘虏、囚犯。所以,可以理解尼德·兰持久的逃跑念头。但船长慷慨地让我分享了诺第留斯号的秘密,我如果一走了之,而又带走了这些秘密,会问心无愧吗?另外,说实话,我想把这次奇妙的海底世界游历进行到底,我想看看地球上的海洋所包含的所有新奇东西,我想看看其他人没有看过的东西。虽然我有可能要以生命为代价来满足这种好奇心!
我们正驰骋在印度洋中,这个广阔的海洋面积达到1亿5000万公亩,海水清澈见底。诺第留斯号一般在100至200米的深度航行,就这样行驶了好几天。每个人都觉得这样的时间太长,太单调无聊。但除了我以外,因为我爱大海。每天,我在平台上散步,呼吸海上清爽的空气,舒展筋骨,有时透过客厅的玻璃板观察海里的无限风光,在图书室里看书,写笔记。这些占据了我很多时间,使我没有一刻感到无聊和厌倦。
一天,当诺第留斯号在北纬9度4分露出水面时,我看到西边海里有一块陆地,峰峦高耸,连绵起伏——那是锡兰岛。(即当今的斯里兰卡)美丽、富饶的锡兰半岛以盛产珍珠而着称于世。我返回客厅,打开地图,仔细研究岛的位置和面积。
尼摩船长这时开门走了进来。
“教授先生,你有兴趣去参观一下采珠场吗?”他问。
“那当然好,船长,”但现在还没到采珠的季节,可能看不到采珠人,不过去采珠场看看肯定也很过瘾。
“教授,”船长又说,“在雷加拉湾,在印度洋,在中国海和日本海,在美洲南部的巴拿马湾和加利福尼亚湾都有采珠的,但采珠最棒的地方却是锡兰岛。渔民每年只是在三月才来到观纳尔湾,一连干三十天。采珠人一般分为两组,两组轮流下水,他们身系一条系在船上的长绳,双脚夹着一块大石头,潜入十二米深的水下采珠。”
“啊!我叫道,他们还在用这种最原始的方法?但你的潜水衣肯定会对他们大有好处。”
“那当然,因为这些人不能长久地呆在水底。据我看来,采珠人在水下最多只能停留30秒,他们需要在20秒内把采得的珍珠贝塞进一个网兜。他们的寿命一般都很短,视力会过早衰退,眼睛会溃烂,他们全身都会发炎,有时还会在水下中风而死。”
“不错,”我说,“这是一种悲惨的谋生方式,因为它只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兴趣。但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一条船一天能采到多少珍珠贝?”
“好的话可达到四五万左右。”
“那么,”我说,“这采珠能保证他们有不低的收入吧?”
“不,他们的雇主却发财。教授,他们通常卖一个珍珠贝才得一分钱,还有好多没有珍珠的贝,那么一周只能挣得1美元。”
“好了,教授,”船长说,“明天邀上你的同伴们,我们去马纳尔湾参观采珠场,如果有幸遇到早来的采珠人,我们就能看到他们采珠了。”
“那好,就这么定了,船长。”
“顺便问一下,教授,你怕鲛鱼吗?”
“鲛鱼!”我惊叫道,“老实说,船长,像这种鱼我从未见过面!”
“别害怕,我们有枪。”
他说完后,从容镇静地溜达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四点钟就被尼摩船长安排的管事叫醒了,我穿衣起床,直奔客厅。
尼摩船长已恭候多时了。
“教授,”他问,“做好准备了吗?”
“做好了。”
“那来吧。”
我随着他走向楼梯,爬上平台,尼德·兰和康塞尔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们很高兴去“海底散步”。放在诺第留斯号旁边的小艇中,五个水手持桨等候在上面。
夜色还没褪尽,空中有朵朵白云,星光闪烁其中,但已不很明亮了。我望着陆地,但只能看到一条模糊不定的地平线。在夜间,诺第留斯号沿锡兰岛西海岸直接上溯到马纳尔岛的海湾两侧。
我们登上小艇。
小艇向南驶去,水手们用力划着桨,珍珠真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似地噼啪落在幽黑的海面上。
晨曦微现,但五英里外的岸边仍然被雾气笼罩着,看不见一只小船,到处一片沉寂。
六点时,阳光猛地照在我们身上。赤道地区没有真正的黎明或黄昏,日夜的交替是很快的,阳光穿透地平线上厚厚的云彩,霞光万道。
“我们到了,教授,“尼摩船长说,“现在我们穿上潜水衣,开始水下旅行。”
我们穿好潜水衣,被几个水手一个个送下水。他们则留在艇上,落下15米,双脚踏上了平坦的沙滩。船长打了个手势,领我们顺着斜坡向水底走去。
来到安静的水底,我一直被鲛鱼侵占的脑际也变得平和多了,动作的灵便更使我信心大增,随后就被美丽的海底世界吸引了。
到七点时,我们终于到达了生长着上百万只珍珠贝的水域。这些珍贵的软体动物贴在岩石上,被自己棕色的丝足缠在石上,不能移动。有着人类破坏天性的尼德·兰很快就往他的怀中塞最好的珍珠贝。
船长打手势要我们跟他走,只有听他的,因为只有他认识路。
这时,一个巨大的石洞出现在我们面前,洞口的岩石上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海底动物。起先洞里很黑,但我的眼睛很快就适应了,我能分辨出几个天然石柱,立在花岗石基上,支撑着一个形状古怪的拱顶。
为什么奇怪的向导将我们引到这么深的地窖里来呢?
下了一段陡坡之后,我们站在一个圆坑的底部。尼摩船长站住了,指着一个我从未见过的东西。
那是一个体积大得惊人的珍珠贝,巨大得简直就是一个大圣水盘,一个两米多宽的大钵。
很显然,尼摩船长早知道这家伙在这儿。他不只是为了向我们展示奇观,而是自己来看看这儿现在的情况。
这个大贝壳半开着,尼摩船长将匕首伸在两壳间不让它们合拢,然后用手掀起贝壳上的膜边。
在两扇树叶状的膜皮里,看见一颗椰子那么大的能自由转动的珍珠,圆圆的、清澈透明、光泽完美,这是一颗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船长想让这颗珍珠在那只贝壳里任其生长,这珠子就会一点点长大。每年,这动物的分泌都会让珍珠长厚一层。只有尼摩船长才知道这个美妙的大自然果实什么时候“成熟”,也只有他认得这个地方。
走出石洞,我们像逛花园似地随意漫步,停停走走,自己想自己的事。过了十分钟,尼摩船长又站住了,但显然我们躲在大岩石后面,然后他指着水中一点,我仔细看着。
5米远的地方,有一黑影缓缓沉到水底。立刻我想起了船长告诉我的——鲛鱼!
但不是,那只是一个印度人,一个采珠人,他早早就赶来采珠了。他的小船就在他头顶几英尺的水面上。他潜到水中,然后再往上游,一颗圆圆的石头吊在他的脚上,石头由一根绳子系着绑在小船上,这样有助于他很快下沉到海底,到水下约5米处,他曲膝跪下,将手边的珍珠贝顺手塞入袋中,然后他又游上去,倒空袋子,将石头提上去,又这样下来一次,大约30秒钟打一个来回。
突然,当这个印度人再次落下时,我发现他做出一个惊恐的姿式,并快速站起来,奋力向上游。一个巨大的阴影出现在他上方,我明白了他的惊恐,那是一只眼睛放着光,嘴巴张得大大的鲨鱼!正向他猛扑过来!
这个贪婪的家伙,把鳍用力一拨,扑向印度人,他向旁边一躲,把鲨鱼的嘴躲开了,但鲨鱼的尾巴击中了他的胸部,将他打昏了。
然而,没过几秒钟,鲨鱼又卷土重来,想要拿这个印度人开荤。这时,船长突然从我身边跳将出去,手中握着匕首,冲向鲨鱼。
鲨鱼正要去咬采珠人,突然发现了新的敌人,立刻转过头来,向船长凶猛地冲过来。
尼摩船长曲膝蹲身,蓄势待发,当鲨鱼冲过来时,他机敏地向旁边躲了过去,同时用匕首一下刺入鲨鱼身上。
鲨鱼更加狂怒,伤口上血流如注,染红了海水,水中一片浑浊,我什么也看不清了。
等海水略显清晰时,我发现船长正伏在鲨鱼身上,一只手抓住它的鳍,另一只手在鲨鱼身上乱刺,但由于每次都没能致命,鲨鱼仍在疯狂地挣扎。
我看得目瞪口呆。船长被猛地甩出,落在水下,鲨鱼很快向他扑去,张开血盆大口,露出锋利的牙齿。情势万分危急,突然我身旁又冲出一人,那是尼德·兰,他手握鱼叉一下击中了鲨鱼,海水更红了,并在鲨鱼的猛烈挣扎下激荡澎湃起来。尼德·兰不愧是鱼叉王,一叉刺中了鲨鱼的心脏,鲨鱼在做最后的挣扎时,又带翻了康塞尔。
尼德·兰扶起尼摩船长,幸好他没受伤,船长走到采珠人身旁,急忙一刀割断他身上的绳索,然后抱起他双腿一蹬,向海面浮去。
我们三个人也紧随其后,劫后余生的人们聚集在采珠人的船上。
尼摩船长首先要把这个可怜的采珠人救活。他在水中呆的时间并不太长,但鲨鱼尾巴的这一击可能对他是一个严重伤害。
康塞尔与船长给采珠人按摩,终于使他慢慢苏醒了过来。他睁大双眼,惊恐地看着面前的四个大铜脑袋。
尼摩船长取出一颗大珍珠,放在可怜的采珠人的手中,他双手颤抖着捧起它,以为遇到了海神。
离开采珠人,我们回到自己的小艇上,卸下沉重的头盔后,尼摩船长首先对尼德·兰说:
“谢谢你,尼德·兰师傅。”
“不必了,船长,”尼德·兰答道,“一报还一报吧。”
船长的嘴间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八点半左右,我们返回了诺第留斯号。
回到自己的房间,我细细地回味着这次马纳尔之行的不平凡遭遇,心中充满了对船长的敬佩。看到他能勇敢地为素不相识的人类做出牺牲,我感觉他并没有完全失去人的仁爱之心。
我把我的感觉说给他听时,他略带些激动的口气说:
“教授,这个印度人生活在被压迫的陆地上,我属于那块陆地,而且会永远属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