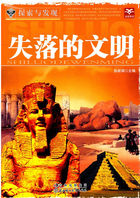经过长期的组织和策划,宾夕法尼亚州的盲人协会会长在1921年美国盲人企业家协会在俄亥俄州举办的年度总结会上提出了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盲人机构的建议,这项决议很快就正式通过了。
纽约的M·C·麦格尔先生是该协会的首任会长。起初,麦格尔先生的经营策略是寻求朋友的资助,从1924年开始,政策有所调整,他决定设立基金,号召分众积极募捐,同时邀请我和莎莉文老师参加。
对于那种为了筹募经费而奔波劳顿的生活我实在有些害怕了。从他们的计划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煞费苦心,但是真正说来,我不太情愿,然而,我心里非常清楚,在当时,慈善机构和教育团体只有凭借公众的慷慨捐助才能正常运转。为了盲人的福利,尽管有些勉强,我还是硬着头皮应承了下来,竭尽用去做。从此,我又和以前一样,开始进出于形形色色的高楼大厦坐着电梯去各个地方演讲了。
这笔基金的建立给盲人们带来许多好处——他们将借助这笔钱学习和掌握一门技术,这样就能自食其力,独立生存了,而且基金会还将为他们提供一展才华的场所;还有一部分盲人天生聪颖,在某些方面有突出的才能,但是往往因为没有好的环境被埋没了,这笔基金将为他们提供所需让他们的才能得以发挥出来——臂如为那些有音乐天赋的盲人购买钢琴和小提琴等乐器,毕竟这些对那些家境贫寒的盲人来说是一笔可观的开支。
从那以后的三年时间里,我的足迹遍至全的每个角落,我访问过的城市大约有123个,参加的集会有249场,对20多万听众发表过演讲。此外,我动员了形形色色的组织和社团,其中有报社、教会、院校、犹太教会堂、妇女协会、青少年团体、服务社团和狮子会等他们经常集会进行募捐,来支持我们的工作,每次都获得了慷慨捐赠,狮子会尤其热情大方,他们不遗余力地支持残疾獐的福利事业,对盲人也付出爱心和同情,在那段时,募捐工作几乎成了会员们的主要工作了。
俗话常说:“年过四十,所有的事业大半都已经历过了,再不会有什么值得喜悦的事了。”
但是,命运总垂青于我,40岁生日过后不久,我又接连经历了几件欣喜若狂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美国盲人事业家协会的创立;第二件是,我们的募捐运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第三件事是,美国盲人事业家协会成立后,将原来百家争鸣的盲文统一了。另外,国立盲人图书馆终于落成了,政府拨出了一大笔经费,大力支持盲文出版事业。紧接着,各州的红十字会也成立了附属盲文机构,专门负责翻译盲文书籍。还有一件激动人民的事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幸失明的士兵们联合起来,为盲人争取福利和保障,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浪潮。这是我多年来的夙愿,现在终于得以一一实现了,我能不感到快慰呢?
1926年的冬天,我们赶赴华盛顿,继续我们的募捐活动,这时国会正好通过了拨款筹建国立盲人图书馆和促进盲人书籍出版事业的提案,听到这个喜讯,我们喜出望外,顿觉未来一片曙光。
一天下午,我和莎莉文老师前往白宫拜会柯立芝总统,他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向他汇报了盲人协会的有关情况和现状,总统一直耐心地倾听我们的报告。最后他兴高采烈地拉起我的手放在他的嘴唇上,告诉我:“你们的工作是伟大而崇高的,我向你们致敬,只要我能力所及,我一定全力协助你们的工作。”
总统言出必行,后来还被推选为盲人协会的名誉总裁。他为我们的基金会作了很大的贡献,还为基金会捐了很多钱。柯立芝夫人对我们的工作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最后竟然参加到我们的行列中来,有许多福利都是她为聋哑人争取的。
盲人议员汤玛斯·希尔先生和赖辛浦夫妇也热心于我的工作,给予我们极大的支持和方便。让我分外感动的是贝尔博士的女儿,也就是现在的艾露滋夫人,也为我们向大众呼吁,热诚地帮助我们做宣传。
在底特律担任残障者保护联盟会的会长卡米尔先生是我的老朋友,知道我们的来意后,他把这件事当做自己的义务,热烈呼吁本地民众,还帮助我们筹划了一次演讲,虽然我们只在该地集会一次但却募集了42万美元。后来又陆陆续续收到许多捐款,从1美元到4500美元不等。我们的义举在这个城市回到颇为可观。
我们在费城逗留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并募集了22万美元。这个结果还要感谢募捐委员会的委员莱克博士有效的劝募和当地民众善良与积极响应。
我们的活动在圣路易、芝加哥、水牛城等地没有掀起高潮,当地的反应比较冷淡,那里的公众似乎也比较冷淡,但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事,罗彻斯特这个小地方却为我们基金增加了15万美元。
众所周知,演艺圈的明星们要比一般人的收入丰厚,生活也富裕得多,如果向他们抻出求援之手,我估计结果不会让我失望,但是没有想到我失算了。我将无数的信件寄往洛杉矶,可是却没有收到什么回昱,直到很晚才接到一封回信,是一位女明星玛丽·白克福寄来年,相形之外,我格外珍惜,她和丈夫道格拉斯·费蒙先生对我们的工作的支持,对他们的好意我格外感激。
在这次旅行途中,我们还走访了圣罗拉的农业试验场。在那里,我们拜访了农艺家鲁沙·巴本克先生,他是那儿的负责人,以前有许多品许的水果。花草和树木都不适应这里的生长环境,可是他接管后,就出现了奇迹,那些无法生长的植物竟然都栽植成功了,而且长势旺盛。巴本克先生不但是个出色的农艺师,而且为人慷慨,还给我们捐赠了一笔钱。他热情地引领我们参观他的试验场,示意我抚摸他精心培植的仙人掌,我担心有刺,他告诉我,这种仙人掌与一般家庭裁植的仙人掌不同,它是经过改良后的新品种,没有刺。我感觉到了那平滑的表面,有一种水灵的丰满,我甚至联想到,它是一种可口的蔬菜。
最近两年,我基本停止了募捐工作,只待在家里写书,可是我们前期的工作和既定目标还差和大截,还有150万美元的空缺,所以我在整理完手头的稿件后,还得再次旅行,筹募基金。
我们以前的奔走呼告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最让我感到欣慰的。在这两年内我没有开展任何宣传和捐款,但我们的活动深入人心,汇款在源源不断地流入我的帐户。比如,在富翁洛克菲勒、勃麦克尔先生等人在去年就捐赠了数目相当可观的一笔钱,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捐款人的姓名和捐款额了,因为实在是多得难以计数。然而不管他们贡献多少,我们对他们的感激都是等量的,所有盲人都会因为他们的善良和同情而备受喜舞,而且这种美德也将世代传承。
募款本来就依赖于无数的好心人的点点滴滴的积累,如果没有这些善良人的帮助,我们就不能按计划为收人谋取福利,协会的工作也会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汤姆斯小姐每次拆信时,迫不及待滑落的经常是那些支票,其中包含了来自各个领域和各个地方的支持,有来自欧洲和亚洲各地的学生、军人、工人等,有的本身就是残疾人,然而,令我们感动的却是他们的善良。
有一天清晨,邮差送来了一封来自底特律的信,她的捐款金额是1美元,没有留下她的真实姓名,只以“一位贫苦的女工”署名。
孩子们也积极响应我们的号召,这使我心中激荡着感动的热流。有的孩子兴高采烈地把他们的存储罐抱到我们面前,爽快地的破,倒出来,全部捐献出来;有的孩子在信中用稚嫩的笔调倾诉他们的真诚和热心,把平日里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零花钱和买可乐、买糖果、买冰淇淋的钱都作为捐款寄给我们。
记得那一次在纽约的安迪集会时,一位残疾少年当场捐献了500美元,还送给我们协会一大束生机盎然的玫瑰花,如今,这位少年已离开人世;那束玫瑰花也早已凋落,但是,他善心的芳华和深情厚意却永远驻留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