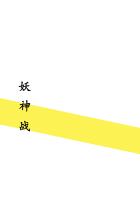母亲是儿子人生中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儿子人生中的第一面镜子。
满月过后,李永书抱着他的二儿子,来到村中的家庙太慰庵里,请庵里的石点师公为孩子赐名。老人二话没说,挥毫在孩子的庚贴上写下“李德海”三个大字。德,是他的辈份,老人的意思是,愿孩子将来德比大海,即使不成大器,也要做一个施德于人的人。
李永书抱着小德海,欢欢喜喜地回家去了。从此,在这个白马乡,就有了一个叫德海的孩子。德海与他的哥哥德业,相去四岁。
二十年代末,正是中国社会最动荡不安的时期。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盘踞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但由于它的不彻底性及妥协性,又为日后的社会埋下了战乱的隐机,这隐机日酝月酿,终于引发了一场内乱,二十年代中国南北大地上的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便是中国的广大农村。
江浙一带的战乱,给苏北大地带来的是更加贫穷,更加动荡不安。那时候,常常有一批批逃避战乱的人们如惊弓之鸟忽东忽西地逃来逃去。
不时有战败的军队骚扰乡里,丘八们每一次的出现,白马乡人则多一次飞来横祸。
兵荒、马乱、蝗灾、干旱,如一道道绳索捆缚在农民李永书的身上,李家的日子越来越难熬。由于缺乏奶水,小德海显得十分瘦弱,常常咬着母亲干瘪的奶头,发出喑哑的哭声。这哭声象尖刀一样刺扎在母亲的心头,于是,哥哥德业混在一帮小兄弟中间,从稻田、水沟里捉来一条条泥鳅为母亲催奶。而奇怪的是,每当母亲沾了荤腥,小德海情愿饿着肚子,也决不沾母亲的奶头。
首先有这发现的当然是母亲,母亲想,儿子真是和尚命吗?从此以后,母亲便长斋念佛,更加至诚地念着观音菩萨圣号,并且想,若是这孩子命中不该饿死,我何必要为他去杀生催奶?
倚着母亲那一点点奶水,小德海一天天长大,虽然仍是那么瘦弱,但一双清丽的眸子里却闪动着一种明澈的神韵,笑起来又是那么天真、逗人。邻居们常常逗着哥哥小德业,说要将他的小弟弟抱走送人,小哥哥不识大人们的逗趣,只要人家说要去抱他的弟弟,他就要挥着小拳头跟人家拼命。
那时候,不管日子过得多苦多累,只要一看到两个儿子,李永书的心头就立即会漫过一丝身为人父的甜意,就觉得再苦再累也算不了什么。
在白马乡一带,一般人家都有供佛的习惯,而李永书家供奉的是一尊黄杨木雕的观音菩萨。这尊观音菩萨更是德海母亲心中的圣物。
那是在小德海不满周岁的时候,一群战败的伤兵半夜窜到白马乡。这群丘八逢财物就抢,逢女人就奸淫。
当骚乱的浪潮席卷到前港村时,全村的人在慌乱中拖儿携女,寻找逃避的地方。李永书架起儿子德业,母亲则抱着弟弟德海,将家中仅存的一点钱物草草卷好,逃到屋后的一间草棚里。当然,母亲在慌乱中仍不忘将那尊黄杨木观音菩萨藏到身上。
德业已经懂事了,他睁着一对惊恐的眼睛紧贴在父母的身边。而不满周岁的德海却禁不住这深夜的惊恐,不停地哭叫着。
母亲将干瘪的奶头塞在孩子的嘴里,并且不住地颂念着“大慈大悲观音菩萨!”当那群伤兵打到李家屋门口时,母亲怀中的德海却象懂事般地一声不吭了。
母亲仍只是默念着菩萨圣号,这时,已经听到那群伤兵穿过后院,寻到柴棚的声音。
一个伤兵泼口大骂:“人都死到哪去了?”
另一个伤兵说:“管他人在哪,老子先点火烧了这棚子再说。”
小德业差一点吓哭出声来,父亲连忙将他搂在怀里,捂住他的嘴。一家人担心的并不是这个已经五岁的德业,而是母亲怀中不满周岁的德海。母亲将德海紧紧地搂在怀里,只是一个劲默念着菩萨圣号,小柴棚里的空气,就像随时就会爆炸一样。
正当那个丘八要闯进柴棚,举火引祸的时候,忽然听到远处响起几声清脆的枪声。几个伤兵听到枪声连忙作鸟兽状逃出了李家院子,眼看就要引发的灾祸突然间消散了。这时,母亲低头看看怀里的儿子,那不满周岁的德海此时正睁大眼睛,看着黑暗中的天空。好象在说:“这世界怎么啦?”激动的母亲禁不住热泪盈眶,伏在儿子的小脸上,狂吻着这个有灵性的儿子:“德海,你救了一家人的命啊!”
在没有灾祸的日子里,一家人虽然日子过得很苦,但仍不失一个朴实农家应有的欢乐。
德业已经上私塾了,而德海也已经学会帮母亲剥毛豆,抱柴禾了。每当父亲从田里忙回来,德海会立即搬出小凳子,说:“爸爸坐坐。”劳累了一天的父亲,此时疲劳全消,于是在儿子的脸上亲一下,坐下来吸一口旱烟。
当冬日清闲的时候,德业趴在小桌上写字,或摇头晃脑地念着先生让背的新书,父亲则躺在床上,将德海抱在他的肚子上,逗着他玩。在一盏油灯下,母亲在给丈夫或是儿子补衣服,纳鞋底,还会给孩子们讲一个关于狼外婆的故事,而更多的时候,则是听母亲讲那些自幼从外婆那儿听来的有关因果报应的故事。在德业、德海幼小的心灵里,从此落下一颗颗智慧的种子,也从此知道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
虽然多病,但小德海毕竟是一天天长大了。同健壮的哥哥德业相比,他则显得文弱而纤细。如果说父亲将自己的遗传因子更多地给了德业的话,那么,德海则较多地接受了母亲的娟秀和灵气。
有时候,当哥哥德业为先生布置的课文而煞费苦心、绞尽脑汁的时候,弟弟德海在听了哥哥的几遍背诵之后,却能流利地背出让哥哥大伤脑筋的“子曰”,甚至还抑扬顿挫,韵味十足。
就象一棵树上长不出两片同样的树叶一样,虽然同是父母的儿子,但德业、德海两兄弟却有着许多不同,坐在一条凳上,小哥哥粗壮得象一条小壮牛,而弟弟德海却纤弱如一个女伢,哥哥说起话来粗声大气,最爱玩的是刀枪棍棒,而弟弟却爱坐在一处独思冥想,好像他小小的脑瓜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号,有许多难以解开的疙瘩。望着小德海那副深思熟虑的样子,谁也弄不清这小人儿的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哥哥德业上学去了,而他最要好的小同伴阿三这几天也到他外婆家去了。德海嫌家里憋闷得慌,于是,他趁妈妈不在屋,一个人悄悄地出门遛达去了。他不知怎么就走到村中的私塾外面。在这里教书的是太慰庵里的老师公石点和尚。石点师公貌似威严实则温和。德海喜欢听石点师公那抑扬顿挫的读书声,喜欢看石点师公捋着他雪白的山羊胡子,让孩子们念“阿弥陀佛”,每念一声,便将一颗炒熟的花生悠悠地分发到孩子们贪馋的小手心里,接着就放声大笑的样子。他伏在屋外的窗台上,专心地看那些小哥哥们在石点师公威严的戒尺下轮流背书,他觉得那很新鲜也很好玩。
这一次正好是他的哥哥德业被叫去背书,他哥哥背的是《大学》中的语录,当德业背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下面却无法接上的时候,眼看石点师公无情的戒尺就要挥到哥哥的手心时,窗外的德海却替哥哥接下去背“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整个学堂的人都被这屋外清脆的童声惊呆了,包括石点师公。窗台上,一张清秀的小脸在他背后芭蕉树叶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明丽。
石点师公走过去,威严地说:“谁家娃,怎么跑到这儿来玩?”
德海没料到自己不经意间的背诵会引来这么多注意的目光,他怯怯地往后退着,却又不敢拔腿逃离。
石点师公终于认出了那个孩子,他笑着捋了捋胡须说:“哦,想起来了,你是小德海,都长这么大了?”
老师公很喜爱这个聪颖的小孩子,说:“你可以在一旁听嘛,以后,你到我庙里去,我教你识字。”
事后,老师公特意找到李永书,说:“你家的老二德海是大器啊,让他来念书吧,我免收他的学钱。”
永书自然十分高兴,心想,我这儿子,说不定将来真大有出息。但他却说:“这孩子多病,不如他哥哥好养,只怕……”
老师公摇晃着身子连忙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圣人的话是不会错的。”
于是父母商量,无论家里多苦多难,也要让德海进私塾念书,从那以后,德海坐到了私塾里,同那些比自己高过一头的小哥哥们坐在了一起,开始学会摇头晃脑地背:“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学堂的院子里有一株枇杷树,三月,枇杷挂果了,孩子们便开始打那棵枇杷树的主意了。但是,没有谁敢真爬上那棵高大的枇杷树,即使最胆大的孩子,他大胆的结果不仅是弄得满口的酸涩,并且那惹事的小手心说不定还会吃石点师公结结实实的一记戒尺。终于等到枇杷成熟的季节,孩子们像过节一样围到那株枇杷树下,这时,石点师公将早已打下的金黄的枇杷分发到孩子们的口袋里,却特别叮嘱说,回家后待先奉给长亲,尔后方能自食。于是,德海揣着满口袋的枇杷,欢快地跑回家去,将香甜的枇杷送一颗到母亲的口里,送一颗到父亲的口里,再送一颗到隔壁李婆婆的口里,直到所有的长亲都已尝过了,这才坐到小板凳上,有滋有味地吃那些枇杷。
五月,是一年中最忙的季节,私塾里的忙假开始了。中午,父亲让德海将家里的那条老牯牛牵到大畈里去放。于是,德海牵着那条老牯牛同隔壁的阿三一同来到大畈里。牛们在大畈里愉快地啃着青草,孩子们在大树下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阿三提议说,我们到池塘里扑腾怎么样。德海说,先把牛拴好,免得吃了人家的庄稼。中午的太阳很烈,德海和阿三一下子脱净了,扑腾一声跳进了冰凉的池塘里。他们玩得好开心啊,却没有料到阿三家的那条小犍牛不知在什么时候挣脱了缰绳,跑到人家的稻田里。等到发现,好大的一片稻子已经被那畜牲吃掉了。二人知道闯下祸了,连忙爬上岸来,各自牵上自家的牛,悄悄地回家了。傍晚时分,被吃掉庄稼的村伯找上门来,定要永书家赔偿损失。德海待要分辩什么,母亲却用严厉的目光阻止了他。母亲什么也没说,拿出家中仅有的一吊钱赔给了村伯。送走了村伯,母亲命令德海说:“现在,你给我跪下!”
德海便不由分说地跪下了。直到天黑尽了,一家人忙完了,母亲才将满眼含泪的德海拉了起来。母亲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跪下吗?”
“我比阿三大,我应该替阿三管好他的牛。可是……”德海仍然是满眼的委屈。
“儿啊,我知道你是委屈的,我也知道家里的那条老牯牛没有吃人庄稼的习惯。但是你要是不承认,隔壁的阿三就要受处罚,阿三家日子比我们家更难,阿三家又哪里赔得起一吊钱呢?”母亲接着又说:“我就是要让你记住,学会替别人受过。”
德海抹了抹眼泪,心里却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好母亲而感到异常自豪。
命运之神似乎总爱捉弄这个小小的生命。他总是生病总是咳嗽,中药铺里的方子一帖一帖地开着,又苦又涩的药汁一罐一罐地喝着,然而却总没有见好的时候。
郎中说,这孩子,真怕活不长呢,小小年纪,得喉痨病,少见。那时候,小德海最怕冬天,每当寒霜降临的时候,小德海便天天咳嗽,小小的人儿喉成一团。于是村里人都说,只怕德海活不长呢,早晓得是这样,满月那天不如让那疯和尚带走了之。
百药无效,首先感到失望的是父亲,他想,老大生得粗钝,老二又命细,不如再生一个吧。不能怪父亲失望,在旧中国的农村,儿子,是家庭的希望,是一个穷苦家庭的未来,只要有一个健康的儿子,一个家庭便也就有了希望。于是,在德海6岁的时候,父母又生下老三德江。
母亲于氏仍是长斋供佛,请求佛力的加被。每逢初一、十五,母亲总要到附近的寺庙庵堂去烧香礼佛。
8岁那年,德海第一次随母亲到太慰庵去。母亲发现,当远远地闻到一股檀香的气味时,小德海就象换了个人似的,再不象一个有病的孩子,他蹦跳着,叫闹着,象出远门的孩子突然回到了外婆的身边,象锁在笼中的鸟儿回到阔别已久的山林。
他来到庵堂里,而对那壁立两旁凶神恶煞的四大金刚,居然没有半点惧怕,却象是早来过这里,他在笑哈哈的弥勒佛前伏地便拜,好象他早就学过礼佛一样。他来到大雄宝殿,睁着一对惊奇的眼睛,久久地注视着那高高的莲台上安祥端庄的三尊大佛,看得出这8岁孩子的心里对这些神圣的金佛怀着怎样的激动的崇敬。
太慰庵里的石点师公对这个小不点再熟悉不过了,老人从这孩子身上感受到一股生命的活力,感受到一种人生的的快意。
老和尚故意问:“德海,你几岁了?”
“过了端午,满8岁。”
老和尚让他认佛经上的字,小德海捧起那本经书,流畅地读了起来:“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剩下的,他读不下去了。
老人高兴地摸着德海的头说:“孩子,跟我做和尚好吗?”
德海说:“好的,妈妈说我刚满月,就有和尚要带我走……。”
老人开心地笑起来,说:“你真是做和尚的命啊,将来做一个大和尚吧。”
德海不懂什么是大和尚,他想做大和尚一定很开心,于是就拍着手说:“好的,我将来一定做一个大和尚。”
小德海9岁这年,他的一位长亲突然死了。那是一位慈祥的老人,老人每次来德海家时,总是抚摸着德海的头,教他背“人之初,性本善”,背完了,老人突然像变戏法一样从背后亮出一包冰糖或是一片麻饼来。老人爽朗的笑声和摇头晃脑背书的样子曾给小德海带来许多快乐。可是,突然在一天夜晚,当老人安详地睡着了以后,就再也没有醒来。
德海随着父亲渡过一条小河,去给长亲奔丧。他去时,便再也听不到老人那大声说话的嗓音,再也看不到老人摇头晃脑背书的姿态。作古的老人此时正直挺挺地躺在门板上,老人的脸上覆盖着一大迭黄表纸。当奔丧的人进门时,死者的家人便要号啕一番,号啕之后,便又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说说笑笑。
小德海望着那个一动不动的老人,他希望老人会再次爬起来,让他背《三字经》,然后赏给他一包甜丝丝凉润润的冰糖,然而老人却始终不肯起来,于是他知道,这个慈爱的老人是“死了”。
呵,“死”是怎么一回事?人为什么要死?死,就是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明白了吗?而这个老人不是前几天还到德海家去过吗?死竟是这样突然,这样不期而至吗?
他问父亲:“人都要死吗?”
“是的,人到老了都要死。”
“人为什么要死?”
“傻瓜,人当然是要死的,不为什么。”父亲感到儿子的提问实在莫名其妙。
过了一会儿,德海又问父亲:“人死以后,又到哪里去呢?”
这一次父亲有些不耐烦了,父亲说:“你真是个小罗索,问个没完;人死后到土里去,什么都没了。”
这一次,小德海大大地震慑了,从此以后,死亡的恐怖牢牢地笼罩在他幼小的心间,于是他知道,自己也是要到土里去的,而且是“什么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