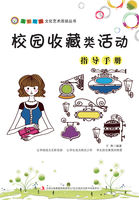正月十九日早晨,钟刚敲五点,白茜就拿着蜡烛来到我的小屋子里,看见我已起了床,穿好衣服。我要在那一天乘马车离开盖茨海德,马车将在六点经过住宅大门口。
天很黑,白茜提着一盏灯笼。冬天的早晨,又湿又冷,我匆匆赶向大门口,我的箱子前一天晚上已经送下来,现在放在大门口。离六点钟只有几分钟了。不一会儿,远远地传来车轮声,通报马车到了。马车来到跟前,只见套着四匹马,车上坐满旅客,管车人和马车夫大声催促,我的箱子给托了上去。我搂住白茜的脖子连连吻她,但被人分开了。
“千万要好好照应她啊。”管车人抱我上车的时候,白茜大声叮嘱。
车门关了。我就这样从白茜那儿、从盖茨海德给带走了,就这样驶向陌生的、在我当时看来还是遥远的、神秘的地方。
一路上的情形,我只记得一点儿。我只知道那天旅程在我看来长得出奇,只知道我们好像赶了好几百英里路。我们穿过好几个城市,在一座大城市里马车停下来了,马给卸了下来,旅客下去吃饭。我给带进一家客店里,管车人要我吃点东西,可是我只怕有谁进来把我拐走,因为我在白茜讲的很多故事里听到过小孩子被人偷走的事。
我终于沉沉入睡了,但不久我就被马车的突然停止惊醒。车门开了,有个人站在车下,借着灯光我看见了她的脸和衣着。
“车上有个叫简·爱的小姑娘吗?”她问道。
我回答说“有”,就给抱下了马车。我的箱子也给卸下来,马车立刻又驶走了。
坐了那么久,四肢都僵了,又给马车的声音和颠簸弄得迷迷糊糊。等到恢复知觉以后,我四下里看一看,空中充满了风、雨和黑暗。然而,我隐隐约约看出前面有一堵墙,墙上有一扇门。我跟着我的新向导穿过那扇门,只见里面有一座有很多窗户的房子,有几扇窗户里灯光闪闪。我们走上一条宽阔的路,从一扇门里走了进去。随后,她带我穿过一条过道,进入一间生火的屋子,就把我一个人留在那儿。
我在火上烤了烤冻僵了的手指,接着向周围看了看。那是一间客厅,虽说没有盖茨海德府上的休息室那么华丽,但也够舒服的了。
一位高个子女士走进来,另一位紧跟在后面。
“这个孩子太小,不该叫她一个人来。”第一个人说道。她打量了我一两分钟,然后接着说,“最好还是马上让她上床睡觉,她看起来累了。你累吗?”她一边说着话,一边将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
“有点儿累,小姐。”
“一定也饿了。让她吃点儿饭再睡,米勒小姐。这是你头一次离开父母来上学吗,我的小姑娘?”
我解释说我没有父母。她问我他们去世多久了,然后便问我的姓名、年龄,以及我会不会读书、写字和做点针线活计。随后,她用手指轻轻地摸一摸我的脸蛋儿,说她希望我是个好孩子,便把米勒小姐打发走了。
那一夜过得很快。我太疲倦了,连梦也没做。睁开眼睛时,听见了响亮的钟声。
一天的功课以背诵《圣经》开始,等背完了,天已大亮。钟又敲起来,大伙儿排着队走进另一个屋子去吃早饭。想到就要有东西吃了,我多么高兴啊!头一天只吃了那么一丁点东西,我这会儿几乎饿昏了。
饭厅桌子上摆着几盆热气腾腾的东西,但是叫我扫兴的是,那股味儿一点也引不起食欲。我看到,大伙儿都表示不满意。行列前面第一班的高高的姑娘们开始嘁嘁喳喳:
“讨厌!粥又烧糊了!”
大家唱了一首赞美诗。随后,一个仆人给教师们端来茶点,早饭就开始了。
我饿极了,如今又乏力,便把我那份粥吃了一两匙,也没去想它是什么滋味。可是最剧烈的饥饿稍微缓和一点以后,我再也吃不下去了。在我周围,汤匙动得都很缓慢。我看到每个姑娘尝一尝她的粥,竭力想咽下去,可是大多数姑娘都是马上就放弃了这个努力。
又唱了一首赞美诗后,大伙儿离开饭厅,到教室里去了。我是最后一个出去的,离开桌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教师端起一盆粥尝了尝。她向别的教师看了看,她们脸上都露出不高兴的神情。
终于钟敲了十二下。谭波尔小姐站起身:
“我有几句话要和同学们讲一讲。今天早上你们早饭吃不下去,现在你们一定都饿了。我已经吩咐过,给大家准备一顿面包和干酪做的点心。”
教师们露出一种诧异的神情看着她。
“这件事由我负责。”她又补充一句,说罢就离开教室。
面包和干酪马上给端进来分给大家,全校的人都欢天喜地。然后老师又下了命令:“到花园里去!”于是我就随着人群,走到露天地里。
我还没跟谁说过话,也没有任何人注意我。我一个人站着十分寂寞,不过我对这种孤独感已经习惯了。我倚在阳台的一根柱子上看着,想忘记寒冷。我偶尔抬起头望望这座房子,只见门上有一块石匾,刻着这样的字:
劳渥德孤儿院——由本都布洛克尔赫斯府上之内奥米·布洛克尔赫斯建造。
我一遍又一遍地念这些字。这时候,背后响起一声咳嗽,我不由得回过头去。我看见一个姑娘坐在石凳上读书,她翻书的时候碰巧抬起头看到了我,我立刻对她说:
“你那本书有趣吗?”
“我很喜欢它。”她停了一两秒钟,打量我一下,然后回答。
“书里说些什么?”
“你可以看看。”那姑娘一边回答,一边把书递给我。
我也喜欢读书,但我很快发现这本书对我来说实在太难了。我把书还给她,她默默地接过去。她正打算继续埋头看书,我又大胆地打扰了她:
“你能不能告诉我,门上那块石匾上写的字是什么意思?劳渥德孤儿院是什么?”
“就是你来住的这所房子。我看,你是个孤儿吧?”
“在我懂事以前,我的父母都去世了。”
“对了,这儿的姑娘都是失去了爹或妈,或者父母都已经去世。这儿就是个教育孤儿的地方。”
“我们不付钱吗?他们白白养活我们吗?”
“我们自己付,或者是我们的朋友付,每人十五镑一年。但这不够,不足的数目由本地和伦敦的好心肠的太太先生们补足。”
“内奥米·布洛克尔赫斯是谁呢?”
“是建造了这座房子大部分的那位女士,这儿的一切都由她的儿子照料和经营。”
“这么说,这座房子不属于那个说给我们吃面包和干酪的高个子女士了?”
“谭波尔小姐吗?当然不是。我倒希望是她。可是她做的一切都要对布洛克尔赫斯先生负责。这里的所有食物和衣服都是由他采购来的。”
午饭以后,又开始上课,一直到了五点钟。
下午惟一可注意的事是:我看见跟我在阳台上谈话的那位姑娘在上历史课的时候,被从班上可耻地撵了出来,站在大教室的中央。我觉得受这种责罚是非常丢脸的,尤其是这么大的一个姑娘——她看上去总有十三岁了,或者还不止。可是,让我吃惊的是,她既不哭也不脸红。
“她怎么能那样安静地忍受下来呢?”我暗自思忖,“她看上去似乎在想着什么超出她的处境的事。她想着的是她记忆中的事,而不是她眼前的事。我不知道她是哪种姑娘——好姑娘呢还是坏姑娘?”
下午五点过后不久,我们又吃了一餐,吃的是一小杯咖啡和半片黑面包。我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可是肚子仍觉得饿。接下来是半个钟头娱乐,然后是学习。再后来是一杯水、一片面包、祈祷和上床。这就是我在劳渥德的第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