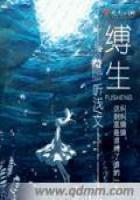保尔好不容易才把脚从黏糊糊的泥里拔出来。他感到脚底下冰冷刺骨,不用看,他就知道是那只破靴底整个儿掉下来了。他从来到这儿的第一天起,就吃够了这双破靴子的苦头,靴子总是湿漉漉的,里面的泥浆被踩得嘎吱嘎吱响。这下更好了,一只靴底掉了下来,他只好光着脚板泡在冰冷刺骨的烂泥里。他从烂泥里捡起破靴底看了看,虽然他已经发过誓不再骂人,但这时候还是憋不住了。他提着破靴子朝板棚走去,在行军灶旁边坐下,解开沾满污泥的包脚布,把那只冻得麻木的脚伸到炉子跟前。
奥达尔卡正在案板上切甜菜,她是厨师的下手。这个巡道工的妻子毫无老态,虎背熊腰,胸脯高高,大腿粗壮,切起菜来,刀工高超,一会儿案板上便堆起一座小山。
奥达尔卡轻蔑地瞥了保尔一眼,挖苦地问:
“你等饭吃吗?还早了点儿吧。你这小伙子显然是偷懒溜过来的。你把脚伸到哪儿去?这儿是厨房,不是澡堂子!”
一个上了年纪的厨师走了进来。
“靴子全烂了。”保尔向他解释说。
厨师看了看破靴子,朝奥达尔卡那边点点头,说:
“她丈夫是半个鞋匠,帮得上忙的。没鞋穿,可真要命。”
奥达尔卡听了厨师的话,再仔细看看保尔,有点不好意思。
“我把您当成了懒汉。”她抱歉似的说。
保尔温厚地笑笑。奥达尔卡用行家的眼光查看那只靴子。
“我家那口子才不补它呢,这根本不能穿了。我家阁楼上有一只旧套鞋,我给您拿来,可别冻坏了脚。唉,受这种罪,哪儿见过啊!明后天就要上冻,您千万得小心。”奥达尔卡同情地说。她放下菜刀,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她回来了,拿着一只高统套鞋和一块亚麻布。保尔用布包好脚,烤得热乎乎的,伸进了暖和的套鞋。
板棚里挤得水泄不通。120个人都挤在这里,有的靠板壁站着,有的爬上了桌子,甚至灶台上也站着人。
潘克拉托夫宣布开会。托卡列夫讲话时间不长,但是最后一句话,使大家惊呆了:
“明天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不能回城。”
老人的手在空中挥了一下。这个手势把大家摆脱污泥,回城同家人团聚的希望一扫而光。一开始,会场闹哄哄的,有人强烈地表示渴望“家庭的舒适”,有人气恼地叫喊,说累坏了,更多的人则沉默不语。角落里,一个人脸红脖子粗地连喊带骂:
“见他妈的鬼了!凭什么罚我们?逼我们干了两星期,该够了吧。谁决定的,谁自己来干。我可只有一条命。我明天就走。”
这个叫嚷的人就站在奥库涅夫背后。奥库涅夫划着一根火柴,想看看这个逃兵。火柴点燃的一瞬间,照亮了他那张气歪的脸和张大的嘴。
“你照什么?我不躲不藏,又不是小偷。”
火柴灭了。潘克拉托夫站起来,挺直了身子。
“谁在这儿胡说八道?弟兄们,咱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城去。要是咱们溜走,许多人会冻死的。
这个码头工人不喜欢发表长篇大论,但是,就这么短短几句话,也被刚才那个人的声音打断了:
“那么非党非团的可以走吗?”
“可以。”潘克拉托夫明确无疑地说。
那人朝桌子挤过来,他扔出一张小小的证件。
“这是我的团证,收回去!我可不为这么一张硬纸片卖命!”
他的后半句话被全场爆发出来的斥骂声淹没了。
“你钻进共青团,图的是升官发财!”
“赶他出去!”
扔掉团证的那个家伙缩着脑袋朝门口挤。大家像躲避鼠疫患者一样闪开。他刚走出去,门就嘎吱一声关上了。
潘克拉托夫抓起扔下的团证,放到小油灯的火苗上。硬纸片烧着了,卷起来,变成焦黑的一团。
突然,树林里传来一声枪响。有个骑马的人迅速逃离破旧的板棚,钻进黑漆漆的林子。人们从学校和板棚里跑出来。有人发现了一块插在门缝里的胶合板。划亮火柴,借着火光,看到胶合板上写着:
通通滚出车站!从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谁敢留下,叫他脑袋开花。我们要斩尽杀绝,一个不饶。限明天晚上以前滚蛋。
大头目切斯诺克切斯诺克是奥尔利克匪帮的一个头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