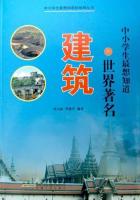裁缝的妻子还没走的时候,我主人家住宅的楼下搬来了一位黑眼睛的年轻太太,她带着一个小姑娘和头发花白的老母亲,那老太婆成天到晚叼着琥珀烟嘴抽烟。年轻太太长得很美,样子威严、高傲,说起话来声音低沉、好听,看人的时候,总是仰起头,微微眯起眼睛,就好像人家离她很远,她看不清楚似的。
有个黑脸士兵丘费耶夫,几乎每天都把一匹细腿的红马牵到她住宅的门口。太太就走出来,站在台阶上。
“罗贝尔,罗贝尔。”她声音柔和地说,用力拍拍马儿曲线优美的脖颈。
随后,她一只脚踩着丘费耶夫的膝盖,灵活地一纵身跃上马鞍,那匹马便高傲地踏着舞蹈般的步子,沿着土埂跑起来。
她端庄优雅,那是一种罕见的美,让你每一次见到她都觉得新鲜,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而且总是让你的心顷刻之间漾起陶醉的欢欣。
一群驻扎在城里的师部军官经常围绕在她的身边,每天晚上在她家里弹钢琴、拉小提琴、弹吉他、跳舞、唱歌。军官当中来得最勤,总在她身边打转的是少校奥列索夫。这人是个胖子,红红的脸膛,头发已经花白,身上总是油光光的,就像是个轮船上的机修工。他吉他弹得很好,在这位太太面前,举止很恭顺,就像是她的忠实奴仆。
5岁的小女孩儿也像她的母亲一样天生丽质,她长得胖乎乎的,一头鬈发,一双碧蓝色的大眼睛放射出严肃而平静的目光,似乎在期待着什么。在这个小姑娘的脸上,有一种与孩子的年龄不相称的沉思表情。
小女孩儿的外祖母从早到晚操持家务。她的两个帮手是愁眉苦脸、一声不响的丘费耶夫和眼睛斜视的胖胖的女佣人。因为没有雇看孩子的保姆,小女孩儿几乎无人看管,整天在门口的台阶上或在门口对面堆放木头的地方一个人玩耍。我时常在傍晚时,陪着这个小姑娘玩一会儿。我很喜欢她,她很快就跟我熟悉了。
她很聪明,但是并不怎么快乐,一种淡淡的、严肃的忧伤笼罩着她。她紧紧地依偎着我,蓝色的眼睛满是期待地望着天空,一字一句地说:
“姥姥常发脾气,妈妈从来不生气,她只是笑,大家都爱她,因而她总是没有时间。家里老是来客人,都是来看她的,因为她漂亮。她是可爱的妈妈,连奥列索夫都这么说:可爱的妈妈!”
我特别喜欢听这个小姑娘说话——她所讲的是我不熟悉的另一种环境。她总喜欢讲她的妈妈,而且一说起来就很多。于是,一种崭新的生活便悄悄地展现在我的眼前,使得我对生活更增加了兴趣。
有一天傍晚,我正坐在门口台阶上,等候主人们从奥特科斯散步回来。小女孩儿正在我怀抱里打瞌睡,恰巧她的母亲骑着马回来了,那太太轻盈地跳到地上,把头一扬,问道:
“她这是怎么啦,睡着了?”
“是的。”
太太把马鞭子掖在她的宽腰带里,伸出两只手说:
“把她交给我!”
“我抱她进去吧!”
“不!”太太冲我喊叫,就像在吆喝一匹马,还在阶上使劲跺了一下脚。
小女孩醒了,眨巴着眼睛,看了看母亲,向她伸出了手臂,她们便一起走了。
过了几分钟,斜眼的女佣人来找我,说是小女孩儿耍脾气,不跟我告别就不肯睡觉。
我走进客厅,在小姑娘的母亲面前很是得意。小女孩儿坐在母亲的膝盖上,那太太正用灵巧的手给女儿脱衣服。
“明天再见。”小女孩儿说,冲我伸出了手。
等小女孩儿走了,太太伸出一个手指头叫我走过去。
“送你点什么东西好呢?”
我说,什么东西都不必送给我,只希望她能随便借给我一本什么小书看一看。
她用温暖芳香的手指托起我的下巴,欣喜地问:“你为什么喜欢看书呢?”
我尽可能简单明了地给她解释,说生活很艰难也很苦闷,而有书可读,就能忘记这些痛苦。
“噢,原来是这样!”她说着站起身来,“这话说得不错,也许很有道理……得,这样好不好?今后,我可以把书借给你,只是现在我手头没有……不过,这本书你先拿去看看吧……”
她从沙发上拿起一本书,黄色封面,书的边角已经磨损。
“你先读完,然后我再给你第二本,一共有4本……”我离开了这位年轻太太的家,带着一本梅谢尔斯基公爵写的《彼得堡的秘密》。我开始全神贯注地读这本书,但是从开头几页起,我就觉得它实在乏味得很。倒是一则关于自由与棍棒的寓言让我觉得挺有趣:
“我比你强,”自由说,“因为我比你聪明。”
但棍棒回答她说:
“不,我比你强,因为我比你有力量。”
他们争着争着便动手打起来了,棍棒把自由狠狠地揍了一顿。后来,据我所知,挨了打的自由死在了医院里。
后来她又借给我一本普希金的长诗集。我一口气把书读完了,由始至终都沉浸在如饥似渴的感情中。当你偶然到了一个从未见过的风光优美的去处,就会体验到这种情感,急切地想要立刻把这个地方跑个遍。当你在森林沼泽地沿着长满青苔的土墩土埂长时间跋涉以后,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一片干燥的林间空地,鲜花盛开,阳光灿烂,那时候你便会生发出这种情感。你会如痴如醉地打量着这片旷地,然后满怀欣喜地四处奔跑,你的脚与沃土上软绵绵的绿草每接触一次,都会带给你无尽的喜悦。
普希金诗句的纯朴与音韵的和谐使得我非常惊奇,以至于此后很长时间总觉得散文不自然,读起来词句别扭,十分拗口。
普希金那些极为精彩的童话,对我来说最为亲切,也最通俗易懂。我一连读了好几遍,直到能把它们背诵出来了,我才上床睡觉。我不止一次把这些童话诗讲给勤务兵们听,他们一边听,一边哈哈地笑,还亲昵地骂上几句。西多罗夫抚摸着我的头,小声说:
“真的,是吧?嘿,上帝啊……”
当我怀着惆怅把书还给那位太太的时候,她还向我简明扼要地讲述了普希金的生平和他是怎么死的,后她问我都喜欢哪些诗。
我对她说喜欢什么诗,还挥舞着两只手,背诵记住的诗句。她默默地、郑重其事地听我背诵,然后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若有所思地说:
“你呀,可爱的小东西,真该去上学啊!这件事让我来想想办法……你的主人是你的亲戚吗?”
看到我肯定地点了点头,她惊讶地叫了一声:
“哦?”那声音仿佛是在责备谁。
后来她又借给我一本《贝朗瑞歌谣集》,这些歌谣把揪心的痛苦和奔放的快乐之情奇妙而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让我简直迷恋到了疯狂的程度。
除了读书外,主人家归我干的活越来越多,我要承担该由女仆做的日常家务,还要当门房,做“跑街采买”。此外,每天我还得用钉子把细纱布钉在宽木板上,再把设计图纸贴在上面,还得誊写主人建筑工程的预算,检查核对包工头的账目。我的主人更是从早到晚工作,就像一台机器。
那几年,市场上公家的建筑正陆续转到商人手里,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一排排商店匆匆忙忙地改建,我的主人接受承包业务——修缮店铺门面,建筑新商店。他还绘制“翻修圆拱、过梁、开凿屋顶开窗”等诸如此类的设计图。我拿着这些图纸,外带一个里面装了25卢布钞票的信封,去见一个上了年纪的建筑师。那建筑师收下钱,就在图纸上签名,写上“图纸与实情相符,工程监督由本人承当,某某。”自然,实际情况他并没有见到,工程监督他也不来担当,因为他正在生病,根本就出不了家门。
我常常把贿赂分送给市场管理员和各种必要的人员,从他们那里得到各种必需的文件,照主人的说法,叫做“从事各种违法活动的许可证”。由于这些活动,我得到一种权力——主人们晚上外出做客的时候,为他们等门。这种机会虽说并不经常有,但有时候他们回家很晚,往往在半夜以后。这样,我就能连续几个小时坐在门口的平台上或者门口对面的圆木堆上,望着我认识的那位太太家的窗户,满怀渴望地倾听那里欢快的谈话声和音乐声。
窗户敞开着,透过窗帘和花卉的阴影,我看见军官们匀称的身影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矮胖的少校像球一样滚动,那位太太打扮得简朴而又美丽,步态轻盈,像在飘动。
我在心里把她叫做玛尔戈王后。
每当我看到我所敬重的那位太太独自一个人在房间里弹钢琴的时候,我心里更愉快。音乐声使我陶醉,周围的景物似乎全都消失了,我的眼睛只盯后面黄色灯光下那女人秀美的身姿,那高傲面庞的侧影,还有在琴键上鸟儿一般上下翻飞的两只白皙的手。
左邻右舍的街坊,我们院子里的一班子人,尤其是我主人一家子,都怀着恶意说玛尔戈王后的坏话,不过说话稍微谨慎些,声音压得低一点儿,并且时不时地扭头朝四下里张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