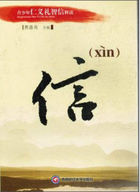连接不断的采访和演讲让我在1913年秋天忙个不停,几乎整个秋天都是在旅途中度过的。我们的经历越来越丰富,我们在华盛顿乘过摇来晃去的乡下电车;在纽约州我们搭乘过一班特别的早班车,这班早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一路上只要遇到农舍它就会停下来收购牛奶,因此,这一路上经过多次停留才达到目的地。
那年,得克萨斯和路易斯安那经历了一次洪水,我们去的时候还可以感受到洪灾留下的痕迹,路面上仍然有不少积水。我坐在车内都能觉察出水流拍打着车厢的震动。突然间,传来“砰!”的一声巨响,车体颠簸并摇晃了一下,车上的乘客惊慌地往外探视,原来水面上漂浮着一段粗大的浮木,车躲避不及,正好撞上,然而令乘客们触目惊心的还有那些漂浮的牛马的尸体,一根被洪水连根拔起的大树竟然挂在我们火车的车头上,它也成了我们的旅伴。
那时,有许多单位和团体邀请我们去演讲,我们去过城市的学校;和妇女协会打过交道;我们深入到偏远的乡村和矿区;有时还到繁华的工业城市为劳工团体演讲。在这期间,我深入了各个阶层,对社会有了更全面的认识,这使我的人生观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以前的想法流于肤浅。比如,我常常认为,即使生理有缺陷,我也照样能和正常人一样享有幸福的生活,可见,只要自己努力去做,天下没有做不到的事,那不是命运所能主宰的。我在这样想的时候,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我拥有的幸福生活主要得益于别人的帮助。虽然我又盲又聋,但是我又是个幸运儿,因为我的家庭幸福美满,如果没有慈爱的父母,没有莎莉文老师和许多好友的协助,我根本就不可能接受高等教育。但是,对这一点我在起初并没有深刻的体会,因而我的观点流于肤浅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今,我对环境对一个人的一生产生的影响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从那些工业区和矿区中的劳工身上,我更加明白,有时候人在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面前真是很无奈,也许他很努力地去做了,但是,命运并不会让他的生活充满阳光,让他实现自己的愿望。
这种想法逐渐在我的心灵深处扎下了根,但我还不至于产生宿命的观点,所以我还是比较乐观的,而且从我和别人命运的对比中,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人生在世不但要自己奋斗,而且还要互相帮助。只要我们时刻为希望奋斗不懈,就能打破逆境对我们的禁锢,而那些飞黄腾达和一生通达的人更有责任和义务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解决困难。
1914年1月,我终于有机会横穿美国大陆了,而且让我欣喜不已的是,母亲将陪同我前往,她一直喜欢旅行,现在我终于可以让她实现自己的夙愿了,而且在旅行中,我们可以互相照应。我们一路上可以享受东起大西洋海滨、西对太平洋海岸的美国大陆风光了。
我们演讲旅行的第一站是渥太华,接着到了俄刻俄州,中途因为计划有变,我们去了一趟伦敦,后来辗转到了密歇根州,随后是明尼苏达和爱荷华,接着一直向中西部行进。
旅行中,母亲虽然兴致高昂,但是还不时担心我会太劳累。她对加州情有独钟,到了那里她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到了黄昏,我们徜徉于海滨的沙滩上,常常乐不思蜀。她忍不住赞叹这里气候适宜,而且一再表示自己喜欢海边风光。
我和母亲曾搭气船出海,享受柔和的海风,那些在我们船尾盘旋飞翔的海鸥吸引了她,她似乎童心未泯,用食物引诱它们,想和它们亲近。母亲是个非常有诗意的人,日落时分,她用诗一般的语言向我描述笼罩在夕阳余晖下的金门桥。她还以崇敬的口气告诉我,美国衫是神秘的“植物之王”,赞叹它的王者之风足以使那些山川大泽折服。
现在,我一面写作,一面重温那段愉悦的时光,那些点点滴滴的快乐就在我的笔端蜿蜒而出,流泻在这一篇篇文章上。我仿佛又看到了“岸之家”;看到了我们追逐嬉闹的海边;看到了我们踩踏过的开满各色野花的小沙丘;看到了海边嶙峋的怪石……
我站在双子海角,任凭清爽的海风吹拂着我的脸颊,母亲突然把我拉到她的身旁,无比激动地告诉我:“看一看这些伟大的自然风景,我的心灵似乎得到了净化和抚慰,我人生中所有的悲伤和不快都随风消逝了。”
母亲告诉我,从这个海岬可以看到远处的城市,以及海岬沿岸繁华的街道,而且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那里的钟楼。海港似乎很热闹,因为每隔五六分钟,就有一班渡轮鸣着汽笛从海港中缓缓驶出。
1914年10月,我开始第二次横越美国大陆进行演讲旅行,秘书汤姆斯小姐一直陪伴着我。
她的工作琐碎而劳累,事无巨细,都要她亲自处理,包括我的日程安排、演讲接洽、事后交接,有时还要根据变化调整计划。汤姆斯小姐是个精明能干的人,她做事从不拖泥带水,而且能将大大小小的事情安排得有条不紊。如果精力和时间允许,她还照料我的生活起居,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我时常想,要是没有她这个助手,真不知道我的生活情况会怎样。尽管卡内基先生资助我们一笔钱,而且数目可观,但是我们还必须努力工作,因为我们的日常开销相当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我的旅行演讲受到了很大影响。首先我们不可能和以前一样想到哪里在就到哪里,另外,当我站在演讲台上时,只要一想到正在进行中的那场愈演愈烈的战争浩劫,我就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轻松地说些仁慈的话了。也许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段时期,我常常梦见血腥和杀戮的场面。在此期间,一些出版社和杂志社向我约稿,要求文风活泼有趣,素材新颖入时。可是,那时我满脑子都是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和枪林弹雨中的士兵,哪里有心情写这些文章呢?
当时我收到了数千封来自欧洲的求援信件,但是,很遗憾的是,对此我也茫然不知所措,而且当时我也自身难保,为了生计四处演讲,在那段时期,我所属的团体展开了热烈的反战运动,热烈地呼吁停止战争,维护和平,想方设法阻止美国成为战争中的一份子。但是以老罗斯福总统为首的团体和我们恰恰相反,他们不遗余力地积极主张美国参战。
我和莎莉文老师是坚决的反战者,认为避免美国卷入战争是众望所归,为此,我们从1916年开始,四处做反战演讲。足迹遍及得克萨斯州、密歇根州、内布拉斯加州等地。但是,我们的努力只是徒劳,最终美国还是卷入了漩涡。
在每个可能的地方,我和莎莉文老师都会毫无顾忌地前往宣传和呼吁,我们曾经在富丽堂皇的礼堂演讲,也在临时搭建的小帐篷里陈词,我们的演讲在听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可不可思议的是,当时大多数媒体对我们的观点不理不睬,这个尚且能够理解,但是,有些报刊的态度却令我们费解,以前他们不惜扭曲和夸大事实,把我奉为“时代的奇迹”和“盲人的上帝”,可是,现在却把我当做政治上的左翼和叛徒,大肆抨击,而且被他们批判得一无是处。
当然,听众也有许多主战派,和我们的反战思想分庭抗礼,最主要的是大众传媒也在散播参战的必要和好处。不久,参战思想便弥漫了整个美国。
当时,我大失所望,直到现在。也不知道如何才能表达出那时的心情!1916年秋天,我身心疲惫,垂头丧气地回到了连杉,也许家能让我平静,可是我仍然觉得悲哀,汤姆斯小姐回苏格兰去了,梅西先生和莎莉文老师分居后就离开了这里,还好有女仆依恩在,她见我回来,兴高采烈地收拾好房间,把屋里屋外装饰一新,然后让我静待满园花开。可是,她哪里明白我的心思,这个时候我怎么会有赏花的心情呢?最后,我想到了母亲,她接到电话就搭车来到了我的身边,让我这颗寂寞而疲惫的心有了些许安慰。
此后不久,莎莉文老师由于疲惫和忧郁,再加上身体弱,再次病倒了。她一直在咳嗽,医生建议她冬天最好离开这里,布拉夕度湖畔更有利于她养病。眼见着原来热热闹闹的家不久将天各一方,我的心里难受极了。如果老师要走,那么依恩也必须离开,因为我们已经没有能力雇佣他了,但是我们和她已经有了深厚的感情,怎么舍得让她走呢?而且她一走,我们在连杉的生活必然会陷入窘境。
我的所有烦恼都源于这件事,从早到晚,我都在考虑如何处理这些事情,没有心思思考任何问题,工作因此耽搁下来。我忽然觉得人生无趣,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产生这种消极的想法。
我常常恐惧地自问:“要是莎莉文老师现在也和我一样如此悲观,那我们岂不是没有任何希望了吗?”
莎莉文老师是我的精神依托,她使我的生活变得妙趣横生,丰富多彩,如果她和我分开了,我就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了。越是这样想我的心情就越不平静。
我从未觉得自己是如此无助,也许正是这样的一种心情催化了我和一位青年的感情。
汤姆斯小姐离开后,秘书的职位由一位年轻人暂代。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书房里思考问题时,他进来了,神态非常平静,他温和地表示要关怀我,我对他的倾诉衷肠深感意外,但随即为他的真诚所感动。他对我表示,如果我愿意嫁给他,他会陪伴着我读书、写作,帮助我搜集资料,莎莉文老师为我所做的一切他都可以做到,而且对我不离不弃。
对方的这一份爱意激起了我心底的波澜,我幸福得颤抖起来,任凭我怎么控制都不管用。我欣喜地想把这个幸福的消息告诉莎莉文老师和母亲,可是,他却阻止我说:“我认为现在告诉他们,时机还不成熟。”
停顿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现在,莎莉文老师病得那么厉害,而你母亲对我还不太了解,现在说出来,她们有可能觉得太突然,说不定还会反对。我觉得过一段时间再找机会告诉她们会更好一些。”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共同渡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我们在树林里悠闲地散步,或者在书房里一起学习,他会念书给我听。
直到一天早晨,母亲跌跌撞撞地闯进我的房间,问我:“看啊!报纸上竟然有这样的消息!太不可思议了,海伦,你已经答应要和别人订婚吗?”
说话时,母亲的手一直在颤抖。这突如其来的事情也让我震惊不已,我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只想替对方掩饰,因则信口说道:“报纸尽会闹些无中生有的事,我对这件事毫不知情。”
我不仅对母亲撒了慌,而且对莎莉文老师的询问也如此说。不久,母亲就辞退了那位秘书。到现在我仍然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什么会一口否认,以至于母亲、莎莉文老师和那位秘书都感到痛苦,这段美好的爱情就这样匆匆结束了。
这一年是充斥着烦恼的一年,但终于也熬过去了。
布拉夕度湖的气候寒冷,莎莉文老师在那里病情不仅没有好转,相反却有加重的趋势,因此,到了5月底,汤姆斯小姐陪同她到波多黎各养病,直到第二年的4月份才回来。在那段时期,我每个星期都会收到她们的来信。
读了她们的来信,我领略了波多黎各迷人的风光和宜人的气候,还了解了闻所未闻的花卉,就在这时候,美国参战了,因此,莎莉文老师提前在4月就回到了我们身边。虽然她回到了连杉,但是真正恢复健康还是第二年的秋天,在为期一年多的休养期内,我们只是在做一些平常的事,没有举办任何演讲。
没有工作,也就没有收入,因此我们的存款也在一天天减少,长此以往,也会坐吃山空。为了减少开支,我们决定卖掉连杉的房子,另找一幢小一点的房子。真正要搬出这所生活了多年的房子时,我觉得难以割舍,心中发酸!这屋子里的任何一件东西变得分外亲切,桌子和椅子都成了感情丰富的老朋友。尤其难舍的是那张我常常在上面进行创作的书桌。还有我的书柜、面对着庭院的落地窗和安放在樱花树下的安乐椅,我依依不舍地抚摸它们,就像和老朋友握手告别一样。然而,离别的那一刻终将来临,我只有洒泪挥别,将这一切珍藏在记忆中最值得回忆的一角了。
带着感伤,带着无奈,我们最终离开了居住13年的房子。这幢可爱的房子会承载更多的温暖和幸福,我们只有这样想,聊以自慰。
现在,这幢漂亮的房子被波士顿的约丹·马许百货公司买下了,作为宿舍提供给女职员。尽管我不再是它的主人,但我还是对它念念不忘,因为那里留存了我太多的记忆,还记录着我无数的欢笑和泪水,那些美妙的往事和那幢可爱的房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