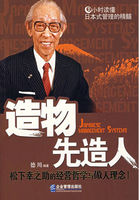歇洛克·福尔摩斯!
还不到一年之后,也就是一八九一年十二月,阿瑟·柯南·道尔医生的大名,已经众所周知了。他的第六个新短篇小说——《歪嘴的人》在十二月号的《史全德》杂志刊出。至今,还有些人认为这是他最好的一篇侦探小说,虽然华生医生的基督教气味名字有点奇怪,但谁能忍得住不看它呢?
在幽暗的台灯灯光底下,我看见他坐在那儿,嘴里含了一根老石南根烟斗,眼睛茫然的凝视着天花板一角,蓝色的烟袅袅上升,灯光照在他沉默、静止、鹰一般有力的面孔上。
由薛尼·派吉所画的那个瘦削的身影,如今人们熟悉得一如公共马车一般,这些依目的地不同漆成白色、绿色和巧克力色的马车,白天涉过泥地,晚上则在吱吱作响的蓝色弧光灯下,整个伦敦市到处可见。马车顶上,有个没有任何女士敢坐的位子,因为马车夫往往会转过身来讲些调戏的话,然而,现在马车夫的话题已换成福尔摩斯了。同样的话题在《声报》拜瑞的短文之中,也出现一个自称(很不幸的)为路加专家的专栏之中。但是,作者本人在哪里呢?
柯南·道尔医生和医生夫人的朋友都知道,这位医生在参加了一个眼科专题演讲会,又参观了巴黎的蓝杭特之后,已于一八九一年三月由维也纳回来了。在伦敦,他们与侯金斯太太和他们的孩子,一起住在鲁塞广场蒙特古街二十三号,就在戴文郡一群名医的诊所中间,柯南·道尔医生设立了他的眼科
诊所。可是,没有一个病人上门。
经过一场几乎使他丧命的流行性感冒之后,他终于做了一个长久以来一直令他犹疑的决定,放弃行医,完全以写作为生。六月时,他在南诺雾找到一幢八字屋顶的大红砖房子,现在,他不但可以供养他自己的家庭,还可以供养他的几个妹妹。
他有很充分的理由相信他有成功的可能。
有一位有着棕色胡子的乔治·纽因斯先生,靠着《珍闻》杂志赚到一大笔财富,最近又新创了一个杂志叫《史全德》。纽因斯先生正是一八八四年时柯南·道尔曾经挑战过的那位《珍闻》的编辑——“下注吧,我跟你赌!”
柯南·道尔自己是否记得这件事无关重要。然而这位年轻医生,如何经由他能干的文学经纪人威特,把《波宫秘闻》这个短篇小说寄给《史全德》,现在却是历史的一部分了。今天的我们可以经由创作者的信函,以及重新发现的新史料,来深入研究福尔摩斯的生活。
通常,我们说他筹划了十二个短篇小说,而这十二篇小说后来集成了《福尔摩斯办案记》,但事实上,当时他心中并没有这样的长期计划。一八九一年四月初到八月初之间,他寄出了六篇小说,而这六篇小说,其实已是他打算全部写的。
在纽因斯的监督下,《史全德》的执行编辑是戴眼镜、大胡子、精明的格林豪·史密斯。格林豪·史密斯付给这位新作者平均每篇小说三十五英镑,还得再减去经纪人费用。这些钱,加上他的储蓄及他的小说出版,对他而言,应该让他在经济上无忧了。当《波宫秘闻》在《史全德》六月份的杂志刊出之后,福尔摩斯在秋天来临以前,便已成为最受大众欢迎的小说人物,编辑立刻邀约更多的小说;但柯南·道尔拒绝了。
因为他手中有更想做的事。
最开始,他很高兴的搬进了在南诺雾坦尼森路十二号的新家。窗框漆成白色,衬着深红色的砖墙,分外醒目,前门有个阳台,花园有墙,房子坐落在半乡下的郊区,你可以呼吸到远方舍瑞岗上的新鲜空气。近处有若隐若现的水晶宫,还有一个幽深的院子,玛莉·路薏丝可以在里面嬉戏。第二年,他决定整
出一块可以打网球的草坪。由于他一直对新机械制品着迷,所以他也买了一辆双座脚踏车;他发现自己和桃薏总动不动就骑上这辆车,在乡间小径上冲来冲去,一天可以跑三十哩路。
现在,把双排扣的长礼服束诸高阁,把优雅的专业姿态丢一边,他可以深深的吸口气。他是个自由人。
生活中最重要的事莫过于他严肃文学的写作。《白色同伴》仍在《康岗》
连载,有可能年底出单行本。他深知,这本书一定会成功。而将近一年的时间中,他一直构思一部新的历史小说。这部新小说,应该部分根据路易十四的宫廷记载,部分根据美国历史学家派克曼的著作,内容应该包括大帝王的宫廷,再穿越过大西洋,进到加拿大黑森林中,那里印第安易洛魁族战歌在林中回荡。书中的英雄则应该是法国的新清教徒,在小说所设定的一六八五年,他可以把麦加·克拉基和迪西莫斯·萨克森唤回。他可以……在这同时,《史全德》杂志的编辑急得快疯了。
六个福尔摩斯的短篇已快刊完。如果这个连载要继续到一八九二年,那么至迟十月续稿就该有着落才行。现在不止俱乐部的一干老绅士,甚至连女读者都看福尔摩斯。
“《史全德》,”柯南·道尔一八九一年十月十四日写信给母亲时说,“不断求我继续写福尔摩斯。我将他们最近的一封信附上。”
这一刻,他真的犹疑了。一方面,他们付他这些小说的刊载费毕竟很高,但另一方面,他那部法国—加拿大的小说就要动笔了,暂定为《难民》。如果写六个福尔摩斯短篇,会延迟他真正想做的事;这样的两难最激怒他。有没有可能,他向《史全德》要求一个事实上极不合理的高价,那事情不就马上解决了吗?
“于是,”他继续给母亲的信,“我会告诉他们,不论小说长短,他们得付我五十英镑一篇,这样我就写。”——“不论小说长短”这句,他特别用斜体字写出——“如此他们也许会考虑放弃。我这个方法似乎有点傲慢,不是吗?”
他们是否觉得太傲慢已无关紧要。回信立刻就到,条件完全同意。何时可以拿到稿子?拜托,事情十分紧急。
圣诞节第二天早上,我去拜访老友福尔摩斯,向他贺节。他穿着紫色便袍,正懒散的靠在沙发里……
就这样,第七个故事开始了,作者闭着眼睛,揣测着福尔摩斯的心理状态。在南诺雾,秋风把落叶吹得在僻静的街道边飞舞。“我们的房子被风吹得好像摇摇摆摆,我以为窗子整个要被刮进屋来了。”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早晨由八点工作到中午。傍晚再由五点写到八点,大门左边的书房里,油灯总是亮着。
“上礼拜,”他十月末的信中写道,“我完成了两个福尔摩斯新短篇——《蓝柘榴石探案》及《花斑带探案》。后者颇刺激。我已想好了第九个故事,因此,剩下的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在所有的评论声中,没有人比他母亲对福尔摩斯更热心。从他开始写作以来,他一定把每一篇小说或故事的定稿寄给她:她的批评,他十分重视。他母亲自己急切到自己构思起福尔摩斯的新案子来,她寄给他一个新构想。故事是一个有一头美丽金发的女孩,她被绑架了,头发也被剪了,然后,为了某个邪恶的目的,被装扮成另一个女孩。
“有关这个金发的构想,我实在编不出情节来,”他承认,“不过,如果你有什么新的念头,一定要让我知道。”
在十分糟糕的雨季,全家人大部分时间都只好留在家中,他继续着他的工作。到十一月十一日,他终于可以向母亲报告,他完成了《单身贵族探案》、《工程师拇指探案》及《绿玉冠探案》,他答应的短篇小说就只差一篇了。他表示,这些短篇他自认都相当够水准,而且,把这十二个短篇集成一册,应该是本不错的侦探小说。
“我想,”他不经意的又说,“最后让福尔摩斯被杀,把他永远的结束掉。他把我的心神从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上拖走。”
把福尔摩斯杀掉的建议,首先在一八九一年末提出来,快把他母亲吓死了。“你不会!”她被激怒了。“你不能!你不许!”困惑而且不知所措,他
问道,那他该怎么办。母亲,就像他还是个十岁的小孩时那样严厉的回答,他可以采用她金发女孩的构想。
于是,母亲的金发构想被转变成不太突出的棕发斐奥丽特·亨特小姐;肥胖的杰佛诺·罗凯瑟先生在他漆着白漆的丑陋屋子中笑个不休;柯南·道尔以《红榉庄探案》结束了这次连载。福尔摩斯的命被母亲救了回来。
对作者而言,他根本不在乎这个,当他写福尔摩斯故事的时候,收到了《白色同伴》的新书,以及来自出版社第一批的书评。书评颇令人失望,这使他对和福尔摩斯有关的任何人都痛恶起来。
他解释道,并不是因为评论者对《白色同伴》有何恶评,而是他们把它当冒险小说加以赞扬。“然而,我想的是描绘出那个时代真正的人物典型。”他们并没有把它看成是第一本描述英国战争史上最重要的典型:弓箭手的书。这使他十分烦躁。
十二月,他开始着手写《难民》,到圣诞假期,他已写了一百五十页。他放弃了重现麦加·克拉基及迪西莫斯·萨克森这类角色的念头,因为那太理想化了。取而代之的是他把注意力集中到阿莫瑞·戴凯帝纳特——一个凡赛那斯国王卫队的法国新清教徒队长;以及艾莫斯·葛林——一个来自美洲英国属地的伐木者。除此之外,他又着手为艾诺史密斯写一本五万字的短篇小说。
对于《难民》,他之前的满怀热情逐渐减低了。小说不好也不坏。不管怎样,他觉得,由大帝王的宫中掘不到能令人眼睛一亮的好东西,在此情形下,那些对《白色同伴》的评语遂令心情更加沉重。“你知道,”他向母亲解释,“我研究思考已整整一年了,我必须把它写出,我不知道等待对我是否有帮助。在我看来,似乎大部分的评论者并不能分辨作品的好坏。”有时候,他的兴味又会忽然提起,他的脸会开朗起来,迫不及待把他才写的部分念给桃薏及康妮听。
会打扮的妹妹康妮,不以美丽自傲,但是大大的眼睛实在真是漂亮,她现在与他们同住。全欧洲各地都有追求她的人;不止一次她想结婚,只是最后总又作罢。“并不是我要干涉,”她哥哥几次用同样的话告诉她,“如果你爱他,这当然也就是了。不过——他实在没脑筋,亲爱的妹妹。”
康妮打字十分熟练,这是他在南海区买的另一部机器,不过自己从不用。
他希望明年洛蒂也能搬来与他们同住;他现在已有能力供养她们了。英尼斯已十九岁,住在离乌沃威治不远,正在准备进军队。以维多利亚式喜爱大家庭的习惯,他希望一步一步的,可以让大家都住在一起;只除了母亲,她坚持靠他奉养她的钱,自己独居。
于是,手中拿着最新写的一叠《难民》的稿子,他匆匆走进他漂亮的新起居室,房间里面铺着大红花地毯,白色大理石的壁炉架上放着插了装饰草的花瓶。洒落在这些东西上的,是一盏台灯放出的光。这盏台灯的灯罩是那种不容易着火的玻璃罩子,盖在灯油所燃起的火焰上。罩子上还有层打褶的蕾丝花边。
“我的文字,”他写信给洛蒂,告诉她关于路易十四、孟提丝潘夫人和麦坦伦夫人的事,“我的文字,我给了读者值回六先令书价的热情!当我念给康妮及桃薏听时,她们听得坐在那里目瞪口呆。谈到爱情的部分,这简直像火山爆发!”
然后,同样的,当他每次被引入文学世界时,也是如此充满了快乐与激情。他被邀请到《游民》吃饭,在那里遇见了受人喜爱、戴眼镜的杰姆。杰姆是《三人同船》的作者,现在是《游民》的编辑;还有杰姆的助理,脾气急躁的罗伯·巴尔;以及巴瑞,此人所著的《弦音之窗》是柯南十分钦羡的。他们食量惊人,从不去注意戒酒不戒酒的问题,桌上袅袅升起的烟云之中,传来一成不变的歌谣:
因为他是个快乐的好家伙……
这位看起来像卫兵般的医生有着卷曲的胡子,以及硕大的脸庞,由于他的大脸现在已胖成完整的圆形了,使他整个头看起来就像个球,在他身上,他们找到了理想同伴的特质。柯南·道尔笑起来时,他毫不作态,也不保留他的欢乐,他的笑有传染性,常常桌子另一端的人,根本不明所以,也跟着笑了起来。
至于巴瑞——“关于这个人,”他写着,“除了身材以外,没有一样是小的。”——他很容易交上朋友。与杰姆及罗伯·巴尔亦然。巴瑞在诺雾一起吃过饭后不久,便邀请他明年春天去科瑞谬:一个苏格兰的“小小红色之城”,语出巴瑞的《弦音之窗》。
柯南·道尔的《难民》在一八九二年年初正式宣告完成。不管他起初是怎么想的,那些在大森林中探险的景象,绝对写来栩栩如生,并具动态描写的部分极具迫力。它们有凶恶的现实,就像黥脸的印第安人真的就在窗外追踪并宰杀麋鹿一般。这整个故事一直安静低调的往前走,直到书的结局才像突然爆开一阵大笑似的,易洛魁族的印第安战士便是如此悄悄的聚集完成,然后潮水般涌向围栏,接着是碉堡,发动最后的攻击。这是本水平参差的书,然而其中有七个章节可谓精彩绝伦。
作者声称对此书“还算满意”。在谈到美洲市场时,他说了一段饶富深意的话:
“身为一个英国人,如果我能描绘出早期美洲人物的典型,并赢得当地读者的认同,如此我将深以为傲。”他告诉母亲。“经由这些国际关系,不同的国家被连接在一起,而真正能使这两个国家连接在一起,那会是在于世界未来的历史。”这些话,他是在一八九二年一月写的。
再次提起了柯南·道尔对戏剧的兴趣的人是巴瑞,巴瑞当时正忙着制作他第一个剧本——《伦敦,行人》。柯南依他自己的短篇小说《二五年的迷途者》,改编成一出独幕剧,后来定名为《滑铁卢》。
在《滑铁卢》中仅仅出现一个重要角色:现年九十岁的一个上等兵,他曾经有一次驾了一车火药,穿过正在燃烧的树丛,来到衡沟门的卫队。故事开始时他几已全聋,又满口怨言,然而这位老兵葛里格莱·布鲁斯特只要一想到摄政王子曾亲自颁过奖章给他,他浑身的老骨头都会笑开来;而当年轻的炮兵士官前去拜访他时,他更开心极了。
“我是以炮兵营弟兄发言人身份前来拜访,”士官长说,“是要让你知道,先生,我们以与你在同一城镇为荣。”
“这正是摄政王子讲过的话。”开心的老人大声说道。“‘军团以你为
荣,’他说。‘而我以军团为荣,’我说。‘这是个极好的回答。’他说,然后他与喜尔爵士哈哈大笑起来。”
任何认识舞台剧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演员理想中的角色——由拖着步子进场,最终在垂死之时,用尽全身力量大声吼出:“卫兵需要火药,上帝垂怜他们应该得到!”巴瑞打算以此作为开幕词,可是后来他们又决定不用。柯南·道尔鼓足勇气,把剧本寄给他幼时的戏剧偶像亨利·欧文。
欧文的秘书布然·史道克的回信很快就来了,此人又是一个喜好运动与宴饮的爱尔兰人。(顺便一提,在布然·史道克所写的欧文传记中曾提到,唯一使读者不认为福尔摩斯中的华生医生就是布然·史道克的原因,是因为他的戏剧背景。)不管怎样,这位英国戏剧界的泰斗,买下了《滑铁卢》版权;于是它的作者完成了他的另一个愿望。
在他工作的最近几个月里,没有事情打扰他,或者说他根本不在意任何骚扰。小玛莉·路薏丝在他书桌上乱爬,撕破了《难民》的书稿。周末时,人们来拍摄他写作时的照片。说是拍摄他写作,过程可没这么简单:闪光灯不断炮轰着;白烟在响声中弥漫整个房间;而他的笔却不曾停下来。
不过,这里得稍做更正。有一件事的确打扰了他。一封印着《史全德》
杂志抬头的信寄到,要求他开始另一波的连载;他气得大吼,整幢屋子都可以听见。
“他们又来烦我要更多的福尔摩斯小说,”一八九二年二月他告诉母亲。
“在压力之下,我不得不出价一千英镑写十二个故事,可是,我真希望他们不接受。”
但是,他们毫不犹豫就接受了,倒是作者自己面临了抉择。
不管这笔钱今天看来有多微不足道,但是在一八九二年,那是极大的一笔款项。这组小说包括了:《银斑驹》、《瑞盖特村之谜》,以及《海军协约》。有件事使他非常惶惑;他不习惯成为名人,因为他并不觉得自己有何特出之处。
几经考虑之后,他相信他有足够的材料完成这组小说。虽然如此,他还是警告《史全德》,别期望他马上交稿。他已经答应艾诺史密斯一篇拿破仑一世
的故事,八月得交稿,然后,他要与妻子到挪威度假。虽然零零星星的,他可以完成一两篇,但是,大部分的小说得等到年底。
一个大风的早晨,在他书房,心绪仍然有些凌乱,他随意翻着一堆旧纸张(他很少丢弃),并拿出三本厚纸板钉成的草稿本。
也许可以说,《滑铁卢》并非他写的第一出舞台剧。现在他手中拿着的,是一出叫《黑暗中的天使》的三幕剧。头两幕是一八八九年他在南海区时写的,第三幕则在一八九○年完成,当时似乎没有人对福尔摩斯感兴趣。《黑暗中的天使》主要是由《暗红色研究》中的犹他州景象改编,整个故事发生在美国,福尔摩斯根本没出场。不过约翰·华生医生倒亮相了。
对任何一类的评论者而言,《黑暗中的天使》都是充满荆棘。传记作者,至少理论上应该如葛莱格林般严谨,他不应该纵容福尔摩斯!华生式的臆测,这在大西洋两岸都造成争论。可是诱惑的恶魔一直召唤着他。任何看过《黑暗中的天使》的人,都会惊骇的发现,华生生命中许多重要的事,居然不为我们所知。
事实上,华生曾在旧金山行医。他的沉默是可以了解的;他行为不义。那些怀疑华生在女性关系上有着幽暗一面的人,会发现他们可怕的怀疑是真的。
也许在他与玛莉·莫斯坦结婚之前就已经有太太了,要不然就是他毫无良心的抛弃了在《黑暗中的天使》落幕时手臂中挽着的那个可怜的女孩。
那女孩的名字?这正是我们的困难之处。如果给她一个知名的名字,那会出卖了作者和那个角色。从最好方面而言,可以非难华生的婚外情;至于最坏,这会破坏了所有的福尔摩斯小说,而造成一个连贝克街具有最锐利推理智慧的人都无法解决的难题。
柯南·道尔,一八九二年在他诺雾的书房中翻阅着《黑暗中的天使》时,他知道,他必须把这剧本永远束诸高阁。这其中有精彩的片段,有《暗红色研究》没出现的喜剧景象;可是,一出关于华生的剧,其中却没有福尔摩斯,那会把所有人给吓坏了;因此很能被了解的,这个剧本一直到今天都还没出版。
三月里,他与巴瑞及一个“红发、年轻、好运动”的阿瑟·桂勒—考区,一起到黄杨岭拜访乔治·麦芮迪士。这位老先生因为神经痛而步履不稳,
他摇摇摆摆的由小径走来,站在门边以标准的梅迪兹(注:乔治·梅迪兹,一八二八—一九○九,英籍作家)散文体献唱了一曲以为欢迎。他是个有礼且热情的矮小老人,有着一撮灰胡子。他大部分时间谈战争,也讲了一些记忆中马波将军的趣事,这些才刚在英国出版。柯南·道尔虽然兴趣盎然的听着他最喜欢的话题,但是他并不太确定他是否喜欢麦芮迪士。
离开诺雾度了一个短暂的假期之后,他又出发到苏格兰去,中间在爱丁堡停一下,再转往科瑞谬去拜访巴瑞,又到艾伯丁郡的艾福特停留了一星期钓鱼。去了爱丁堡之后:
“我与独脚的勇敢韩利一起吃午餐,一个《金银岛》中约翰·修佛那个角色的真人。他是《国家观察者》杂志的编辑,一位严厉的评论者;而在我心中,他是现存最好的诗人之一。然后我来到科瑞谬,在这里,我发现巴瑞的家庭比韩利还不寻常;可是,我十分开心。”
科瑞谬这个红色的小城有一件神秘的事:依他们这里的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实在不能了解巴瑞怎么能在伦敦那么出名;是的,还有怎么能靠写书赚钱。
这不只令人搞不懂,简直是毫无道理可言。
“这里有些人,”柯南·道尔观察道,“以为巴瑞出名是因为他字写得漂亮。还有人以为他自己印书,然后在伦敦沿街叫卖。他散步时,人们跟着他,或躲在树后窥视,看他是怎么弄出名的。”
那是一个很好笑的不平衡画面:一个非常矮小的苏格兰人,与一个异常高壮的爱尔兰人,庄重的衔着他们的大烟斗散步,整整十五哩的路程中,全神贯注的不停争论。戴着苏格兰帽、留着胡须的脸,一张张的由树后探出来。(现在已出名的巴瑞其实并不抽烟。可是,通常他出现在大众面前时总是衔着烟斗。后来,他成立了一个板球队,每次他上场打击时,就要朋友们帮他照顾他的空烟斗,朋友们都大声抱怨。)
四月,他回到了诺雾,完全专注的写艾诺史密斯的小说,他打算取名为《大阴影》。大阴影是写有关拿破仑的故事;我们听到了拿破仑罗曼史的第一记鼓声响起。他到苏格兰的访问给了他开头几章的背景,全书的高潮在滑铁卢一役达到顶点。可是就像那个独幕剧一样,滑铁卢对他而言,不仅仅是教科书
中的一件事迹,那也是他自己家族历史的一部分,每一套军服、每一顶军帽的颜色都是鲜活的。在那个战场上,他不止一次提到他的祖先。
“有整整五名打过这一仗,”他说,“其中三名就留在那里回不来了。”
在《大阴影》中,最后是一个战争场面,枪炮声盈耳,烟硝味刺鼻,这就像七十一苏格兰高地人军团中杰克·考德和杰米·霍斯克夫经历过的那样。就在那场法国骑兵突然由烟雾中出现进攻的战役中,步兵团撤退了,那种如梦般不真实的情景,任何经历过枪林弹雨的人都会知道。书的开头,潮水冲洗的海边,读者会发现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一人从海里来,有着一抹猫须般的胡子,他自称戴赖朴,他和村民玩着猫捉老鼠的游戏,正如同他的帝国将爪子伸向整个欧陆一样。
仲夏,他完成了《大阴影》之后,终于可以懒懒的坐在他的新草地网球场一端躺椅中,头戴草帽,身穿灯芯绒夹克,好好的做一些评估。
《白色同伴》卖了一版又一版,这证实了他深信不疑的大众好品味。《麦加》也一样。可是,接着(他几乎认为这是“不幸的”)那本纽因斯先生出版的《福尔摩斯办案记》也是一样。这提醒了他,如果新的连载像他们催促得那么急,要在今年十二月出版的话,他得像部没感情的计算机那样加紧工作。
目前他只完成了三篇:《银斑驹》、《硬纸盒探案》和《黄色脸孔》。(我们根据他一八九二年的日记,《黄色脸孔》原名《灰面人》。而《硬纸盒探案》则在纽因斯发行单行本时从《福尔摩斯回忆记》中删除。任何人如果翻阅一八九三年一月份的《史全德》杂志,便可看到那篇福尔摩斯有名的思想观测推理小说,讲到有关亨利·华德·毕切尔和南北战争[现在已改名为《住院病人》]的往事,这篇小说原名就是《纸板箱探案》。除了第一段之外,后来在一八九三年八月《史全德》登载的《住院病人》,开头已完全不一样。)虽然如此,至少还有一篇福尔摩斯的短篇并未登上《史全德》。事实上,再没有任何一篇福尔摩斯小说比这篇被遗忘的小说让华生对福尔摩斯的锐利推理能力更为吃惊的了。
“事实上,亲爱的华生老兄,你是个再好不过的研究对象了。”他
说,“你生活得十分起劲,你对外界的刺激反应很直接。你脑筋运转的速度也许缓慢,但从来不会不被察觉。吃早餐的时候,我发现你比我面前的《泰晤士报》的大标题还容易让我了解。”
在《乡间市集》小说中,福尔摩斯如是说。在所有模仿贝克街这位名侦探的小说中,只有这篇出自柯南·道尔本人手中。他是在四年后为爱丁堡大学的《学生报》写的,目的是帮助大学扩建他们的板球场地而筹资。在此特别一提的是,这只是他所做的许多诸如此类事情中的其中一项。
对于蜂拥到南诺雾访问他的人,他把福尔摩斯的成功归功于裘瑟夫·贝尔医生,他的照片现在被放上书房的壁炉架。贝尔医生慷慨的立刻否认了此事:
“以他神奇的想象力,柯南·道尔医生让微不足道的小事有了大用,而且他还热情地记得他昔日的老师,这使一切变得更加美好。”
“不,不是这样!”他的老学生说。“一点也不!”
如此,为了掩饰他厌烦福尔摩斯这个天大笑话,柯南·道尔严肃的告诉访问他的人,他不写更多的福尔摩斯小说,是因为他怕把这个他十分喜爱的角色给破坏了;而且,他继续开玩笑,决定在以后的小说中,偶然会对那个惹人嫌的角色的真实身份,透露点线索。(毫无疑问,这是指华生,你在这些小说中也注意到此类线索了吗?)
同时,还有另一个重大原因让他十分满意。就是在作者与有名望的出版商联手经过五十年的奋斗之后,美国国会在去年通过了国际版权法案:这给予作者对自己的创作品之法律权利,可以阻止盗版。为什么长久以来,美国一直拒绝加入大英帝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所有其他的文明国家的共同协定,使许多人迷惑不解,也曾使查理士·狄更斯暴怒,甚至当前的美国国会还是对于创作权利有所保留,可是这项法案至少已保证他会增加一大笔收入,这是从他那些值得一读的小说,加上美国读者固执的喜爱福尔摩斯而来。
诺雾的家庭生活过得很平静。康妮终于真正恋爱了,她遇到了一个二十六岁的记者,名叫恩勒斯特·威廉·洪能,小名威利,态度矫健活泼,又能言善道。看他们两人在草地上打网球,康妮的这位老哥十分开心,嫂子桃薏亦然。
康妮的长裙,优雅的随着她接球的动作款摆着,威利则戴着草帽,身着白色的陀螺形法兰绒装。
至于桃薏——哈!他已经不再能和桃薏一起骑双座脚踏车了。另一个孩子将于秋天出世;这次,当然,会是个儿子。以前那些脚踏车长征行径,他现在想来都觉得自己错了。桃薏并不十分健壮,可是却急欲加入他的嗜好,从来不拒绝坐前座,让他踩着脚踏车,与他一同出游。有一次,在骑了三十哩回来之后,他在给洛蒂的信中,痛责自己丝毫没顾虑到而使桃薏疲惫不堪。
不管怎样,桃薏盼望着他们挪威的假期。他们八月去了挪威;九月,当他才再次回诺雾静下心来开始工作时,却意外收到了一封巴瑞来的电报。电报中的急切措辞令他匆匆赶到巴瑞所在的沙佛克的艾得堡;他发现这位《古灯诗》的作者亟须援手。
“你有没有可能,”巴瑞问道,“帮我的轻歌剧剧本一点忙?”
似乎是,巴瑞轻率的答应了为迪欧莱·卡弟写这出歌剧,计划在塞佛的吉伯特-沙利文传统会上演出。它有两幕,巴瑞已经完成第一幕,也草拟出第二幕的大纲,可是,他病倒了,急得不得了。他的朋友能帮他写第二幕的歌词及一些对白吗?
柯南·道尔脱下外衣。不错,他对轻歌剧一窍不通,可是巴瑞需要帮助。
除此之外,他跟自己争辩,一个称职的作家,应该能够写出从科学论文到滑稽歌词的任何东西。
“是关于什么的?”他问巴瑞,“剧情是什么?”
“嗯,背景是牛津或剑桥;我没说明是哪里。布景是一所女子学校。”
“女子学校?”
“是的,一所女子专门学校。剧中的两个英雄,一个是枪骑兵军官,另一个是牛津的大学生,他们进了女子学校的宿舍……”
“噢,老天!”
“不,不,没有任何伤风败俗之事。那个大学生,”巴瑞继续说着,大笑起来,使他的脸开朗了一些,“被他的训导长和两只‘牛头犬’追赶。训练长躲进个老爷钟里,与女教师一起唱双重唱。你先看看我写的。”
就在同一个月,他写了福尔摩斯与《珍·安妮》——或称之为《优良行为之奖赏》——同时,柯南·道尔因为一桩意外之事,写了另一篇与《珍·安妮》完全不同类的诗句。报纸上报道,英国海军曾引以为傲的纳尔逊爵士老旗舰“闪电号”被卖到德国拆解。这真把柯南·道尔给气疯了。
在美国,曾经有一次,对克伦威尔的战舰“老钢号”有同样的建议,这激起了奥立佛·温戴·荷姆写下了那些伤感的词句,开头是:“哎,把她破旧的舰旗扯下——!”同样的,纳尔逊的旗舰也使柯南·道尔深受刺激,在报上,他向着皇家海军顾问们,以极其讽刺的语句,写下了他《谦卑的请愿》:
谁说国家的荷包扁扁,
谁怕所有权或公债或贷款,
当昔日所有的荣耀
被规划成现金资产?
如果时运艰难且百业萧条,
如果煤与棉最后都卖不出去,
我们还有可以交换的东西——
我们光荣的过去。
地下还有一个墓穴躺着
政要或国王的尘土;
还有莎士比亚的家可供出售,
弥尔顿的房子也能提供价钱。
克伦威尔抽出的剑值多少?
爱德华王子的甲冑值多少?
我们萨克森阿佛德王的墓又值多少?
它们全都可以出售!
沉静而理性的人们或许会说,这全是感情用事。一块木头就是一块木头;
生锈的大炮不比等重的废铁值钱。当他们的双眼因死亡而再看不见,当他不能再拯救我们,即使是纳尔逊将军又怎样?柯南·道尔的回答一定是悍然抛出这样的句子:
你们这些唯利是图的人们,
你们难道不知道
有许多金钱买不到的事物?
这是他哲学的一部分。或许这只是小事一桩,可是,这却是未来大事的先兆——那些关乎人类正义之事。也正是这样的性格使然,多年之后,考森·柯南汉说他宁可面对五步之内的枪口,而不愿面对柯南·道尔眼中的怒火或冷嘲热讽。
但一八九二年落幕时,他显然并不在这样的情绪之中。十月中,他最钟爱的妹妹洛蒂,由葡萄牙回国与他们同住,她被拖着四处参观所有的东西。十一月,桃薏的第二个孩子诞生了,正如父亲预期的,是个男孩。
经过一番争论,他们把男孩取名为艾利因·金士力,来自于《白色同伴》中的艾利因·爱瑞克森。每个圣诞节,他们都请邻居的孩子一起欢宴,柯南·道尔医生特别喜欢扮成圣诞老公公。可是这个圣诞节,玛莉·路薏丝及艾利因·金士力的父亲,决定要特别款待孩子们。
为了这个,他花了很多时间想出一套吉柏瓦克类型的服装,那样子恐怖得令每个亲眼见到的人至今记忆犹深。他相信,扮成这副样子,威风凛凛的大步走进来,孩子们一定会觉得开心得不得了。结果,除了婴儿之外,大家全都吓坏了。事后,这位受良心谴责的父亲,几乎整夜陪伴着不停哭泣的玛莉,用各种方式向她保证,那个可怕的怪东西已经被赶跑,不会再回来了。
一八九三年年初,新的福尔摩斯小说开始在《史全德》连载,在写完后面几个故事之后,他带着桃薏去了一趟瑞士,雷清贝瀑布的急湍声,在他们耳中不断隆隆作响。他需要短暂的休息,他因为必须匆匆构思小说情节而宣告筋疲力竭;这种滋味,所有必须在时限之内交稿,又每次得想出新情节的作家全都
了解。如今,他已不再是让人拉线的木偶了,而是个被掐着喉嘴的巨大脑子。
在家乡,他们要求他巡回演讲,他对此极感兴趣。写剧本也使他兴头;欧文不久将演出《滑铁卢》,轻歌剧《珍·安妮》也在春天彩排。对演讲和剧院,他两者都十分喜爱。
可是,在那之前,他还有一项工作。一八九三年四月六日,在诺雾——他坐书房的火炉边,患了感冒,无聊的翻着《傲慢与偏见》,一堆油漆匠正在屋外敲敲打打——他放下书本,给母亲写信。
“这里一切都好,”他说,“我正在写最后一个福尔摩斯的故事,在这之后,这位先生将消失了,永远不再回来了!我厌倦了这个名字。”于是,莫拉提教授等在黑岩石旁;雷清贝瀑布的情节展开了;接着,轻松愉快的叹了一口气,他把福尔摩斯给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