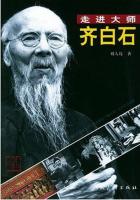1969年12月26日到达下放目的地,这个日子像刻在脑子里。
广西到处是山,北方人常说“开门见山”而在我们住地,不用开门从窗户就能看见山。
广西可以说没有明显的四季,热得时间很长而且气温很高,夏季进伏后有时赶上整月的“南风天”阴天多雨,潮湿的墙上流水,一出太阳就是上班时间也允许晒被、晒衣服。当地也多吃辣椒防风湿。每天离不开洗澡,当地叫“洗凉”。各单位都有洗凉房。
广西农村到处是蛇,有毒蛇也有草花蛇,挺吓人的,人们走远路,手里总拿着树枝、竹竿一类的棍棒。人未到先“打草”,目的是为了“惊蛇”。患者中也经常有被蛇咬伤的。
广西的蚊子又多又凶,一年四季离不开蚊帐,蚊子的个头特别大,有人开玩笑说“系上线能当蜻蜓玩”。好容易熬到白天蚊子歇了,墨蚊又来了,而且是成群结队,比小米粒还小,一巴掌打下去,十几个小血点。晚上蚊子,白天墨蚊我们给它起个外号叫“两班倒”!
以上介绍的情况都是对工作开展的不利因素。广西农村的医疗工作重点在两个季节,一就“春插”(清明节前完成水稻插秧);二是“双抢”(收头苗稻子,种二苗稻子,合起来叫做抢种抢收),这个时候,要送医送药到田间地头,还要适当的参加劳动,水田里经常遇到蚂蟥(水蛭)吸血,因为它有吸盘,打都打不掉。同时它吸血时吐出水蛭素能抗凝血,所以伤口流血时间相对要长。虽然没有什么后遗症,但从城市来的人总有些畏惧心理。叮在腿上不下来,真腻味人!
当然广西农村居民生活中最辛苦的是爬山过坳。广西山连山、山套山,岂止十万大山?这样的地形不可能有成片的耕地,全是在山之间开垦的小块地,农民住在附近形成村庄。因此以公社(乡)到大队、生产队,偶尔有些小路能踩单车(骑自行车)到村里,绝大部分全靠步行,山高坡陡道路崎岖,有的大队翻过一座山要两个小时,也就是说,医疗队员背着药箱、器械,不停地爬到山顶至少要一个小时。山顶上有风,凉快,喝水休息会儿,再往下爬。这也不说是对意志体力和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思想的真实考验。有了这样的实践,才能理解村里的重病人,用担架需五六个人轮换抬到公社卫生院很是辛苦,所以医务人员不分昼夜竭尽全力地抢救病人。如果不下乡,这种医患的亲密感情是不容易建立起来的。
山区农村环境卫生很差,苍蝇、蚊子多,靠天然泉水,饮用水和洗东西都在一起。粪便管理更谈不上,还有些村户“人畜混居”(上面住人楼板下面养牛)煮饭(冬天取暖)全部烧柴(树木),墙都熏黑了。
语言不通也给工作带来障碍。当地全部讲“壮语”。
整个公社没有电,靠有线广播,电话是先摇几圈然后通过总机联络。打长途要到公社邮电所,想与县以外联系,双方对话要靠当地话务员传达。
文化生活更谈不上,家信最快半个月,报纸只能看五六天以前的。一两个月演一次露天电影(县电影放映队)这些年没超过五个片子。即《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奇袭》、《铁道卫士》。银幕上演什么,底下观众说着“台词”,连农村的孩子都背得很熟。
我们也入乡随俗,一日吃两餐,米饭、青菜或南瓜,为什么这样节省首先每月要给婆家、娘家寄去孩子的生活费,平时多多少少积攒些路费,那时候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还不足一百元。
穿戴上除了下乡走山路废鞋必须随时添置以外,不买任何服装,本来从要求上生活要朴素,另外,收支平衡后所剩无几,也只能勤俭朴素,在计划收支时甚至计算包括每人每月值几次夜班,因为值一次夜班有两角钱夜餐费。
胖子经常下大队,下生产队,用心学习壮语,不到一年他能用壮话问病史、写病历、解释病情、讲清治疗方法。例如,一般一岁上下的壮族儿童不习惯穿衣服,都是用壮家自己织的土布,再用蓝靛(一种野生的花草)染成蓝黑色,往孩子身上一围,用线绳一捆,再用背脊往身上一背,不论是走山路,干农活,甚至挑柴火都不耽误。男人和妇女一样背孩子。(这一类北方少见。)
就是小孩看病,也要问清男孩女孩。每当这时总要请当地医生翻译,于是胖子下功夫苦学苦练壮语,一次给婴儿看病,胖子竟大胆地指着孩子问妈妈:“拉普赛(男孩),拉麦博(女孩)?”妇女回答:“拉麦博”。话音未落孩子的妈妈惊奇地笑了,在场的一位壮族男青年对同伴说:“呆亦翱刚撞了!”(他也晓得讲壮语了)壮胞的兴奋是对胖子的最大鼓励,他觉得方向对了,发音对了,更重要的是他感到医患距离更近了。天津医生讲壮语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到生产队、大队、公社甚至县里……胖子的嗓子不错,我至今还记得他说“拉麦博”那个“博”字,是个短爆破音,又准确又好听。后来被任命为院长下乡的机会更多。在大队除治病外,还要培训赤脚医生,宣传预防老年慢性气管炎,普查钩虫病,丝虫病,钩端螺旋体病和督促“二管五改”等。他向当地草医学习,辨认多种当地草药并掌握治疗的疾病和方法。经常采回一些比较珍贵的药草如:半枝莲、半边莲、白花蛇舌草、小田基黄等等。他背诵的草药,药性赋我还记着两句:“方茎中空善治气,有毛有刺力更雄……”
胖子下乡,我一个人在家除上班、值班外,经常控制不住想家。特别是惦记着孩子。看书看报也常常走神儿,特别是晚上太静又没有电,不时传来狗叫声,很难入睡,从梦中哭醒的事,时有发生。生活上也不像以前那样规律,总觉得一个人的饭省事,又懒得做,有时吃一个玉米就当了饭。
不久,我开始感到不想吃饭,恶心腹胀,全身无力,然后发烧不退,整天输液服药。胖子正下大队我没有告诉他。一周后不见好转而且精神很差,医院在晚上八点钟给大队打电话,让胖子急速回院。为了安全大队党支部书记考虑三十里山路不放心派一个基干民兵背着步枪护送他。从晚九点靠月光和手电筒,顾不得深一脚,浅一脚走到家,整是晚上十二点。等回家一看他大吃一惊,人极度消瘦,两眼窝深陷,发黑(像熊猫的眼)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
经多方检查确诊为:急性传染性肝炎。我只好在家里隔离休养,胖子一边上班一边服侍我,好在住地就在医院不远。他每天不停地劝、说、讲今比古,这些大道理当时明白极了,可是一想到老人、孩子,嘴唇一哆嗦眼泪就下来,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这次重病为了不给家人添心思,婆家、娘家人都没告诉。
病后二十多天我已经能下地了,一下地就嫌屋里乱,胖子劝我说当前重中之重是我的身体。我当着他点头,他上班去我还是偷偷的搞卫生整理。只要我能动就不允许家里不像样。
中午胖子兴冲冲地跑回来说:“公社邮电所打来电话,让去取邮包!”这消息十分突然,在这以前,家信中没提到过寄包裹的事儿。我让胖子带图章马上去取,心里还是盘算邮包里是什么呢?
胖子回来了,两手抱着一个大盒子。盒子外面是用旧背心缝的一个套,上面写着收件人地址、姓名。这字体太熟悉,“是我爸寄来的!”激动得我喊出了声。我问胖子“邮包怎么还用木头盒子包装。”胖子也说:“可能是怕碰的东西。”
我从小急性子,找来剪刀剪去缝线,露出了一个大木盒,钉的真结实,木盒足有一尺半长宽,高不少于八九寸。越快要打开时心里越紧张越感觉是个谜团。用改锥小心翼翼地撬开后。啊!一股小磨香油味扑鼻而来,是满满一盒子各式各样的桂顺斋的小八件,油纸的侧面还有“字号签儿”。这时医院的会计送来一封信,说就在报纸里夹着的。我接过来看是爸爸的信,我明白了爸爸遵守邮局制度,邮包内不许带信。
信是这样写的:
景雯宝明:见字如握
前接来信知你们都好很忙。家中都平安勿念。我不住在单位,放心。近接上级通知,咱家属于“战备疏散”对象。和你们一样“四带”到天津南郊区北闸口村落户。咱一定服从命令。正准备搬迁。考虑到以后不像住在市里方便,我在桂顺斋挑了各式各样新鲜点心五斤,根据邮局的规定,我亲自钉了个木盒子做包装用。虽然邮资贵了点,想到你们接到后的高兴情形,值。近期不要给家里来信,等我的信,按新地址再给我写信。东东可爱不必惦念。
马三立
70年5月10日
信还没读完,已经被滴落的泪水浸湿了一片。心里真是百感交集。想到爸爸妈妈,天津的亲人,太疼我们了,他们怎么会知道我重病方愈就送来营养品呢?难道真是心灵的感应!爸爸太舍得花钱了,虽然当时五斤点心到不了四块钱,可是花了十九块多钱的邮资,加在一起超过了我的半个月工资呀!想到全家被“疏散”落户到郊区,虽然不太远,但家庭成员的工作生活发生这么大变化能承受吗?我问胖子怎么会全家到农村去呢?胖子擦干眼泪对我说:“别哭了,你刚好点儿,千万注意不能再反复,运动当中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只要全家平安,以后还不知道怎么变化了。”
两个人长时间望着保持完好,五颜六色,样式各异的新鲜点心,一股暖流在全身回荡。我们手捧桂顺斋点心热泪滚呀。也许在两千多名下放广西的医务人员中,我是为数不多的收到从家乡邮寄来糕点的人。我满足,我骄傲!
我和胖子在广西下放了十年零四个月。其间曾几次回津探亲,所有的时间都守护在老人和孩子身边。在南郊北闸口家中,了解了大家的工作、生活情况。看到了我的女儿东东,又在姥爷的腿上翻跃,像是接了我的“班”。天津美术学院著名画家王麦秆先生夫妇和孩子王德成先生都下放到北闸口,德成一定要给胖子画像,十分认真一动不动地画了两小时,胖子表示感谢。爸爸心疼地问胖子:“累了吧?”又诙谐地说:“以后要不听话,就找德成给你画像!”
十年间我们没有在双方老人面前尽孝,具体说是爷爷、奶奶、二姑、二姑父和其他姑姑、姑父、大伯、大妈抚养照顾了扬扬;是姥姥、姥爷、各位姨、姨夫、舅舅、舅母关心培养了东东。这些年我们走了送,来了接,感情上的关怀,经济上的援助。我和胖子没齿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