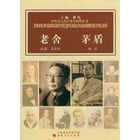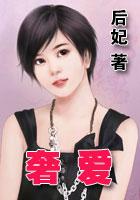1949年1月14日下午,天津市。
天,阴沉、昏暗、低垂。一阵紧似一阵的西北风旋起大量的沙尘漫天弥散,这风声就像一群野狼轮流地拉着长声嚎叫,听起来瘆人。天冷,地都冻得裂开了缝。光秃秃的树枝上看不到一点儿绿色也找不着一只鸟。从天到地全凝固了似的,没有一点生气和希望。
远处传来稀疏的隆隆炮声。住家的门是不轻易开的,有的甚至在大门外面砌了防护墙只留小门出入。商店大部分不开门,个别的早晨开会儿午后也早早关上了,怕抢!只有烟囱楼子敞着小窗户,点烟用的盘香摆在铁丝做的架子上像个小宝塔。香极慢地燃烧着,几乎看不到香头上的“红火儿”。好半天才晃晃悠悠有气无力地冒出一缕青烟,马上又被风吹散化为乌有。这香火已是弱不禁风摇摇欲坠了。隐隐传来卖烟小孩的吆喝声:“金枪牌烟卷儿三根两毛钱儿。”那时候穷人家连整盒烟卷儿都买不起,只能论根。
街上行人不多,但个个表情严肃。目光警觉,很少驻足交谈,各怀心事疾步快走,真像是暴风雨前出来寻食的蚂蚁,达到目的就迅速返回自己的窝里躲起来。偶尔有一两辆“胶皮”(人力车)匆匆而过,拉车人头上冒着热气。明知跑着拉车累还是要跑,一为多赚点钱二为取暖。
荷枪实弹的军警好像斗败的鹌鹑无精打采,耷拉着脑袋缩着脖子三五成群地调来调去,嘴里还骂骂咧咧,使得街市上的气氛紧张无序,呈现一片萧条凄凉的景象。
我们家住在南市福安街九成里2号,房后不远就是广播电台。在前院的一间平房里住着七口人:三爷爷、妈妈、我和两个姐姐、两个弟弟。屋子里没有像样的家具,不知道为什么把原来的炕也拆了,更显得空荡荡的。在对着门的墙角处铺着一溜儿厚厚的稻草,上面有被和褥子,这就是“地铺”。老年多病的三爷躺在一边一动不动。妈妈和大姐在地铺上面用箱子、砖、木板又搭成一个小屋,还拿棉被当作帘子。刚搭好时我就领着弟弟出出进进还没完没了地问妈妈:“搭这小屋干吗呀?啊?”妈妈缠不过我就小声地说:“要打仗了。”后来才懂得小屋是为了挡枪子儿。那年我不到八岁、大姐十三岁、二姐十岁、大弟四岁、二弟才两岁。
严寒的冬季昼短夜长,加上阴天五点钟就黑了。饭后,弟弟们都睡了,妈妈在煤油灯下缝衣服,脸沉沉地一句话也不说。大姐皱着眉头在支炉儿上赶碌着烙饼,随时把放凉的饼装进面口袋里。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心想这得几天吃完?明明是白面裹着棒子面,可大人们非叫它金裹银(鱼儿)饼,不明白。
风更大了,刮得窗户呱嗒呱嗒地响,我睡不着蒙着棉被在小屋里,来回数着家里的人。爸爸这些天总没在家,我忍不住问妈妈:“爸爸上哪儿去了,怎么还不回来。”妈妈没有回答。不懂事的我硬是推着妈妈的腿不停地问。妈妈是世界上脾气最好的妈妈,她忍着心烦对我说:“你爸爸在北平(北京)啦,还不知道他怎么样了。”我看了看妈妈不再问了,敢情妈妈也在想爸爸。
屋里院里街上都安静极了,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一阵清脆的枪声打破了沉寂,紧接着枪炮声连成一片。妈妈急忙放下针线,用木棍顶好门,吹灭油灯爬进小屋抱紧弟弟,我们姐儿仨也搂紧妈妈一动不动甚至不敢大声喘气。黑暗中我看见妈妈睁大眼睛盯着周围,侧着耳朵分辨声音,似乎做好了各种准备。
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轰隆”一声巨响,整个房子都在摇晃,后房山像是被什么推得颤巍了一下幸亏没倒,一家人抱得更紧了。恐惧笼罩着大地,更折磨人们的心灵,就这样胆战心惊地等着、等着,不知道还会有什么灾难降临。后来才听说我们门口巷战特别激烈,因为电台是“兵家必争之地”。那声巨响是一颗炮弹落在我家附近,房子炸坍了,一家人伤亡惨重。这炮弹离我家才咫尺之间呀,童年的我就领略了战争的残酷。
第二天,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了!紧接着北京也和平解放了!不久,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屋门开了,急匆匆走进一个人,我一眼就认出是爸爸。
爸爸更瘦了,眼窝深陷神情疲惫,呼吸都有些急促。他先是注视着妈妈,然后是三爷和我们姐弟,最后目光又落在妈妈脸上。那目光中充满平安重逢的兴奋和骨肉团聚的欣慰。此刻他的喉咙哽咽了好像在说:“兵荒马乱我把一家老小都留给你,你是怎么熬过来的?你可受苦了。”妈妈的眼睛模糊了,这个坚强的女性,不曾被贫穷、饥饿、疲劳、疾病、战乱和恐怖所屈服,却禁不住丈夫钦佩、慰藉、真挚、深情的目光。劫后余生亲人重逢刹那间使她百感交集异常激动,连身体都有些颤抖。然而她很快的收敛了泪水,尽量使自己恢复到平日的安稳恬静,用眼睛告诉爸爸:“什么都不用说了,你平安回来就好!”
窗外风雪已停,皎洁的月光照在屋顶、地面的皑皑白雪映得大地变得晶莹明亮,人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新世界。屋内大家把爸爸围在中间说着自己想说的话。今晚炉火格外暖和,对于这家人来说又一次迎来了自己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