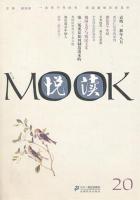想起李白,想起杜甫,想起古老的大师,我又怎能克制住内心的膜拜?
在我的视力无法抵达的时空,蒹葭苍苍,这史书记载中最原始的植物,简直是为一群人而生长的。他们布衣草履,贴着水面行走,歌哭歌笑,放浪形骸,在荒芜中显示出精神的繁荣。《诗经》与汉乐府,民间的神曲,挽留了一批无名的大师和朴素的艺人。
然后就是巨人的时代。重温我们民族文化的历史,无异于翻阅一部东方版的巨人传。在露天的殿堂,在高耸入云的阶梯教室,瞻仰那一张张闪烁于时间深处的面孔,不得不感叹,他们是文明的诸神。人类需要这样的歌者。
先秦诸子、竹林七贤、初唐四杰、唐宋八大家……蓬莱文章建安骨,江山代有才人出。在山之巅,在水之湄,在汉字与岩石的夹缝,这是怎样一个无限繁衍的群体。黑暗中的乐队,数目不详,却准确地在岁月的唇边高擎起千万朵金黄的喇叭花。他们衣袂飘然的身影,从地平线上出现了,又消失了,只留下了声音。即使是这个人化的呐喊,在我们今天充满喧嚣和躁动的生活中,也带有格言的魅力,穿透钢筋水泥的屏障。这历经锻炼、百试不爽的犀利哟!
看见蝴蝶我想起庄子,舞姿翩跹。看见月亮我想起李白,对影成三人。陶渊明是时间深处的隐士,采菊东篱下——更确切地说他代表一种生活方式。而去赤壁则怀念苏轼——灵魂俨然,有故地重游之感。想起古老的大师,曾经为战乱、贫困、厄运重重阻挠,却依然留下美丽空灵的文字,我承认自己是雕花走廊外迟到的书童。生者与亡者,仅仅一纸之隔。愿我的阅读或朗诵,能给他们以慰籍。
长安米贵,洛阳纸贵。和苦难的大师们相比,遗憾的是我们生存在一个文化贬值的时代——被风花雪月疲软了骨气,被流行歌曲、天皇巨星或颓废摇滚、盗版书刊等磨钝了听觉。或许我们更为不幸。大师们的思想,春风吹又生,依然新鲜。现代人的灵魂,却在物质的牛角抵触而折旧了,伤痕累累,破绽百出。
齿轮没有记忆。工业社会产生不了真正的牧歌。再发达的电脑,也创造不出神话般的灵感。精神家园杂草丛生、地址不详。在荒凉的时刻,从蒙满灰尘的书架上取下古代圣贤的经卷,字里行间的呼吸滚烫炙手,我又恢复了清洁的宗旨,并且惊讶:大师们在那原始的年代,居然诞生了如此进步的思想——它们甚至是刻在竹简或印在毛边纸上的。我们的物质与精神,究竟哪些在倒退呢?或那些在进化?
他们的名字,构成我内心的星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大师们生活过的。所以我热爱这个世界。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文学,曾经表达过他们的思想——只要这么想一想,我就加倍地热爱自己的母语。古老的大师,我遵循你们的语法,而触摸到古典的中国。
我们民族众多的节日中,至少有一个节日,专门用来纪念一位古老大师的。那简直堪称文化的节日。龙舟与粽子的祭奠,延续了整整两千多年。哦,屈原,两千多岁的大师。欧洲产生过荷马,而东方的第一位大诗人则是屈原——世界的天平终于平衡了。我无意对楚辞与荷马史诗进行比较,屈原早已被公认为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台湾的余光中先生说过:“我蓝墨水的上游是汩罗江。”地图上的这条河流,中国历史上的这条河流,是因为一位大师将其作为归宿而出名的。
秦时明月汉时关,葡萄美酒夜光杯。王国维的辫子,给古典主义的王朝打了一个死结。作为二十一世纪初的青少年,当众人皆醉,绅士淑女们忙碌于追款傍腕,争风吃醋,追逐巴黎香水、名牌时装、别墅豪宅和香车宝马时,我为什么对古老的大师念念不忘呢?
我们生活在今天,这不是一个产生巨匠时代。在这个时代巨匠也会寂寞的。他们鬼斧神工的风景,快要被拜金主义的推土机排挤到镜头之外。但我们仍然需要保留这样浑厚卓越的画外音。大师们创造的奇迹,哪怕是文明的碎片,也补贴得了理想的创伤。
到了该告别苍白的时候了。
所以,在灯红酒绿的都市里,我开始怀念那些遥远的人物和遥远的事迹。或许,它能给疏忘与蒙昧提供以古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