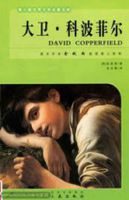“没见谁是憋死的。”贱舌子说。
不远处,一只手分开树枝,露出两张脸。
“他们在烤兔子。”河下一郎说。
“烤野兔子一定很香,咪西……”古贺董咽下口水,在亮子里街头,小贩卖一种熏兔头,他吃过一次。
“哪呢!”河下一郎斥责道。
古贺董立刻哑口,还是忍不住说:“他们放不放辣椒?”
“你说什么?”
“山民烤兔子要是放辣椒,味道更鲜美。”古贺董说。
“只可惜,他们吃不到了。”
“你要杀掉他们?”古贺董平淡地问。
贱舌子木把翻动即将烤好的兔子,黄白净子脸木把往一个木墩上摆碗筷,准备吃饭。对于留守在木营地的两个木把来说,这是生命中最后的晚宴,杀手离开树棵子,借着高高的木楞垛掩护,接近两个木把。
熏兔子味道更浓,古贺董一脚掉进暗水漏子(土层下的水坑),脏了鞋子,刚要脱下擦拭,河下一郎说:“你饶到他们的后面去,用刀,别用枪。”
古贺董向另一方向猫腰跑去,河下一郎原地不动盯着两个木把。古贺董很快绕到两个木把后面,向河下一郎打手势。
河下一郎用手势发出了动手的命令,同时一跃而起,他俩从两个方向恶虎捕食一样扑过去。
两个木把几乎没怎么挣扎,给扳倒、弄死,河下一郎瞟眼两具横躺地上的尸体,轻蔑道:
“黑头糜子!”
古贺董从架子上摘下野兔,这是飞来的口福。
“报告司令,人带来啦。”军官带一个叫郝秀才的人进来,自从司令部贴出招一名会写会画的秘书告示,先后有四人前来应聘,司令都没看上,这是第五个应聘者。
洪光宗摆下手,军官退出去。郝秀才有些紧张,怯生生的不敢正眼看洪光宗。
“你是郝秀才?”洪光宗问。
“鄙人姓郝。”郝秀才回答,“名秀才。”
“唔,秀才。听说你是一个写匠。”洪光宗听环儿说过他。
“能写几个字。”
洪光宗指着桌子上的纸笔道:“那你写写。”
“不知司令叫我写什么?”郝秀才问。
“愿意写什么,写什么。”
郝秀才沉吟片刻,大笔一挥,龙飞凤舞。写罢,拿给洪光宗看。
“倒笔邪神,果真厉害。”洪光宗阅读,欣悦道,“不过,你把我说得像朵花似的,我哪有什么雄才大(略),小把戏。郝秀才,我看你真有两把刷子,本司令身边缺你这样耍笔杆的人,你给我当秘书吧!”
“谢谢司令,”郝秀才谦虚道,“我是一个穷酸秀才,半瓶子醋……”
“别老头过河——牵(谦)须(虚)过度(渡)。先给你出道题,答不上,我真不能用你。”洪光宗说。
“我试试。”
“别人求我办事,送钱送物,也有送人的。搁你,送什么?”
“为达到目的?”
“定然。”
“给你半张纸。”郝秀才略作思考答道。
“哈,哈!”洪光宗笑道,“金纸银纸啊,才给半张,那么金贵?”
“普通纸,连宣纸都不是。”
“你也太抠搜,连送纸都只给半张。”洪光宗说。
“这是秀才送的礼啊。”
“有什么讲究吗?”
“常言道,秀才人情纸半张。”
“咋说,也是抠门儿。”
“虽说官不打送礼的,可是也要看给什么人送礼。有人喜欢金条,有人喜欢捧臭脚……可司令您,生性耿直,吹吹拍拍的人您一定不喜欢;您疏财仗义,对金钱也不喜欢。可您却爱才,选秘书看什么,他能说能写能画,所以我才扯半张纸,写上心里话,把我这一堆儿一块儿原封原样撂在司令面前,喜欢不喜欢,司令定夺。”郝秀才说。
“你是我的副官秘书了。”洪光宗说。
“谢司令提挈。”郝秀才感谢道。
“互相提鞋(挈)吧!”洪光宗说。
“司令,”黄笑天进来,凑近洪光宗耳边说,“郑记米行和马具店,昨夜给胡子抢了。”
“姥姥个粪兜子的,哪个吃豹子胆的绺子。”洪光宗骂道。
“划满洲。”
“又是这个划满洲,蹬鼻子上脸嘛!把刁团长给我叫来。”
“是。”黄笑天应声刚要走,被洪光宗又叫住,说,“不用啦,我们一起去校军场。笑天,这是我刚招的秘书郝秀才,你先带去换换行头。”
巡防军校军场的操场上,士兵正操练,刁团长和几个军官站在点将台上。一个军官快步跑上台,对刁团长说些什么。
“走!迎接司令去!”刁团长整理一下风纪,跑步下台去。
侍卫、副官拥着洪光宗走过来,刁团长等人敬礼,洪光宗还礼。
“报告,部队正操练,请司令校阅。”刁团长道。
“唔,继续操练!”洪光宗说。
刁团长请洪光宗登上点将台,台下,士兵仍在操练,洪光宗露出满意的笑容。
“请司令训导。”刁团长说。
“啊,啊,今天不讲了,我是来找你。”洪光宗说,“刁团长,你带上人马,把马家窑给我平喽。”
“马家窑早是一个废村,平它做什么?”刁团长不解地问。
“村子是废了,可藏着胡子,划满洲压(住)在哪儿。”洪光宗说。
马家窑若干年前生气勃勃的一个村子,徐将军在这里和老头好绺子进行一场恶战,近百户民房给枪弹打着火,活捉的胡子大柜老头好,吊在村头的井挑杆上,用胡子的酷刑穿花——扒光衣服,让瞎虻、小咬、蚊子吸干血——处死他,那个后来叫雨蝶的女孩,在草丛中目睹父亲老头好给巡防军残害致死。从此,马家窑成为残垣断壁废弃的村子,十分荒凉。
最近,划满洲绺子来此地趴风(躲藏),修复了一个地主的土大院里做匪巢。
划满洲同二柜盘腿坐在炕上,炕桌子上摆着茶壶,两人喝茶,抢劫成功的兴奋劲儿尚未过来。
“真是痛快啊,大哥,今年冬天弟兄们的棉衣不愁了,高脚子(马)鞍具也够用上几年。”二柜说。
“咱们也别只顾乐,得精神点儿,”划满洲喝口水说,“损失东西的店铺老板心疼胆疼,肯定要报案。”
“陶知事手下卫队那几头烂蒜,抽大烟扎吗啡,还怕他牙长咬了我们的脚后跟。”
“不是还有巡防军吗,惊动他们对咱们不利。”
“大哥过虑了,巡防军管辖数个三江这样的县,虮子大的小县官洪光宗能放在眼里边?俄国人、日本人他都不屌(理),何况陶知事。”
“兔子不吃窝边草。二弟,兔子为啥不吃窝边草?”
“留着青黄不接时吃啊。”二柜不假思索道。
“胡嘞嘞,兔子不吃窝边的草,为了遮挡自己,防鹰……”划满洲斥打他一句,然后道,“按理说巡防军不会理睬店铺给谁抢去几袋米的鸡毛蒜皮小事,可是有人向巡防军求援就不同了。洪光宗不会坐视不管,亮子里毕竟是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发生店铺遭劫,他没面子。司令发起火来不得了,他一打喷嚏,三江方圆几百里都伤风。”
“大哥的意思是?”
“挪窑(换地方),马家窑不安全。”划满洲说。
“我立马去安排。”
“不,白天明晃晃,挪窑目标太大易暴露,掐灯花(晚上)时行动。”
夜色带着几分诡秘包裹住马家窑,周遭漆黑一团。
刁团长带部队悄然包围了马家窑屯子,他一脚踩空摔倒,一个士兵急忙扶起他:“团长。”
“妈的,吓我一跳。”刁团长道。
匪巢里,划满洲下令道:“鞴联子!(鞴马)”院内集结待命的土匪行动起来。
“上马!”划满洲再次发出指令道,他不知道自己逃不出去,巡防军把他们团团包围。
土匪纷纷上马。
“弟兄们,风紧拉花(事急速逃)!”划满洲说,“麻溜影(跑)!”
刁团长果断命令道:“狠狠打,别让一个胡子漏网!”
士兵向土匪马队射击。
“开边(打)!”划满洲举枪高喊道。
司令部的书房里上了灯,洪光宗半仰在椅子上,听念书。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郝秀才捧着一本书只差没摇头晃脑,不然与私塾先生无二。
“报告司令,刁团长求见。”黄笑天进来说。
“噢,”洪光宗忽然坐起身子,他等着刁团长清剿胡子的消息,“他们出师怎么样?”
“刁团长说,生擒了划满洲。”黄笑天眉飞色舞,说划满洲绺子不堪一击,没多大工夫就被俘获,羁押在军营里。
洪光宗、刁团长、黄笑天等人进院,几十个土匪捆绑着,由武装士兵看押。
“谁是划满洲?”洪光宗问。
“我是划满洲。”划满洲从土匪堆里站出来,毫无惧色道。
“嚄,是你。”洪光宗走近一步道,“你知道我今天要把你怎么样吗?”
划满洲几分凛然道:“能怎么样,大不了是个死。”
“你不怕死?”洪光宗问。
“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划满洲匪气十足道。
“算你有种!我只问你,你服不服?”洪光宗问。
“哈哈,服你?”划满洲大笑说,“其实你比我高不哪儿去,还不是点儿高,运气好,拣驴镫套脚上。”
“照你的说法,我这个司令不过是拣来的。你看这天下有一下拣几千兵马的吗?”洪光宗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