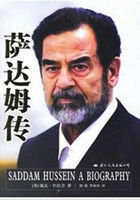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将失去劳动能力,再老一些,他们还可能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因此,老年人需要年轻人的赡养。这赡养可以来自社会,也可以来自老人的子女。在中国,不论城市还是乡村,主导的赡养方式还是家庭赡养。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是法律(包括《婚姻法》和《老年人权益保护法》)规定了的。但是,中国农村和城市对老人赡养的方式还是有所区别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第十一条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顾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根据此法律条文,对老年人的赡养义务分为“经济赡养”、“服务赡养”和“精神赡养”三种方式。正是赡养方式的不同,使中国城市和农村的赡养特点区别开来。在城市里,大多数的老人都有退休金和医疗保障,因此,留给子女的赡养义务就仅仅剩下了“服务赡养”和“精神赡养”。而在我国农村,子女对老人的赡养则是全方位的。农村中的子女不仅要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且还要承担老人的生活费用和医疗费用。由于中国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短期内不可能建立起来,中国农村以家庭为主的赡养方式,在可预见的将来,还会持续下去。
在中国的传统价值中,“孝”是处于核心地位的价值。“养儿防老”是平安村村民普遍持有的看法。对村民来说,对父母的“生养死葬”是做儿子天经地义的责任。因此,赡养老人的义务不仅仅是法律的规定,这义务还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但是经验告诉我们,文化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往往有很大的距离。在中国的历史文献、文艺作品和民间传说中,孝的故事和不孝的故事都不绝于耳。在平安村,村民们最常引用的故事就是《墙头记》,如果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人们往往就会和他开玩笑说,“你迟早还不是唱‘墙头记”’。平安村的老年人赡养状况如何呢?老年人赡养和财产继承的关系是什么样的?本章将重点讨论这一问题。我们首先来考察平安村对老年人的赡养方式。
平安村的赡养方式和文献报道中其他地方的赡养方式是相似的。最基本的赡养原则是儿子们平均分担对父母的赡养义务,这是和他们平均地继承父母的财产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必须分阶段叙述赡养的方式和特点。在上一章已经提到,目前平安村分家的时间普遍提前,因此在儿子们分家的时候,父母往往还比较年轻,身体健康,大多还有很强的劳动能力,有些父母甚至比他们的子女挣的钱还多,还要从经济上资助儿子。在这一阶段,父母往往独立生活,独立起灶吃饭。即使他们已经不再劳动,也仅仅需要儿子给付生活费,以及生病时的医药费。儿子们在这一阶段的责任是分担老人的生活费和医药费。虽然老人们独立生活,但他们需要轮流住在各个儿子家。这种做法也适用于独子的家庭,只不过如果只有一个儿子的话,老人不需要经常搬家。一个儿子的情况下也有父子合灶的现象,但是如果老人还有收人,则经济收入上往往是分开的,而且往往是老人承担共同生活的费用,如饮食、燃料、水电费等。也有父子两代人达成某种默契,分别承担某一项或几项费用。
当父母进入暮年时,或者其中一方亡故后,如果只有一个儿子,两个日常生活单位往往会合并。如果有多个儿子,赡养就进入了“轮养”的阶段。根据和儿子们商定的期限,老人轮流吃住在各个儿子家,但医药费仍是几个儿子分摊。文献中对于“轮养”的研究很多,在大多数文献中被称为“轮伙头”或“吃伙头”(谢继昌,1985;Cohen,1992;陈运飘等,1997;李亦园,2002)。从学者的研究结果来看,这是在中国被广泛实行的老人赡养方式。本书将使用“轮养”的术语。无论是“轮伙头”还是“吃伙头”,都仅仅包含了轮流吃饭的意思,而儿子对年老父母的轮流赡养其实不仅仅是“轮吃”,还有“轮住”和“轮流照顾”的内容,因此使用“轮养”的说法更加符合老人赡养的实际情况。
在平安村对老人的赡养除了“轮养”的方式以外,还有一种方式是几个儿子(通常是两个)分为两组,每一组分别赡养父母之中的一个,我把这种方式叫做“分养”。其他学者也已观察到了这种赡养方式,如王崧兴把舟山岛渔民的老人赡养方式分为了五种,其中之一就是“年老父母分开,各归一个儿子扶养”(王崧兴,1986)。费孝通也在江村观察到,“有7户在儿子分家时,老夫妇分别住在两个儿子家里”(费孝通,1983)。在平安村我发现有两户人家采取了这样的赡养方式。关于“分养”稍后再讨论,现在首先讨论“轮养”。
在有多个儿子的情况下,“轮养”是一种最常见的赡养方式,甚至可以说是常规的赡养方式。轮养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轮吃”,二是“轮住”。上文已经说到,“轮住”是比“轮吃”更早开始的过程。当父母还身体健康、生活自理的情况下,他们往往独立起灶,仅仅轮流住在各个儿子家。只有他们进入暮年或有一方去世之后,赡养才进入既轮住又轮吃的阶段。我把仅仅“轮住”称作“第一轮养阶段”,把既“轮住”又“轮吃”的阶段称作“第二轮养阶段”。在平安村,在下述三种情况下父母在第一个阶段不轮住。第一,当初在分家时有一个儿子分到较多的房子(通常是小儿子,而且通常分到老家的房子),老人会久住在这个儿子的家里。第二,父母和儿子们关系闹僵,父母无奈之下借房或租房居住。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因为在村民看来,不让父母住房子是严重的不孝行为,会受到舆论的谴责。第三,某些家庭有在城市工作的儿子,父母可以长久居住在这个儿子的房子里。在我重点调査的平安村第四村民组,一共有9个家庭是这样的情况。我在讨论农村的宅基地政策时还要涉及这一问题(参见第六章)。
在轮养父母的有关事项中,首先是父母的轮养周期。轮养周期的长短并不是固定的,随着情况的变化,如父母健康状况的改变,轮养的周期会发生改变。这一周期由父母和所有的儿子商量后决定。一般情况下,父母越老,健康状况越差,则轮养的周期越短。轮养周期的长短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父母的便利程度,二是贯彻兄弟们义务平等的原则。在父母身体健康或仅仅轮住的情况下,如果频繁地搬家,显然太麻烦,因此在第一轮养阶段,轮养的周期一般较长,大多是一年,甚至更长。但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和身体状况的恶化,兄弟义务平等的原则使得轮养周期越来越短。这是因为,在老人年老和生病的情况下,赡养的负担变得沉重,周期缩短有利于儿孙们轮流休息。再者,年老的父母进入暮年后随时都有亡故的可能性,轮养周期的缩短使得兄弟们承担的义务更加平均。假设一位老人有两个儿子,他们约定的轮养周期是一年,那么完成一个轮养周期需要两年的时间。再假设老人在年中去世,如果他死于轮养周期中第一个儿子的家,那么这个儿子就会感到不公平,因为在新的一轮赡养中,他赡养了半年,而他的兄弟却一天也没有赡养。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缩短赡养周期,不论老人死在哪一个儿子家,造成的不公平是有限的。在平安村,我观察到的最短的轮养周期是10天。当老人进入生命的最后阶段,即使住在某一个儿子家,也是由儿子们轮流伺候。老人往往在咽气前或死后马上被搬到长子的家里,因为习惯上葬礼在长子家里进行。
其实,在老人身体还健康的时候,儿子们内心更欢迎老人住在自己家里,因为老人可以在很多方面帮助自己儿子的一家。比如老人可以帮助儿子带孩子,有些老人还给儿子一家做饭,干其他家务(关于老人对儿子家的贡献,请参考第五章)。我听村民讲,有一个丧偶的老婆婆有四个儿子,她每到一个儿子家就负责给儿子一家人做饭,而她的儿媳妇们却到别人家里打麻将,到吃饭时才回家。这个老婆婆几次跟儿子们提出来她自己分灶吃饭,因为她做一大家人的饭太累了,相对来说做自己的饭还能够轻闲一些。但她的儿子们(其实是儿媳妇们)都不同意,因为他们都想吃“现成饭”。只有等到老人年龄太大了,生活需要人照顾的时候,儿子们才不情愿老人在自己家里住,因为这时老人已经成为真正的负担。我在《老年人问卷》中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您的儿子们(或儿媳)是否有不欢迎您住的表示,如不按时接您、催您早走:给脸色看、不给准备床铺等行为?A。有;B。没有。”所有的老人在回答这一问题时都选择了B,但我判断这是“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在作怪。因为当我和老人们聊天的时候,有些老人就开始抱怨儿子们的上述行为。有一位老人说,有一次,她在二儿子家住满期限后,她的三儿子就是不来接她,她就跑到三儿子家里去质问她的儿媳妇为什么不来接她,她的三儿媳妇说她家里没有床。老人说,“她什么没床,她的床就放在楼上,床头和床板都在那里!”对老人来说,他们的内心是很敏感的,儿子们到时候不主动来接自己,他们就会感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更不用说为此事和儿子们争吵了。
一般情况下,多数的父母在轮养的制度中都得到了比较好的赡养,虐待老人的毕竟还是少数。但老人的心情可能并不好。李亦园在谈到“轮伙头”时写道:
但是,从父母的立场来看,吃伙头的办法对他们的权威性有很大的打击。在名义上他们虽然像活祖宗一样被供奉,但是实际上在轮流到各家去吃饭时,难免有被忽略之时,有时还要看媳妇们的脸色,甚至有的还要为媳妇收拾碗盘等等,那就很像一个老妈子了。(李亦园,2002:162)
老人在被轮养时也有受到虐待的。大陆的学者在广东普宁市西陇村观察到,“有极个别的人家,借用吃伙头来虐待老人,当轮到老人(尤其是丧偶的老婆婆)到家中吃饭的日子,儿媳妇便有意把伙食标准降低,把饭菜弄得差一些”(陈运飘,1997)。我在平安村没有发现和上述事例类似的情况,可能是老人不愿意诉说这样的事情,但我在对老人们进行访谈的时候,我能够感到他们对子女的不满。在谈到有些事情如照顾是否周到、饭菜是否可口时,老人们虽然嘴上说“好!好”!但他们在说“好”时表情很不自然。还有时,老人们在谈到一些问题时欲言又止。这从侧面反映了老人们的生活状况。
另一种赡养老人的方式是“分养”。有两种情况导致对两位老人的分养,一是一个家庭的几个儿子不是一个母亲所生;二是一个家庭正好有两个儿子,而其中一个儿子(或儿媳)和父母中的某一个关系不好,这样在分家时这个儿子就可能会提出两个儿子分别赡养一个老人的要求。在后一种情况下,一个儿子往往承担赡养某个老人的全部义务,包括生活费用、医疗费用和丧葬费用。第一种情况较为罕见,几个儿子不是一个娘时,可能造成赡养父亲和赡养母亲的儿子数不同的结果,就像第二章第三个故事中讲述的情况。我还听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我的一个受访者有兄弟六个,他排行老四,但他的三个哥哥是其父的另一个老婆所生。在分家时,几个兄弟就达成了协议,由前三个儿子赡养父亲,后三个儿子赡养母亲。这个受访者的父母已经去世好多年了。
我在平安村访问了分养父母的两个家庭。其中一个家庭的老父亲还在世,另一个家庭的老人都已经去世。第一个家庭的父亲叫做文楼,文楼有两个儿子,1980年分家时两个儿子都已经娶了媳妇。文楼和他的大儿媳关系很不好,她在分家时公开、明确地说不赡养自己的公爹。这样分家时就规定由大儿子赡养母亲,二儿子赡养父亲。两个老人的生养死葬的费用都分别由赡养自己的儿子承担,“互不相干”。不幸的是,老母亲在分家后不到一年就去世了,而老父亲至今健在。二儿子曾经向大哥提出,大哥也应当和他一起赡养父亲,但大哥坚决不同意。因为有分家时的约定和“白纸黑字”的分单,二儿子也就只好如此了。乡亲们普遍认为,二儿子其实并没有吃亏,因为文楼是一个非常勤快的老人,身体强壮,他直到前几年还在田里劳动。直到最近两三年,由于年纪(今年82岁)过大了,才不再下田劳动。我们看到,在将两个老人分养时,兄弟们平等承担赡养义务的原则转化为了“风险平等”的原则,而不是“实际”承担的赡养义务的平等。在这种情况下,谁吃亏谁沾光就看他的运气了。
第二个家庭的母亲在六年前去世,父亲去年去世。虽然两位老人已经去世了,但他们的故事有时还会成为村民议论的话题。我对老人的儿子和乡亲们进行了访谈,并且收集到了他家的分单,照录于后。分单上明确写明大儿子赡养父亲,二儿子赡养母亲。
分单3:
分家清单
立分单人高亮国、高立星经二人研究协商,愿意另居生活,并经老人同意。今将分家清单如下:
第一,高亮国今分到空院一处、南小房一间、木材十一根,钢材、砖瓦石头、水泥2吨、大小树共三棵、缝纫机一台、飞鹤自行车一辆共折款两仟元。
第二,高立星今分到旧院一所、房屋8间,包括树在内,梯子一个、小拉车一辆、自行车一辆、沙发一对。财产折价由立星再拿出现金250元给亮国,财产作价两仟二百伍拾元。
第三,善(赡)养老人:每人每年给老人除小麦450斤、玉米100斤、谷子50斤、油3斤、棉花3斤、粉条20斤、肉30斤、豆腐10斤、煤一吨,每月每人除钱4元,母人有老人房子3间。高亮国善(赡)养父亲,活者善(赡)
养,死后脏(葬)埋。立星善(赡)养母亲,活者善(赡)
养,死后葬埋。
第四,待客一对一年的待。
口说无凭,立字为证。
立分单人:高亮国、高立星
中人:赵明来、高青山、高明祥
一九八四年二月一日立
分养老人的原因我没有问出来,也许是他们有什么难言之隐,也许只是因为他们认为分养老人更好吧。如果我们不考虑风险(赡养两个老人的负担畸轻畸重)的因素,分养老人的办法对儿子们还是很有吸引力的。老人们不用搬来搬去,兄弟们也用不着为了老人的居住期限、医药费、丧葬费等问题发生纠纷。儿子们可能是省了事,但这客观上造成了老人分居的结果,费孝通已经意识到了这种赡养方式“结果成了老夫妇的分居”(费孝通,1983)。对老年人来说,年老时最大的问题就是孤独,夫妻分居不同的地方,子女又为生活和事业而忙碌,结果必然是加重老人的孤独感。乡亲们向我讲述了这对老夫妻的故事:
文昌(故事里父亲的名字)的老伴身体有脊柱炎,她的腰直不起来,弯着腰生活了几十年。老了以后,她根本就走不了路,实际上就是被关在家里。文昌的身体比较好,因此他就经常来看望他的老伴,可他们谁吃谁的饭。文昌还经常给他的老伴买一些水果点心之类的吃头(当地话,“食品”之意)给她送去。可是文昌和二儿媳妇关系不太好,她不给她公公自己家大门的钥匙。白天二儿子两口子都去上班了,他们就把大门锁上,这样文昌就进不了门。
有一次,文昌给他老伴买了一些点心,可他就是进不了二儿子家的门,因为他们都上班去了。老两口儿见个面都不容易,把两个老人分开的办法不好。
无论是“轮养”还是“分养”,产生的原因都是老人没有自己的房子。在对老人进行访谈时,很多老人都表达了希望有自己的房子的想法,而且他们特别羡慕那些有儿子在城里工作的老人,因为他们不用经常搬家。我通过访问也得知,在平安村第四村民组,有儿子在城里工作的9个家庭中,只有两个丧偶的老太太在各个儿子家轮住,而这两个老太太是因为年纪太大了才这样的,她们原来也是独立居住在城里儿子在村里的空房子里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提前把房子的所有权转移给自己的儿子,并不是完全符合老人们内心的愿望。但是,在传统和现实力量的挟持下,“生前继承”是他们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