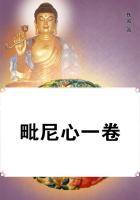这是北京普普通通的一个院落,灰色的瓦房灰色的墙,墙不高,挡人不挡盗。瓦是鱼鳞瓦,地是砖墁地,连大门也是拿黑漆油的,白天黑天一个颜色。别看这院的房舍一般,住户属于小市民阶层,而它原来的建筑布局却完全合乎京城四合院的规范。东西南北房各三间,相对相称跟麻将牌那样码成一座方城。
随着时代的变迁,如今已完全打破了原有的格局,各家各户都盖起了小房,永久的、临时的、过渡的,大大小小高高低低,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真可称得上是见缝插针,星罗棋布。就用下象棋来说吧,多数人家还是恪守老帅不出城的规矩,只是支支士、飞飞相、擓擓将,把原来的住房接出一间半间。反正四合院的中心是公海,你延伸我也延伸,只要不把领海扩大到二百海里就说得过去。可是有一户就是不管那一套,横拱竖拱就是不走回头路,过河小卒赛如车,于是遭到另一家戏弄,说这是日本人的蚕食政策。
“那也比不上您那隔山炮厉害,专隔着子儿打。马走日,象飞田,就是跑马占圈您还得蹦一阵子吧!”这话也是乐乐呵呵地说,只是话里有话。
刚才说这话的姓杨,五十,是个齐不齐一把泥的泥瓦匠。他手艺不高,至今还是个四级工。可他生儿育女却很有办法,而且品种齐全,一生就是三男三女。这是那个朝代的产物——人多力量大。可是原来那间小房搁不下这力量大,“文革”期间又因他是领导阶级,便搬大杂院来了。当时他以为这是占领上层建筑,其实也就分他两间小房住。被挤走的是个老太太。后来孩子们一天天大了,房子也就小了,再加上大儿大女在一块儿挤宿犯忌,只好找领导去要房。可是织席的睡土炕,他们单位是个施工队,会盖大楼,轮到住房却没他们的份儿。没辙,只好自力更生一下了。他自己说得好,我一个无名小卒有啥能耐?也就是会点儿手艺割得出一身臭汗呗!结果拱出个外号叫“过河卒”。
“过河卒”虽然占院里地方不少,却未引起公愤。他平时为人不错,心热。谁家盖小房都少不了他,而且是自告奋勇跑前跑后一通猛张罗。最让人忌恨的却是那位“隔山炮”,居然隔着两家的小房把房盖到院子当中来了。不仅占了大伙伏天乘凉的地方,连院里那棵老枣树也垒在屋里边,一刮风枣儿就落在他那油毡顶的小房上,连枣儿也归了他。
“隔山炮”姓钱,退休前在菜摊上卖菜,长年跟那些老太太们打交道,耳朵磨出茧子来了,不论院里人们说出多刺耳的也算你白说。可是没人理的滋味也不好受,便买了只百灵往他那纪念堂式的小房屋檐下边一挂。心里说:没人理鸟儿理,只要把食给添足了,让它叫啥叫啥。可是鸟儿不知道啥时候该叫啥时不该叫,在人们午休时仍然叫个没完,吵得街坊四邻谁也甭想睡着觉。
钱老头不是那没心计的人,他那小九九不光是在算盘上拨拉,为了得到住房他也没少动心眼子,到处去打听人们都是怎样捞到房的。他认为那些抢住公房的不是上策,抢了个提心吊胆还不见得能长久住下去,到时候还得卷铺盖给人家搬家。还有那些住不上鸳鸯楼婚后没地方趴窝的年轻人,拿被单把树一圈,结婚证往上边一挂,就在灯火辉煌的长安街边上安营扎寨过“周末”了。这是自己给自己抹黑,你自己抹的花脸自己去擦,只顾屁股不顾脸的是那秃尾巴的鹌鹑。
后来他又听说另一件新鲜事。那事就发生在朝阳门外,据说有一对新婚夫妇将一根两米粗的洋灰管子当新房,挂帘的一头还贴着双喜字。有个帮办喜事的人还用一根长杆儿挑着放挂鞭,那挂鞭是一千响,把过路人的心都快崩碎了。那二位新郎新娘也真够意思,既不恼也不怒也不觉得丢份,还热情地向前来围观的过路行人点烟递糖。这一来人们的反应可就大了,说什么的全有,就是没一句好听的。没过三天有关部门找上门来了,找他们搬家。一句口舌没费就有了房住了。
当时“隔山炮”还以为这主意高,便撺掇儿子也这么做,没想到人家偷驴他拔橛儿,刚拿砖头将一根用来修地下工程的洋灰管子堵上,就让管市容的给抓住了,说这是有意败坏首都的名声。一听这话他也傻了眼了,若是真为这些犯了法,儿子关了、媳妇散了,闹了个鸡飞蛋打到时候就是哭也哭不出韵调来。此举只好作罢。
以上这二位是院里最让人头疼的主儿,用北京人的话说那叫“没法说”。除此之外剩下的那些户就处于守势了。有的是死守,有的以功为守。
住西房的两家老街坊,三间房两家住,当中打了隔断。隔断是纸糊的。有窟窿,那屋炖肉这屋香,这屋开电扇那屋凉。过去“哥俩好”的时候,两个喝酒是隔着隔断划拳的,赖都赖不掉,能瞧得见对方出的是几个手指头。后来那个洞虽然没有糊上,拳有的时候还划,可心上却有了隔阂。其实就为了门前那块地。原来那块地是两家种花的地方,后来便一家种花一家栽葡萄。葡萄往上发展占天不占地。占地不行,各有各的地盘。种花的受到威胁为了抢争一片阳光,也把花给拔了,不栽葡萄栽树。北京这地方是讲究院里有石榴树的,过去看谁家日子过得富不富,院里得有这几样:肥狗、鱼缸、石榴树。现今的说法则是石榴花开红似火,让人看了日子过得红火。石榴熟了也让人喜兴,那咧开嘴的石榴叫“开口笑”。可是对方看了却笑不出来。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便也栽了树了。他栽的是椿树,树苗是从乡间路边上刨来的。栽树时还跟他那近邻说是受到他的启发,才想到栽树绿化北京的。绿化首都人人有责。不光净化空气夏天有阴凉,到时候还有香椿吃,香椿拌豆腐,香椿炒鸡蛋,香椿……其实他栽树的目的是因为这种树长得快,只要一扎下根便猛着劲儿往高蹿,那棵石榴树岂能遮得住它?姥姥!
在这个大院里共有十多户人家,只有一户不与人相争。他也没有什么可争的,一人一屋住着折跟头打把势都搁得下,只是有些孤单。他一生无儿无女也没有赏花弄草的兴致,更没有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想法。只能眼望着窗外去回忆小时候在树下捡枣儿的事。那会儿树还不大,枣儿却结得不少。当时的男人都留着辫子,穿长袍马褂儿,是没人上树打枣儿的,做那种事也不体面。可枣又馋人,所以一到夜里刮风的时候便摸着黑到树下去捡枣。枣噼哩啪啦往下掉跟下冰雹似的。那枣是牛心枣又脆又甜,一掉地上就碎。如今他也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这枣儿他算吃不上了,牙已全部脱落。
有时候他还常常怀念唐山大地震那个年月,那时候这个院宽敞得很,为了怕房倒屋塌砸着,人们便在院当中躲地震,全院近百口人全都挤住在一起用帆布搭的大棚下边,连夜里有人说梦话都听得见。一到下雨天大伙便往一块儿挤,越挤越暖和,不分男女。如今连那块躲地震避风雨的地方也让各家挤没了,人情也淡了,更加深了这位八旬老人对过去的留恋。
有一天,老头的干闺女讨换来两只鸟儿,对他说:“这是你大孙子敬你老人家的,一对二十块!”
老人很不落忍地说:“又让大孙子花钱,净惦着我。”
“不惦着你惦着谁呀?你是他的老祖。”这干闺女是个寡妇,不仅会说话还会办事,当老人硬塞他手里一卷钱时她接了,可是叠了叠又顺手塞到老头的衣兜里了。然后像哄小孩那样问着她干爹:“你见过这种鸟吗?”
老头说:“见有人养过,叫什么什么鹦鹉。”
“这叫虎皮鹦鹉,跟那鹦鹉不一样,鹦鹉会学舌,这鸟……”说到这儿她话停住了,又上前对老头的耳边说:“这鸟叫的声音也不小,就是贫点儿,成天喳喳。往后您就不怕他那鸟吵了。”
老头说:“若像家雀那么喳喳倒也好听,百灵鸟都有这么一口,叫家雀闹林。”
“学家雀叫倒不怎么刺耳,钱老头子那鸟还会学猫叫,又不是二八月成天闹哪门子的猫!”寡妇说到这儿又把话一转,说:“您瞧这对鸟长得多好看。上下一身绿,一个月下一窝,不出二年您这屋子就成了鸟舍了,说不定还有老外来观赏呢!动物园的飞禽馆就卖票。”
老人听了觉得他这干闺女很会说话,心里很高兴。人老了,跟前需要有个人像哄孩子那样哄他,老小孩儿嘛!
他们这门干亲是在两年前认的,当时老爷子还不太同意,他怕给人家添累赘。可院里这位街坊却说谁都有老的时候,人老了就得有个人伺候,也算是学雷锋承包到户,不认也得认。并立了字据进行了公证。一方有责任尽抚养义务,一方有房屋继承权。
虎皮鹦鹉是观赏鸟,看起来好看,叫起来难听,可它爱叫。直到把鸟笼往门前一挂,才向老爷子交了实底,是为了让他那百灵学上这口刺耳的音,才特意跟人要了这两只鸟养着的,不为听鸟语,为逗气!果然见效,这边一挂出去那边就把鸟笼给摘了,怕脏口。两家又门对门挨着,躲又躲不开,只好把他那百灵笼放进一口缸里让鸟儿与外界隔离,成天闷着。他心里说:惹不起还躲不起?这是从过去养净口百灵那里学来的做法,为了防微杜渐,就跟防那抢刀子磨剪子的“呱啦啦”的声音一样,只好让他那百灵鸟委屈一下了。
相比之下,在这个院里要数周老太太最没有反手之力了。因为她是原来这个院的房产主,尽管帽子已经没人给戴了,可还觉得头上有个箍箍着,怕有人念咒。而真正的房产主在北平解放时就跑到台湾去了,房产主的帽子自然要有人替他来顶,那时儿子还小,她这周王氏自然也就周吴郑王了。“文革”中她挨了斗,扫了街,交出了地下埋着的金银财宝,人也被从原来的大北房里轰了出去,一直住在这靠边的一间小东房里忍着。有钱不住东南房。东房夏天热来冬天凉。边上还有个厕所。后来城市改造把厕所挪到大门外去了,便成了一块宝地。自然也就成了全院人的众矢之的。可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周老太太先占一步,搬了炉子作为桥头堡,架上锅就在那里升火做饭。为了守住这个阵地,就连下雨天也不往回撤,火炉旁边插根棍儿,棍儿上撑一把伞。别瞧这破伞不起眼儿,却起到了路口交通警那把伞的作用,还真没人敢接近它。因为周老太太这煤球炉子是天天灭天天生,每生一次都要放一次烟幕弹,谁要想靠近它得先考虑考虑,又是烟又是火,没事找呛是怎么着?
多亏老太太多年坚守这块地盘,若不这回儿子回来还真没地方去住。
周老太太就一个儿子,大学毕业后为了使他跟家庭划清界线,才特意把他分配到外地去的。他学的是桥梁专业,经他建造和设计的钢铁大桥就有好多座。不知跨越了多少道江河,却未能给自己搭成一座鹊桥。不是没人愿做那搭桥的喜鹊,是他不敢接受这天河配的姻缘,在千里之外成家吧,又怕影响他对老母亲尽孝,况且像牛郎那样担着儿女也进不了北京城。在北京找个爱人吧,更是个伤脑筋的事,每年只能按探亲假的日期七七相会一次,然后再挥泪告别去做那隔河相望的牛郎织女。为此,这门婚事一直拖到今天。过去说“人过三十天过午”,“三十而立”。按说老太太的儿子年过四十才搞上对象就够晚的了,但总比看着他打一辈子光棍儿好,马王堆出土的种子照样会结出瓜来的。难怪这次儿子回京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儿子结婚。高兴得她见人就说:“托大伙的福,这是给我们家落实了母子政策。”一高兴竟然把照顾身边有一子女的政策说成了母子政策了。
为老太太的儿子结婚盖房,也算是院里的一件喜事,远亲不如近邻自然是都来帮忙。这是四合院居民特有的一种风尚。如今过河卒老杨头又成了施工的大拿,挂线、把角全是他。他腰里插一把瓦刀、一把桃花铲,手里拿一个卷尺,这儿拉拉,那儿量量,然后下着令说:“就从这儿垒,深三米二,宽三米三,三三见九,十米出头,间量够大的了。靠一边放双人床,从一边开门,这样屋里宽敞,连搁大立柜生炉子的地方都有了。然后再吊个灰顶,四白落地,像这样的新房你往哪儿找去?”
周老太太家盖新房,使全院人都喜气洋洋,同时也使一些人后悔,一些人效仿。后悔是认干爹的一家,若知道盖新房全院人会帮忙的话,当初就不认那干亲了。这等于贴上了一贴老膏药,揭都揭不下去。原以为老爷子是个棺材瓤子活不了多久的,没想到老骡子破瓦房,老爷子越活越硬朗,猴年马月才会腾出那间屋来?她儿子一直等着那间屋当新房。
为老爷子的寿数,寡妇跟儿子曾做过估计,也就是一年半载的事,谁知二年过去了还照样吃喝。老爷子还常常念叨,人到老的时候血脉亏了,非丝棉不暖非鱼肉不饱。这不是老爷子嫌伺候不周吗?有一天早晨去给倒尿盆,看到屋里没一点儿动静,窗帘也没拉,门也没开。都到人们上班的时候老爷子仍在床上挺着,脸朝上。她细瞧了一阵然后又隔着门缝用耳朵去听,连爱打呼噜的声音也没了,心想这回可熬到头了。便叫来儿子跳窗户进屋,好为老爷子穿寿衣去火化。没料到一直在床上挺着的老爷子跟诈尸那样猛一下坐了起来,大喊一声:“谁?”下边紧接着一句是“抓贼”。
今天当他那干女儿回想起来真是后悔死了,后悔当初打错了算盘。
从盖房受到启发的那栽树的两家,也想借大伙帮忙的机会大兴土木。可是树已经长大了,并进行过注册登记,不是你想刨就刨的,毁树罚款,有价,少则二百,于是种椿树那家的女人便责备起他那一家之主来了:“净出那馊点子,人家栽花你种葡萄,人家栽树你也栽树,成天盼着它往高长啊,长啊,长出事来了吧?还是棵臭椿让你当香椿树给栽上了,你说你这人臭不臭呢?”
那个被数落的男人有一定之规,挨老婆骂的时候虽然一句也不吭声,借来一把镐就去刨去了。他在心里跟自己说:多亏这棵臭椿占着,若不连这盖小房的地方也让他那“八匹马”给跑马占圈了。
就在全院人兴高采烈大兴土木的时候,市场规划局来人了,说这是违章建筑,必须得拆。毁树也在罚款之列。人们开始还以为这是敲竹杠的,便递烟递酒用好话哄他。可是人家烟酒不沾,一副包公相。没辙,只好群起而攻之了。因为有一户被拆除,其他那些违章建的小房也就站不住了,岂能让他从一户攻破?!带头反攻的是“隔山炮”,甚至连一向站在领导阶级的“过河卒”也说了过头的话:“你们还让不让我们这些老百姓活呀?”
争是争,骂是骂,最后还是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去。可是等来人一走,不知谁嚷了一句:“没有家贼引不来外患!”全院的人一怔。
骤然间,大家的目光里多了些异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