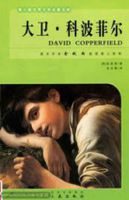步出阳光灿烂的特区机场,裴子鸿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华露打传呼。不到三分钟,回话铃就响了。到底是特区呵!他抓起电话,手竟不由自主地有点颤抖。
“喂,老婆吗?”听筒里传出一个男人粗哑的声音。
“哦,对不起,你的--”他赶紧将电话递给报亭里的女子。女子接过去听了片刻,嗔怪地将电话又递了出来:
“什么呀,刚才不是你打的传呼吗?”
他以为是号码传错了,摸出小本子来对着重拨了一遍。
“……搞什么鬼名堂!”听筒里传出怒吼,依然是那个男人。
“你是这个号吗?”他将传呼机号读了一遍。
“怎么不是呀,神经病!”
拿着猛然搁断的电话,他懵了,想不出究竟发生了什么阴差阳错。冷静了一会儿,他不得不拨了个公司办公室,回来的却是刺耳的忙音;再拨,依旧。他忽然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这座他已经在其间生活了若许年的南国大都市,在仅只离开大半月之后,一下子变得冷漠而陌生了……
电话到底还是通了。听筒里传出聂刚的声音:“老板吗?哎呀呀,还以为你撂下我们不管了呢!”
“公司的情况怎么样?”他迫不及待地问。
“一言难尽,见面再说吧。”
“事情到了你手头总离不了一个难字。”他心头陡然升起一阵不快,“我走时不是把一切都安排定了的吗?”
“情况特殊哇!”
“华露呢,在公司吗?”
“已经七、八天没露面了。”
“你说什么?”
“说得客气点儿,她出事了;说得不客气点儿,她不辞而别了。就这样。”
“狗屁!”他勃然动怒,同时一股森然冷气袭遍全身,“你几个也太容不得人了!小鸡肚肠,自己无能却又嫉妒人家做事,你以为我不晓得你们搞的鬼名堂?烂药都撒到我女儿那里去了!我无所谓,可人家还是个黄花女子,经得起这样泼污水?又要挑担子,又要遭暗算,换了我也不会干!”
“老板,老板!事情还没有弄清楚,你先别这样冲动好不好?有话回来当面说吧。”那边的声调也提高了,而且透出怨忿。
“好,所有的人都在办公室里等着!”裴子鸿气急败坏地撂下电话,出去拦了一辆的士。
聂刚在大厦门前迎候他。
办公室里只有张维东和罗伟两个人木头样地坐着,见了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
“还有人呢?”他坐到写字台前,憋着气问。
“小夏买菜去了,没通知到。”
“龙玉珠呢?”
“她还住在医院里,恢复得很慢。”
这倒是他没有想到的,压了又压,还是忍不住悻然道:“生病了还有精神到处撒人家的烂药!”
“不会吧。”聂刚道,“刚才我回忆了一下,你走后嘉玲就来过两次电话,一次是罗伟接的,一次是我接的。当时她住在隔离病房里,连医院门都不能出的。”
“哼,聂刚,果然不出我所料,你们已经抱成团啦!”裴子鸿冷笑道,“弄得我们父女反目!”
“说了半天,到底是什么事嘛?”
“还装什么?我和女助理的私情呀!”
不知是因了他的直言不讳,还是事情本身出乎意料,不但聂刚瞪圆了眼睛,另两位也都悄然坐直了身子。
“不是她作怪,就是你们捣鬼!”
罗伟凝神地望着自己的皮鞋尖,许久,才带着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抬起头来道:“老板,我说一个看法,你听得进去呢就作个参考,听不进去呢就当我没有说。我认为,做这件事的只会是一个人:华露。绝对是她本人!”
屋里的空气顿时凝固。除了罗伟,所有的人都在顷刻间变成了泥塑木雕。
裴子鸿丝纹不动地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和表情,不看罗伟,也不看聂刚和张维东,连香烟灰崩落在手背上都没有感觉。
“何以见得?”他终于开口道。
罗伟慢条斯理地作答:“其一、你走后她几乎都是独来独往,我们在办公室她回宿舍,我们回宿舍她到办公室。她有和嘉玲通电话的机会。其二、她有动机……”
“什么动机?”
“想用这种卑劣的手段使你陷入难以脱身的家庭内讧之中,以便她和她的同伙在这边实施精心策划的阴谋。”
“什么阴谋?听起来就像天方夜谭一样!”裴子鸿极僵硬地笑了一下,“她真失踪了?你们就这样肯定?”
“反正是不见人了吧。”张维东道,“整整一个星期了。那天下午三点钟左右,小夏看见她提着一个包出了门。两天后她打来一个电话,说买摩托的事被方老板骗了,第二批五百辆根本不是正宗进口货,而是走私进来的杂牌二手货,有些根本就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破烂。现在方老板已不知去向,她只有拼命出去找,找得到就回来,找不到就不回来了。还劝我们不忙去报案,说那等于自投罗网,全部东西都会被没收,而且还说不清楚。我见情况不对,竭力想稳住她,劝她回来,直接向你报告情况。她回答说没有必要了,让我转告你,请你多多保重,然后就把电话挂断了。我把情况告诉大家后,都认为其中必有蹊跷,便又给她打传呼,结果她的传呼机已经换主儿了。”
裴子鸿猛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他竭力想稳住自己,但密密麻麻的汗珠已经无可阻遏地从背心、颈项和额头上冒了出来……
“款子呢?”他近乎绝望地问。
“款子头天到,第二天就划走了。”聂刚道,“当时我还挡了一下,说不是货到了才付定金吗?她说发货票和报关单都拿到了,不会有问题。再说你也授予了她全权。幸好我盯得紧,只划走了协议上的一百八十万,还留了二十万在账上。”
“货呢,现在那些货在哪里?”
“全部堆在北郊的一个旧仓库里。据后来被我们买通的一个守库员说,这批二手摩托已在那里堆放一年多了,去年货主开价五十万都没能脱手。”
“包装都是清一色铃芝大排量,但除了码在外面的几辆看得点儿之外,其余的只能折折零件卖了。”张维东摇头不已。
裴子鸿无力地闭上了眼睛,身子不由自主地往下滑去。他依稀听见他们在喊他,又有人过来搀扶,他想说“没关系”,却没能发出声,终于被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抬到长沙发上。张维东冲了杯热果珍,一点一点地往他嘴里灌。他喝了几口,感觉好一些了,便推开众人,一个人静静地躺着。
“裴总,打个的回宿舍休息吧。”不知过了多久,聂刚过来附耳道,“我扶你下去。”
他未置可否,可发觉他们真的开始动手时,不知从哪里生出一股力气,竟挣扎着撑了起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用不着,绝对用不着!你们以为我这么容易就倒了吗?倒不了!……”
“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说你身体可能太疲乏了。”罗伟的话里带有一种此刻令他特别不舒服的哐哄味儿。
“莫多说了,我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他说着又躺回沙发。三个人也就不再劝他。聂刚找来一床毛巾被给他盖上。
约莫半小时后,裴子鸿从衰弱迷糊的状态中慢慢恢复过来。他刚睁开眼睛,三个人立即围过来。
“感觉好一点了吗?”聂刚问。
他并不理会,却恹恹地问道:“公司里发生的这些事情龙玉珠一点都不知情?”
“现在当然都知道了。”聂刚说。
“她怎么说?”
“她大哭,哭得很伤心。”
这倒有些出乎裴子鸿的预料。尽管他明白她哭的原委相当复杂,还是有些感动,说道:“过两天我去看看她。”
“她要是晓得你回来,肯定会要求出院的。”罗伟道,“她说不管你怎么对她,她都要再向你进一次忠言……”
“恐怕这也是你们的想法吧?”裴子鸿注视着围绕在自己身边的三个部下,眼睛忽然有些发潮。三个人跟他的时间,最短的罗伟也有一年了,最长的聂刚已经三年,虽说工作上也常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总的来说还是忠心耿耿,没有二心的,这在跳槽成风的特区也属难得了。华露到来之后,确实也有意无意地让他们坐了些冷板凳,可事到如今,却还不见哪个有幸灾乐祸之态或甩手离去之意……沉吟了一阵,他接着说道:
“你们几个都是与公司共过患难,对公司有贡献的人,现在我想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对这个公司还有没有信心?还愿不愿意再跟我裴某人一起去拼杀?如果你们已各有志向,我既不勉强你们,也不责怪你们,各人结清手续走路;如果你们还愿意--真心实意地愿意继续跟我干,那么从今以后,我就只有八个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请你们现在就当面给我个话。”
话音才落,罗伟的眼睛就红了,接着张维东也有些呼吸不畅。聂刚到底经的事多一些,稳了一阵,缓声说道:
“裴总,说实在的,得知你回来,我们都打算挨一顿臭骂之后提起包包走路的,没想到你却没有真正责难我们的意思,而且还说了这些有情有义的话……叫我怎么说呢?我只能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就这一点,我聂刚也愿意追随你裴总到底!”
张维东和罗伟也跟着表了态。
裴子鸿听得鼻腔发酸。自下海以来,他还是第一次从这些拿钱干活的打工仔身上如此深切地体会到情义二字的分量。他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和他们紧紧相握着,似乎只是在这一瞬间,他们才彼此真正认识了对方,而且都被一种共赴危难的悲壮氛围感动得无以复加。
第二天,裴子鸿请三个人一起在外边吃了一餐很铺张的早茶,然后就开始布置应变事宜。他要求大家首先是要保密,公司所发生的事情对外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泄露。接下来就是要到电视台去发一则启事,内容当即拟定如下:华小姐,我们在你主办业务期间,没有积极地主动配合支持,至使你的工作不能顺利开展,还遭受了不少冤屈。在此我们谨向你赔罪道歉,并对工作上的损失承担责任。现在老总已回公司主持工作,我们都殷切盼望你回公司共图大业。热诚地欢迎你早日归来!落款为你的同事小聂等。要求电视台安排在晚上的黄金时播出,连播五天。
看着聂刚他们困惑不解的神情,裴子鸿内心里远非如他表面上这般指挥如定,他甚至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为挽回危局而略施小计,还是对华露依然情丝难断。他只是想,即使是侥幸不成,至少也不会更坏,充其量破点儿小财而已。
此后几天,裴子鸿一直待在公司里,除了办公室就是宿舍,哪儿也没去。
龙玉珠出院了。人清瘦了些,话也少多了,见到电视上在播“启事”也无动于衷。裴子鸿知道她心头还梗着一口气,便主动跟她谈起华露的事情。他谈她听,木头一般,直到最后,才突然冒出一句话来,使他的所有分析、推测都变得苍白可笑,失去了分量。她断然道:
“华露百分之百是和方老板串通一气来搞的这件事情,甚至极可能原本就是方老板放出来的风筝,说不定两个此刻正在哪儿举杯同庆呢!裴总,你是太君子,太乐观了!”
裴子鸿一时哑口无言。其实,他已经想到了这一点,只是没有勇气认可,更没有勇气说出来罢了。那样的话,他就输得太惨,太不可原谅了!他宁愿相信华露是在“报复”,是在耍性子或者遇到了什么特殊而又特殊的意外。
他输不起这着生死倏关的棋!
五天“启事”播完,终于有了反响--吴铭的电话来了,开口便打哈哈:
“哎呀我说裴兄啊,怎么搞的嘛,到手的金丝雀都给飞啦!可惜,可惜,太可惜了!你看我跟你打个商量要得不:我接着你的启事再来上几天,点名聘请她到我这儿来,仁兄不会介意吧?”
裴子鸿气得发抖:“如果你找我就为这事,别怪我撂电话啦!”
“呵,别忙别忙,开个玩笑嘛,开个玩笑……”那边立即换了口气,“今天找仁兄主要为一件事情:后天我和别人合伙在石玑路投资的一处物业要奠基剪彩,不知老兄是否肯赏脸光临?”
“那得看到时是否有空啦!”他冷冰冰地说,脸上却倏然窜起一股火烧火燎之感。
“届时好多朋友都要来,包括市里的一些头面人物,共请了三百多人,办了点不成敬意的小招待,还有点小表示。来玩玩吧,权当解解闷儿……”
“感谢盛情,但还是定不了。”说罢他就挂了。
妈的,欺人也不是这种欺法呀!他忿然不已:将来老子发了,要让这些杂种都像叭儿狗似地在面前打转儿!你不能垮,你无论如何也要度过这个劫难!
一连数日,他闭门谢客,苦思苦想着挽回危局的办法。
沈郁香来电话了,谈了谈她姐姐的近况后,便直截了当地说起贷款的事情,而且就像预感到什么不测似的,一口一个“必须要按时归还本息,开不得半点玩笑呵”“到时我这头挽不起疙瘩是要坐牢杀头的哟”重锤似地打得他眼冒金星,喘不过气来,最后要他从现在开始“倒计时”!那口气使他疑心那边是不是也出了点什么问题,但他没有问,实际上是不敢问。仔细想想,沈郁香这次贸然贷款给他,也真是冒了大风险的。
束手无策中,又是几天过去了。
“倒计时”的嘀嗒声越来越频繁地在他耳畔鸣响,最后简直变成了索命的声音,弄得他白昼焦躁不安,夜晚恶梦不断。他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那个日甚一日地逼近的令人不寒而的可怕结局。再这样守株待兔地傻等下去,你不仅将毁了自己,还将使沈家两姐妹都陷入灭顶之灾!他简直不敢想像两姐妹面对骤然降临的大祸,将会作何反应……
其实裴子鸿心头已经想到了一条出路,但他一直在拼命地阻止自己靠近这个巨大的诱惑,因为他知道那已不是一般商业意义上的铤而走险--它将彻底改变迄今为止他还勉强维持着的整个人生态度,他甚至不敢深想在这条路的另一头将会是什么命运在等待自己……可是如果侥幸成功,他将至少能够保全沈家姐妹,能够为自己赢得一点喘息时间,他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再去想别的办法,或者去寻找华露和方老板,他不相信他们能够上天入地!
辗转反侧。他这辈子还从来没有这样举棋不定过,包括当年与沈郁芳分手,充军到乌蒙以及后来自砸铁饭碗等,都是一咬牙就过来了。而且他实际上很明白,这步棋基本上已属于别无选择——没有别的任何奇迹出现的可能,现在他不过是在眼睁睁地拖延时日而已。
怅惘彷徨中,一件小而又小的早已远逝的往事,忽然带着一种新的启迪,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际:当年工宣队进驻学校大办学习班时,校园里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一股偷盗自行车铃的暗流,好好的车子随便放在哪儿,转身一会儿,车铃便不翼而飞。当时单卖的车铃偏偏又缺货,于是丢了的便在没有丢的身上打主意,新丢的又去别处想办法,造成恶性循环,以至上午才偷过来下午又被偷走,这边才偷过来那边又被偷走的情况不断发生,弄得人哭笑不得。后来工宣队决定抓抓这件事情,组织大家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分析,分析来分析去,不知怎么又批判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结果越弄越糊涂,后来不得不由工宣队长亲自登台,用“大多数同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个别的,坏就坏在第一个偷的人身上”的说词下台。
当时他和大家都曾以此为笑料,然而现在,他似乎却觉得不那么可笑了。工宣队长并非全无道理。
峨岭又来长话了。他悸颤不已地听了半天,才听出说话的不是沈郁香,而是沈郁芳。沈郁芳兴奋得就像大病痊愈似地告诉他,她已经安上住宅电话了,是以郁香的名义安的,话费可以按月报销,接着便开始了没完没了的诉说,一忽儿儿子,一忽儿自己,一忽儿过去,一忽儿现在,一忽儿痛苦,一忽儿开心……他心头五味杂存,却不得不耐着性子周旋应付,只感到是在还债。有一阵她谈起学校当年的往事时,又引他想起了那个“车铃效应”的事情,极想说上几句,但不知为什么话到嘴边还是忍了,尔后就有些走神,不时陷入一种茫然空落的状态,直到电话里传出“喂喂”的叫喊,方才回过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