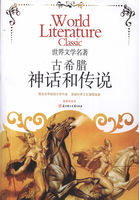不读《明良》、《击壤》之歌,不知《三百篇》之工也;不读《三百篇》,不知汉、魏诗之工也;不读汉、魏诗,不知六朝诗之工也;不读六朝诗,不知唐诗之工也;不读唐诗,不知宋与元诗之工也。夫惟前者启之,而后者承之益之;前者创之,而后者因之而广大之。使前者未有是言,则后者亦能如前者之初有是言;前者已有是言,则后者乃能因前者之言而另为他言。①
从远古的原始歌谣到《诗经》,从汉、魏到六朝,再到唐、宋、元,诗歌的发展是一代比一代好,一代比一代进步,这正是“踵事增华”的结果。但是,在叶燮这里,“踵事增华”并没有被赋予某种终极性的价值而加以绝对化,它只是艺术迁谢过程中的一个自然的现象。“踵事”和“增华”实际上是对诗歌演变的基本方式的一种描述,它将诗歌的各个阶段连接起来,使之形成“节节相生”的环状结构。在叶燮看来,诗歌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具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后人无前人,何以有其端绪;前人无后人,何以竟其引申乎?”他虽然认为后者比前者好,但并无意要否定前者,他描述诗歌三千多年的发展态势,其立意在于使得一个完整的诗歌艺术生命体凸现出来。叶燮把这个艺术生命体譬喻为“地之生木”:
譬诸地之生木然:《三百篇》则其根,苏、李诗则其萌芽由蘖,建安诗则生长至于拱把,六朝诗则有枝叶,唐诗则枝叶垂荫,宋诗则能开花,而木之能事方毕。自宋以后之诗,不过开花而谢,花谢而复开,其节次虽层层积累,变换而出,而必不能不从根柢而生者也。②
在这个譬喻中,诗歌的各个阶段构成了艺术生命体的组成部分,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不是低级和高级的关系,相互之间也不具有目的性,正如伸枝开花并不是生根发芽的最终目的一样。宁毋说,这只是生命展开的自然样态。“踵事增华”并不是一个预设好了的结果,而是艺术生命体成就自身的一道法门。如果“踵事增华”是进化论的一个必要的矢量,那么自宋以后,其“增华”的进程还必然会继续下去,并且臻达到某个更高的阶段,也就不会是叶燮所说的“木之能事方毕”,“开花而谢,花谢而复开”了。事实上,叶燮非但没有将“踵事增华”这个自然事实目的化、矢量化,反而很小心地躲闪、掩蔽这个观念:“故无根则由蘖何由生,无由蘖则拱把何由长?不由拱把则何自而有枝叶垂荫而花开花谢乎?”在叶燮看来,崇源与崇流都是不足取的,二者都没有将诗歌当作一个完整的艺术生命体来看待,“故止知有根芽者,不知木之全用者也;止知有枝叶与花者,不知木之大本者也”。
因此,叶燮的诗歌史观已经超出了简单的进化论、退化论等层面,他的真正意图在于,通过把诗歌的演变过程具象化为一个完整的生命体,探寻艺术自身演化的内在规律,从而使得人们不再纠缠于进化、退化的意气之争。而对艺术演变过程的描述和对其规律的总结探讨实际上也就是使艺术时间得以敞开的一种方式。
(原载SocialScienceResearchVolume1,Number1,June2005,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文版2005年第1期)
杨晦文艺学研究的学术成就与历史贡献
杨晦(1899-1983),原名杨兴栋,字慧修,后痛感社会黑暗,更名为晦。辽宁省辽阳县人。中国现代著名剧作家、翻译家、评论家、文艺理论家和教育家。杨晦与20世纪同龄,他的一生见证了中国现代史上历次重大的社会变革,也见证了现代中国波谲云诡的学术演变历程。五四运动时期,他与许德珩等人最先逾墙冲进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成就了一段历史的辉煌。20年代以后,他与陈炜谟、陈翔鹤、冯至四人创办沉钟社,这是鲁迅所说的“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这个时期,杨晦既搞戏剧创作,又从事翻译工作。他的“散文诗”般的独幕短剧感动了不少人,在当时的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他的外国文学译介,填补了当时中国翻译界的某些空白。40年代,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作为民主爱国的文艺战士与眼光独到的批评家的杨晦。这段时期,杨晦可谓活人多矣,许多爱国进步师生都受到过他的保护。在文艺批评方面,杨晦成绩斐然,他的“明确而精细”的批评让老同学朱自清大为激赏。从40年代中后期到整个50年代,是杨晦文艺理论思想的成熟期,他提出的文艺“公转”“自转”理论以及他对当时现实主义理论的清醒反思为后来者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理论启示,被誉为中国现代文论的拓荒者。从50年代末开始,他转向了中国文艺思想史和元曲的研究,尤其是其关于创建中国文艺思想史学科的设想,气魄甚伟,构架宏大,直接促成了北京大学古代文论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建国后,杨晦担任了十多年的北大中文系主任,培养了一大批重量级的学术人才。杨晦可谓桃李天下,贤者三千,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剧作与翻译成就
1917年,杨晦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与朱自清、顾颉刚等人同班。或许是因为自己的兴趣,或许是当时社会现实的驱使,杨晦并没有在哲学上开出一片学术天地,而是将主要的精力转向了文学与翻译。而在“五四”前后,最能发挥思想启蒙与社会教化作用的文学形式就是戏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杨晦主要是以戏剧的创作实绩确定了他在文坛上的位置。以往的文学史教材在谈到杨晦的时候,也主要介绍其在戏剧创作方面的成就与特色。杨晦一生的文学创作主要是戏剧和散文,但最能反映杨晦文学天分的还是他的戏剧创作,杨晦尤其钟情于戏剧,有一种“戏剧情结”①,他的创作、翻译、批评、文论研究都与戏剧密切相关,可以说,戏剧贯穿了杨晦整个学术人生。
杨晦创作的戏剧并不多,从《来客》(1923年)、《苦泪树》(1926年)到《除夕及其他》(共收有《笑的泪》(1926年4月)、《庆满月》(1926年9月)、《磨镜子》(1926年10月)、《老树的荫凉下面》(1926年11月)、《除夕》(1926年12月)五个独幕剧),再到《楚灵王》(1935年),公开发表的完整剧本只有8个,除了《来客》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其余全部刊载在他所创办的《沉钟》周刊或半月刊上。加上早期创作但没有发表的《谁的罪》(1922年)、《屈原》(1924年)、《夜幕》(1924年),杨晦一生共完成了11个剧本的创作。除了《楚灵王》是五幕剧,其他都是独幕短剧,这些作品选取的大多是北方农村和北京底层人民的生活作为题材,写的是说书艺人、瞎子、雇工、乡村教师、小贩等“小人物”的悲喜故事。杨晦的戏剧创作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主要作品是剧作集《除夕及其他》;后一个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代表作品是五幕历史剧《楚灵王》。这两个阶段在剧作类型、作品内容以及创作姿态方面都有所不同,显示了作者艺术思想与心路轨迹的变化。杨晦前阶段的剧作关注下层人民的贫苦命运,受20世纪20年代社会问题剧的影响,其创作多围绕当时的社会问题展开。与流行的社会问题剧不同的是,他喜欢用散文诗式的语言和气氛来写戏剧,他的散文化短剧写得“深沉黯淡”,长于点染情感氛围,带有散文诗的气息;其剧中人物之间的外在行为冲突并不突出,作者更善于展现小人物的意志与悲惨命运之间的隐忍与抗争。杨晦后期的历史剧一改“隐忍”的剧作题旨,以“搏击”的姿态来对抗社会黑暗势力,是其创作心路历程的重要转变①。
评论界关注的比较多的还是杨晦的独幕短剧。20世纪20年代,诗人朱湘认为杨晦的戏剧“有一种特殊的色彩”,因此“在近来的文坛上无疑的值得占有一高的位置”②。这种“特殊的色彩”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杨晦具有非常丰富的生活经验,对北京底层社会情形非常熟悉,所以无论是人物形象塑造还是对话,都写得鲜活自然。同时,杨晦善于运用陪衬、烘托等艺术手法映照出人物悲苦的生存境况以及坚强不屈的人格意志。唐弢在40年代这样评价杨晦的《除夕及其他》:“充满散文诗的气息,深沉黯淡,令人心碎。”③“散文诗”这一描述非常准确,杨晦戏剧大都没有在舞台上演过,有论者将其原因归为杨晦剧作的“散文化”特征④,这不能说毫无道理。诗人朱湘也明确指出,《老树的荫凉下面》“这出戏是决无排演之可能的”⑤。20世纪70年代末,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对杨晦戏剧作了一些补充:“在《沉钟》上发表的独幕剧却显示了一种比较特殊的格调。……这些作品大多截取和再现现实中的一个片断,篇幅短小,少有尖锐的戏剧冲突,但生活气息浓厚,口语的运用颇为出色。”①到90年代,学界对杨晦的剧作有较为细致深入的研究,如陈永志认为,杨晦以“悲喜互衬”的方式让剧中人物的灵魂渗透着一种悲哀的情感,这是一种“精湛的悲剧艺术”。此外,杨晦剧作中人物的“坚强意志所显现出来的信念与思想的坚执”让人感动,而这也是“杨晦对自己美学追求的自觉实践”,他最终来源于杨晦的人格魅力。由此,杨晦戏剧艺术的成就可以归因为“生活的充实”、“人生的悲悯”、“性格的刻画”、“悲剧的气氛”等方面②。杨晦的戏剧创作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独具特色,可惜未能上演,但作为戏剧创作的一种新尝试,自有其美学意义和价值,值得我们关注。
在杨晦的整个学术生涯中,翻译持续的时间最长,在1925年到1944年这20年的时间里,杨晦翻译的外国文学及理论著作达十余种,逾百万字。作为“沉钟社”的发起人和主要成员,杨晦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和西方文学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5年10月起,杨晦从英文译本转译罗曼·罗兰的《悲多汶传》,并陆续刊载于《沉钟》周刊第1、3、4、6、7期,1927年7月由北新书局出版。1931年,傅雷翻译了《贝多芬传》,但因此前已有杨晦、徐蔚南等人的译本故未能出版,十年后傅雷又重新翻译了此书。这样来看,杨晦翻译的《悲多汶传》应该是国内比较早的中译本。虽然后来出现了其他译本,但是杨晦的译介之功是不能被抹掉的。早在1926年,杨晦就开始翻译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幽囚的普罗密修士》。他在该书的小引中说到,这是他三年前(民国十五年,1926年)的旧译③,译的时候在天津,所根据的是“世界名著”中堪培尔的英译本,同时还参考过Blackie和Pottor两种译本。因为这些本子都是韵文的形式,所以当时也就写成了分行的形式。但是考虑到翻译韵文最好采用忠实而又带些诗意的散文为宜,所以最后又根据Smyth的散文译本改译成现在的样子①。古希腊戏剧研究专家罗念生曾谈到,五四运动后不久,他就读到过杨晦翻译的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幽囚的普罗米修斯》,大概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一些古希腊悲剧已经被翻译过来,除了杨晦翻译的《被幽囚的普罗米修斯》外,30年代石璞翻译了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后来赵家璧又翻译了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美狄亚》,李健吾翻译了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被绑》,叶君健翻译了《亚格曼农王》(即《阿伽门农》)②。这样看来,杨晦的这个译本就有可能是国内最早的古希腊悲剧译作,其价值当不可小觑,对于国内古希腊悲剧研究及翻译者来说,这个本子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文献资料。
由于编辑《沉钟》,杨晦同鲁迅有过一些交往,《鲁迅日记》中有多处关于杨晦的记载。20世纪20年代,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许多青年看不到社会的出路,于是堕落沉沦,消极玩世。这与俄国作家莱蒙托夫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中所描述的情形颇为相似。可能是因为这层原因,鲁迅建议沉钟社翻译这部小说。据杨铸先生编的杨晦年谱,1929年7月,杨晦遵从鲁迅的建议自英文转译《当代英雄》,连载于7月至10月的《华北日报》文艺副刊,署名寿山。但笔者认为杨晦真正动手翻译该书应该比这个时间要早,《当代英雄》篇幅很长,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恐难完成。陈炜谟在1927年11月8日写给杨晦的信中说:“你一面译《当代英雄》,一面亦该写两个剧本。”③有可能杨晦一时无法着手这个事情,所以到第二年3月初,陈炜谟又提醒他:“《当代英雄》我预计了一下,至迟四月尾便译好了。”④所以,杨晦应该在1928年就开始翻译这本书了。可能是因为时间太仓促,这部长篇的前面几章翻译得并不太理想,有许多句子都是直译过来的,因而读起来有些生硬,有些句子还带有不同程度的语病,或是不符合语言习惯,或是文白相杂,或是修饰语用得不当。但随着翻译的深入,这样的句子就越来越少了,用语渐入佳境,尤其是描绘风景的句子和人物对话的段落,译得非常流畅自然,就好像是译者在转述一个鲜活动人的故事,文字中跳跃着一种充沛且急切的情感。尽管该译作有些瑕疵,但不可忽略其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的意义和价值。自“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界对莱蒙托夫的译介就有些冷清,而且一直是将他作为天才的诗人来看待的,其作为小说家的实绩并不曾被中国读者所知晓。鲁迅早在《摩罗诗力说》中就将莱蒙托夫作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派”诗人来介绍,他自己曾计划翻译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准备在《域外小说集》中发表,但小说最终未译出,《域外小说集》也因销路问题停版了。①后来鲁迅建议沉钟社翻译这部小说,才有了杨晦的这个译本。学界认为,“这是《当代英雄》在中国的第一个全译本,并首次采用了与现在的通译名一致的名字,译文也比较忠实”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