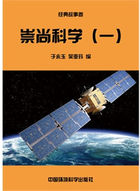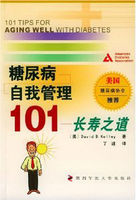“雷斯垂德,你也许对这东西感兴趣,”他拿起那块石头说,“这就是凶手用的凶器。”
“我怎么看不出来有痕迹。”
“是没有痕迹。”
“你是怎么知道的?”
“这下面的草还活着,说明石头在那里才几天,草上面没有石头拿走后该留下的痕迹。它的样子和伤痕完全吻合,再说并没发现有别的凶器。”
“杀人犯呢?”
“凶手是个高个子的男子,他左撇子,右脚不好使,蹬一双厚底狩猎皮靴。套件灰色披风,抽印度雪茄,并使用雪茄烟嘴,上衣口袋常揣把很钝的小折刀。另外有别的迹象,但凭这就足以帮我们查清楚了。”
雷斯垂德哈哈乐了。“我还是保持怀疑,”他说,“口头上说得过去,可我们面对的是顽固的英国陪审团。”
“等着看吧,”福尔摩斯平静地说:“你按你的方式去做,我照我的想法去干。今天下午我会很忙,可能会坐晚上的火车回伦敦。”
“让案子就这样啦?”
“已经处理完了。”
“我怎么搞不清楚。”
“咱们已经破解开了呀。”
“你说谁是凶手?”
“我刚才描述的那个有钱的人。”
“他会是谁呢?”
“要知道这人是谁不怎么难吧。这儿的人口挺少嘛。”
雷斯垂德抖了抖肩膀,说:“我是个着重实际的人。我不可能在这地区查找腿瘸、左撇子的男人,那样我会让苏格兰人笑话的。
“是吗,”福尔摩斯和气地说,“这是我给你的一个机会。你的住址到了,再会吧。我在走前会给你留张便条。”
把雷斯垂德留在他的住处后,我们便驱车回到了下榻的旅馆。刚一到,午饭就摆到了桌子上了。福尔摩斯默不作声地在思索,脸上出现忧郁的神情,人只有在茫然若失时才这样。
“华生,”饭桌收拾好后,他对我说,“你在这椅子上坐着,我来同你聊聊。我有点不明白,想听听你怎么说。抽支雪茄,说说看。”
“好吧。”
“是这样的。我们在解决这个案件时,小麦卡瑟的诉说有两处立即引起我们的注意,我说的这两点尽管对他有利,而你不觉得这样。第一处是,据他所言,他父亲在见到他之前就高喊‘库依!’;第二处是死者临死前怪异地提到‘阿莱特’这个词。你清楚他模糊地说了几句话,可他儿子只听清这几个字。我们只好从这两点开始破案,我们不妨认为这个小伙子说的是真实的。”
“这个‘库依’是啥意思呢?”
“嗯,我想他不是冲他儿子喊的,死者只知道儿子在布里斯托尔。他儿子听到父亲大喊‘库依’很偶然,他这喊声恐怕是引起约见的那个人的注意。‘库依’是澳洲一种典型的用语,只在澳大利亚主仆之间使用。据这,我们可以极有把握地推断:麦卡瑟在池塘会晤的那个人曾在澳洲住过。”
“‘阿莱特’又怎么讲呢?”
福尔摩斯从口袋里拿出一张叠好的纸铺在桌上,“这是我昨天打电报到布里斯托尔要的,”
他接着说,“这是维多利亚殖民地的地图。”他用手挡住部分地图问:“这几个字怎么读?”
我说:“是阿莱特。”
他把手挪开后,又问:“现在呢?”
“巴拉莱特。”
“说的对。这几个字就是死者临终前说的,他儿子只听清后面两个音节。他想说出凶手的名字,是巴拉莱特来的。”
“太棒了!”我惊叹道。
“这已经很明确了。你看,我又把调查圈子大大减小了。有件灰色披风这一点已经证明那小伙子说的没错,是实话。这回我们就不是模糊的概念了,而是扎实的目标;凶手一定是从澳洲巴拉莱特来的男人,有件灰色披风。”
“会是这样的!”
“另外还有我们今天的侦察。我对地面进行了周密察看,发现了蛛丝马迹,我连凶手长什么样都告诉雷斯垂德那个笨蛋了。”
“你又是怎样推想出来的呢?”
“你不了解我的想法吗,不就是对小细节的察看嘛!”
“我清楚你是从他迈的步子来判断他的个子;对那双靴子的推断也许是从脚印发现的。”
“是这样呀,这并不很难。”
“他走路摇晃,你又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他的右脚印总是比左脚的模糊,这说明他的重心在左脚上。从这一点看,他肯定是个瘸子。”
“你说他是个左撇子又怎么回事?”
“你该记得在审讯中法医对伤势的记录吧!打击来自正后方,而且伤在左脑,若不是个左撇子,怎么会这样呢?那父子俩会面时,凶手就站在那棵树后,抽着烟,因为我发现了雪茄的烟灰。你知道我对烟灰做过一些研究,并写了篇专题论文论述了140多种不同的烟灰,包括烟斗、雪茄和香烟。我对烟灰的特殊经验让我知道那是印度雪茄。发现雪茄后,我就到四周去找,最后在草丝里找到了他随手扔在那里的烟蒂。确切地说是印度雪茄,和在鹿特丹生产的那种一样。”
“你是怎么知道他使用雪茄烟嘴的呢?”
“我瞧出烟蒂没进过嘴,因此可断定他用了雪茄烟嘴;烟头被削掉了,但削得不平,因此可断定他口袋里的刀子不快。”
“福尔摩斯,”我说,“你简直成神仙了。凶手准会抓住,你又救了一个小伙子的命,这就像你砍断了套在他脖子上的绳索一样。我清楚这一切是谁做的,凶手就是——”
“特讷先生来啦!”旅馆服务员一边大声通报,一边推开客厅的门,把客人领了进来。
本来是个陌生的面孔,但令人记得住!他走路特慢,一瘸一拐的,弯着背,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但他那遍布皱纹轮廓分明的五官以及强壮的四肢,可以看出他力大过人,个性独特。
他的胡子卷曲、头发灰白,那双下垂的眉毛让人感到高贵、有权有势。可是他脸色苍白,嘴唇发乌,鼻孔两边发青,一看就知道他患有慢性病,已经很严重了。
“这么说您收到我的便条了,请在沙发上坐吧。”
“我收到了,看门人送来的,说是您想在这儿见我,免得引起别人传言。”
“若是我直接到您那儿拜访,我怕别人说这说那。”
“你为什么要见我呢?”他眼中充满着绝望的神色看着我同伴,像是他的事情已让人知道了。
“是这样的。”福尔摩斯说。他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像是在回答他的目光。
“麦卡瑟的事我全都明白了。”
老人用双手挡住了脸部。“愿上帝帮助我。”他大声说,“我不想让那小伙子受冤屈的,我向你保证,如果巡回审判庭判他有罪,我会把实情说出来替他澄清的。”
“您这样说我真高兴。”福尔摩斯沉重地说。
“若不是我那宝贝女儿,我早就说了。如果我被捕,她会伤透心的。”
“可能不至于到那一步吧。”福尔摩斯说。
“你说什么?”
“我不是官方侦探,我是您女儿请我来的,我在为她做事。不过小麦卡瑟得无罪释放才行。”
“我是个快要死的人了,”特讷说,“我患糖尿病已经好多年了。我的家庭医生说我不一定能活一个月。可我情愿死在自己家里,不愿死在大牢里。”
福尔摩斯站起身,拿着他的笔坐到桌前,在上面放了一迭纸。“只管把实情告诉我们,我把案情记录下来。然后您在上面签个字,华生先生可以当证人。这样,为了小麦卡瑟,在处境不利的情况下我会出示这份供词。我向您保证,不到危急关头,我不会出示这份供词。”
“这不要紧,”老人说,“我能否活到巡回审判还是个事呢,这对我没多大关系,我不愿看到艾莉丝难过。我今天就把实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你们。为这事我已经想了好长时间了,说起来也简单。”
“对麦卡瑟这死鬼你们不了解,他简直是个恶鬼!这是实话,愿上帝保佑你们永远别受到这类人的伤害。二十年来,他的魔爪狠狠抓住我不肯放松,我这一生都让他毁了。我跟你们说说这是怎么一回事。
“那还是六十年代在矿上的时候。当时我是个一身血性的小伙子,活泼好动,凡事都想去做。后来,我交了几个坏朋友,开始酗酒,由于开矿不景气,我们当了这里人所说的抢劫犯。
我们一伙六个人,过着浪荡的生活,时不时抢劫车站,或拦截那些到金矿去的马车。我有个称号叫巴拉莱特的黑杰克,我们这帮贼被当地人称为巴拉莱特帮。直到今天,那里的人还有知道的。
“有一次,一支黄金押运队从巴拉莱特驶向墨尔本,我们埋伏在路边偷袭了他们。押运队中有六个士兵,我们也是六个人,可以说阵容相当。我们是排射过去的,一下子就从马上摔下四个卫兵。我们赢了,可我们的人也死了一个。我用枪顶着押运队车夫的脑袋,就是麦卡瑟。要是我当时一枪把他打死就好了。我瞧见他那双小眼睛不怀好意地盯着我,像是要记住我长的啥样,我心一软就饶了他一命。我们带着这些黄金逃走了,很快就成了有钱人,而后来到英国,没有受到任何责难。我同老伙伴分手了,决心过一种平静、有品味的生活。我买下了刚好在市场上出售的庄园;再用一些钱做了点好事,用来弥补我以前的罪恶。我成了家,妻子早逝,给我留下了惟一的爱女艾莉丝。她还在婴儿时就用她娇嫩的小手引导我走正路。
这是我以前想不到的事。总之,我和过去不一样了,尽力做力所能及的事,本来一切都好好的,没想到麦卡瑟会突然闯进我平静的生活。
“那天我到城里办一件投资方面的事,不料在摄政街碰到他。他穿得破破烂烂,光着脚。
“‘杰克,我们来了,’他往我的胳膊上碰了一下,说,‘我们就两个人,我和我儿子,你收留我们吧,我们会亲如一家的,若不,英国的治安很严,随便喊一声,警察就来找事。’
“就这样,他们跟我来到了西部农村,再也甩不掉了。从那之后,我让他租种一块最好的土地,租金不用交。做了好事的我却无法安宁,无论走到哪里,他那狡诈狞笑的面孔总在我身边。艾莉丝长大以后,情况更不好了,他知道我怕艾莉丝了解我的过去胜过怕警察。他就敲诈我,不达目的就绝不松手。我几乎满足他的一切要求:土地、金钱、房子,后来他跟我要我的女儿,那是我怎么也不会应允的。
“你瞧,他儿子长大成人了,我女儿也不小了。大家都了解我身体很不好,他认为他儿子一定会继承我的财产,他盘算得很美。我在这点上不肯服输,并不是我对那小伙子不喜欢,可他身上流着他父亲的血。我无法忍受让他该死的血统和我的混在一起。我一百个不答应,麦卡瑟就威胁我。我骂他狗胆包天,我们约好那天中午在两家房子之间的那个池塘边解决此事。
“我赶到那儿时他正在和儿子说话,我在一棵树后边抽烟边等着,等到他一个人的时候再说。当我听到他和儿子谈的话,我的内心就鼓起了邪恶的风暴。他在催促他儿子和我女儿成亲,一点不想想她会不会愿意,就像我女儿是街边的妓女一样。一想起自己和最疼爱的女儿竟然会遭到这种人的控制,我受不了,气得发疯了。怎么不能摆脱呢?我快要死了,不怕什么,尽管我头脑还清醒,身体还强壮,可我明白这一辈子没什么意思了。我还有女儿和财产!我知道只要能堵上这张臭嘴,一切会好起来的。于是我要行动了。福尔摩斯先生,我真想和从前那样。我曾有罪,并为此遭受磨难。要让我女儿也落入那张逼我于死地的魔网,我无法忍受。我一下子就把他打翻到地上,就像打一头恶狠狠的狗。他儿子听到他的嚎叫就赶了回来,那时我及时地在树林里藏了起来。不过后来我又得回去,慌乱中掉下的披风又被我捡了回来。先生,这就是整个事件的真相。”
“行啦,我无权参与对您的审判,”当老人在那份口供上签名的时候,福尔摩斯说,“乞求上帝不要让我们受到类似的威胁。”
“是这样,先生。那你准备怎么做呢?”
“您的身体状况不好,我不准备采取任何行动。您自己心里明白,在不远的日子,您将为此受到巡回审判更高一级的审判。您的供词我会保存好,万一小麦卡瑟被处罚,我不得已会出示这份口供,可要是他被无罪释放,这就不会让外人知道,我们对您的秘密,无论您的身体怎样,都会守口如瓶的。”
“我们就再见了,”老人郑重地说,“将来您自己在临终前,想起您曾经让我平静地死去,您会有很大的安慰的。”说完,他高大的身躯慢腾腾地站起来,步履艰难地走出了房间。
“真要感谢上帝哇!”福尔摩斯默不作声了半天后说,“怎么命运总爱捉弄那些可怜、寻求帮助的人们呢?这次听到类似案件,我就会想起巴可思特所说的话,然后并对自己说:要不是上帝保佑,就没有我福尔摩斯。
在巡回审判庭的审判中,由于歇洛克·福尔摩斯起草并提交给辩护律师几份申诉书,小麦卡瑟终于被宣布无罪释放。老特讷先生在我们会面之后又平静地活了七个月,现在已经去世有些日子了。我猜测以后的日子会是这样:麦卡特的儿子和特讷的女儿一起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而对于他们父辈间的恩恩怨怨压根不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