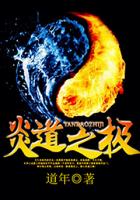攀登数学高峰的华罗庚
1979年11月9日,在法国南锡大学的礼堂里,举行了隆重的授奖仪式。中国数学家华罗庚教授,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光荣地接受了“荣誉博士”证书,这是法国授予世界著名数学家的崇高学位。可是,这位荣获国际学术荣誉的数学家的手中,却只攥着一张初中毕业的证书。
罗罗的命运
在江苏省南部,有个县城叫金坛,那是一个山清水秀的鱼米之乡。就在这个城镇的一座石拱桥旁,住着一位小商贩华老强。
1910年11月12日,华老强收购蚕茧、土麻回来,他刚放下箩筐,听得“哇”的一声,婴儿落地了。
“噢,晚年得子,恭贺大喜!”接生婆把滚胖的“老来子”捧到华老强眼前。
华老强咧开大嘴笑了起来,“嘿嘿,昨天夜里就梦见生了个儿子,特地赶回来的。”接着,他操过一个箩筐,把孩子放了进去,上面又反扣上一个箩筐,喃喃自语着:“进箩避邪,同庚百岁。”
孩子就取名叫罗庚。一个驰名中外的数学家,就这样诞生在破旧不堪的箩筐里……的确,这些破烂的箩筐,并没有给华家带来一点生气和欢乐。父亲常常担着空箩筐,垂头丧气地走进自己的小杂货铺。
那小小的柜台后面,华罗庚正在帮母亲缠纱线呢!
父亲喊着华罗庚的小名:“罗罗,帮着干活哪?”
“罗罗比他姐姐缠得还快呢!”母亲接过话头,又递给华罗庚一大支线,转身冲华老强说,“用这两天缠线的工钱,买了半斗碎米。”
父亲的嘴唇颤动了一下,没作声。
母亲叹了一口长气,“哎,这穷日子,真是清水煮石头,难熬呵!”
父亲板着阴沉沉的脸,拿起一本学算命的黄皮书《子平命理》,摇晃着脑袋一板一眼地哼哼着:“天干、地支,年、月、日、时,八字属相……”突然,父亲威严地喝了一声:“罗罗,全背下来!”
“好!”罗罗接过书把胸脯一挺说:“阿爸,我学会算命,帮家里挣钱。”
华罗庚起小记性好,过目不忘,那大小流年,背得滚瓜烂熟。他还学着给人算八字呢?七算八算,他可看出了破绽,“啊哈,全是骗人的玩意儿,原来同一个时辰的人,有着不同的命运呢!穷人总是薄命的!”
华罗庚生气地把《子平命理》往地上一扔,“屁话!一个人的命运是操在自己手里的。”他一把拉过书包,拿出代数书举在空中,冲着父亲喊了起来:
“学数学,才是真的科学呢,从这里找出路!”
罗呆子破难题
华罗庚扔掉了算命书,钻到数学里去了,他整天低着头趴在柜台上做数学习题。
有一天,父亲的一个朋友来到柜台前面,把铜板往柜台上一扔:“买根香烟。”
华罗庚没有听见,仍旧低头不停地写着。
“买烟,罗罗!”那人拉开了喇叭腔。
父亲从里屋三步并做两步跑了出来,给朋友递上一支烟。他收起铜板,看了儿子一眼,“成天抱着‘天书’,能当饭吃?!”
那人笑笑说:“你们父子俩象十二月门神,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呀!”
父亲咬着牙说:“蛇吞象,不自量!”
“罗罗,”那人又笑了笑,劝解地说,“你阿爸一大把年纪了,你还不一门心思帮他做生意,这些‘天书’给你们家攒不来半个铜板。”
华罗庚一声不响,又低头写了起来。
“哼!真是个呆子。”父亲没好气地说。
从此,街头巷尾传开了,“罗罗改名啦,他阿爸都叫他呆子”。
说真的,他的呆劲上来呀,忘了喝水,忘了吃饭,要是碰上个难题呀,小灯里的豆油熬干了,他还不上床睡觉呢!
华罗庚上初二那年,有一天,数学老师讲完课,对同学们说:“我给你们破一道有趣的难题。”
同学们一个个瞪大了眼睛。
数学老师闭起两眼,拖着长腔,脑袋来回晃悠着说道:“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剩二,五五数之剩三,七七数之剩二,问物几何?”
老师的话音未落,一个带着乡土气息的男同学应声答道:
“老师,是23!”
全班同学刷地把眼光都集中到这个同学身上来了。原来不是旁人,正是那个课外贪玩好动,不爱说话的罗呆子!
老师惊奇地问:“你懂得神机妙算吗?你懂得韩信点兵吗?”
“不懂,我没听说过。”这个朴实的学生给了一个朴实的回答。
于是老师就说开了:“这个问题,是我国古代数学的光荣,到现在,外国教科书上还命名为‘中国剩余定理’,也叫‘孙子定理’。”
“中国剩余定理?”华罗庚出神地望着老师,不知其中的奥秘,虽然他在后来的工作中,经常巧妙地、灵活地、变化多端地运用这个方法。
老师那威严而又疑惑的目光,又落在华罗庚的身上。他不知道剩余定理,不过,即使他知道用这个定理,也不至于这么快就得到答案哪!“华罗庚,你用什么方法运算的?”
华罗庚答道:“一个数,3除余2,7除也余2,那必定是21加2,21加2等于23,不刚好是5除余3吗!”
“嗯!”老师满意地点点头,又转向大家:“你们听懂了没有?”
同学们一个个瞪着大眼,望着老师。
下课铃响了,顿时,叽叽喳喳,一阵轰乱,教室里像开了锅的水。一个年纪大的同学撇了撇嘴说:“哼!呆子也会破难题,瞎猫碰死老鼠!”
可不是嘛,谁能相信小学毕业的时候,仅考了个50分的罗呆子,居然能够解开扬名中外的剩余定理。可是,谁又能知道,这个罗呆子日夜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劳动呢!
弄斧到班门为了帮助家里挣钱,华罗庚经常跟着父亲出去干点零活。有一次,华罗庚跟随父亲到金坛茧场盘点蚕茧。父亲掌秤,儿子监秤。华罗庚一进茧场,就看见堆成小山似的蚕茧,雪亮雪亮的,眼看蚕蛹就要变成蛾子,钻出茧子来了,怪不得老板敲着长烟袋,在旁边使劲地叫唤:
“快点,快点,弄不完不准吃饭。”
他们父子两个和伙计们整整折腾了一天又加大半夜,华罗庚困得脑袋直摇拨浪鼓,靠在神柜边就呼呼地睡着了。
一阵烟雾钻进他的鼻孔,把他给呛醒了。他睁眼一看:哟,香炉里直冒浓烟,旁边还围着一大排人,两手合拢抱在胸口上,嘴里念念有词:“阿弥陀佛,菩萨保佑……”父亲呢?紧锁着双眉,一动不动,像根木桩。
华罗庚一骨碌爬起来,凑到父亲跟前,“阿爸,出什么事了?”
“哎,两厚本账对不上,差上千块钱。”父亲哭丧着脸说。
场里的伙计凑到老板跟前说:“老板呀,鞋里长草慌了脚!要是出了蛾子,就全完蛋啦!”
老板扬了扬手说:“大家先吃饭去,填饱肚子再算!”
伙计们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外走去。华罗庚立在那里没动弹,父亲扯扯他的衣角:“走呀,罗罗。”
“我来看看账本,你们吃完消夜儿定定心再算。”
小伙计乜斜他一眼,笑道:“别班门弄斧啦!”
华罗庚没有作声,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哼!我偏要在鲁班门前耍一耍大斧。”
华罗庚看大家都走了,他抓过算盘,噼里啪啦地算起账来。
当大家吃完消夜儿进屋的时候,华罗庚高兴地说:“阿爸,账货对口,一文不差。”
父亲拿过账本检查了一遍,破脸笑了。小伙计跑过来,拉起华罗庚的手:“咳,真没想到你是个‘活算盘’。”
华罗庚从小就喜欢解难题,尤其是得伤寒病左腿残废以后,更是把全部精力都用在思考各种各样的数学难题上。他的老师王维克把难解的习题和新出版的数学书,破例地借给他。有一天,他突然发现大学教授苏家驹竟然解错了题,他提笔解析这位知名数学家的论文,不觉心头一笑:“嘿!这回真的要在鲁班门口抡大斧啦!”
1930年,华罗庚的《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了。
一个失学在家、卖点针头线脑的小店员,向大名鼎鼎的数学权威挑战了!
当时,在清华大学担任数学系主任的熊庆来教授,看到了华罗庚的这篇文章以后,高兴地说:“这个年轻人真不简单,快请他到清华来!”
“方法就是速度”
1931年夏天,华罗庚到了清华大学,在数学系当助理员。你看他,领文具,收发信件,通知开会,还兼管图书,打字,保管考卷,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可是到了夜间,他也从不安闲,三天两头跑图书馆。
有一天,几个同学围着图书馆的管理员问道:“嗳,华罗庚又借了几本书?”
“五本!”图书管理员伸开巴掌比划着。
“那前两天借的那大厚本《函数论》呢?”
“已经还了。”
同学们瞪着疑惑不解的眼睛:“这个大部头,至少也得看个十天半月的。可他只用几个夜晚就读完了。”
一个同学说:“像他这样看书,不是走马观花,就是浮光掠影。”
另一个同学神秘地说:“听说他长了一对猫眼,黑夜里也能看书。”
“哦,是真的?”
“那今天晚上我们去侦察一下。”
这天夜里,几个同学借着月光,悄悄地来到华罗庚的窗下。只见他翻开书本,看了一阵,关上灯躺下了,把书立在胸脯上,两眼直直地盯着它……同学们眼看着月亮跨过了树梢,爬过了房顶。这时候,华罗庚才拉开电灯,翻到最后几页看了看,脸上掠过一阵满意的微笑,便把书撂在一边,又拿起另一本书兴致勃勃地读起来。
同学们推开房门,一哄而入,“嗳,华罗庚,你是咋学的?快说,别保守啊!”
原来,华罗庚有着奇特的读书方法,他不光用眼看,而且能在黑暗里用心看。他说:“每看一本书,都要抓住它的中心环节,独立思考,自求答案。要是结论和书上一样,就不必一字一句地去记忆。因为了解了以后记住的东西,比逐字逐句的记忆更加深刻。如果说,知识是距离,那么,方法就是速度。不断改进方法,可以加快速度,缩短距离。”
就这样,华罗庚用他的“直接法”,大口大口地吞食着数学宝库里的知识营养。
他,以惊人的毅力,只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攻下了数学专业的全部课程。
他,以敏捷的才思,一口气写了三篇数学论文,寄到国外,全都被发表了,创造了当时清华园的最高记录。
数学系主任熊庆来教授亲自推荐华罗庚加入大学教师的行列,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荪,破格地接纳了这位自学成才的年轻学者。这一年,他刚满24岁。
从此,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助理员,破天荒地得到了大学教师的头衔,并且被送到英国深造去了。
人们称颂他:“华罗庚无师自通,独辟蹊径。”
青年们询问他:“成才的奥秘究竟是什么?”
请读一段华罗庚的自白吧:
“中国古代有句老话:‘班门弄斧,徒贻笑耳’。可是,我的看法却正好相反:弄斧必到班门。因为只有不畏困难,勇于实践的人,才有可能攀登上旁人没有登上过的高峰。”
天才的光荣称号,决不会属于懦弱的懒汉。
牲口棚上的论文抗日战争爆发以后,1938年,华罗庚告别了留学两年的英国剑桥大学,返回祖国,在西南联大担任数学教授。
坐落在昆明“翠湖”湖畔的这所国立大学,常常被日本重型炸弹的烟尘所污染,华罗庚每次讲完课,总要在野草丛生的校园里,呼吸一点新鲜空气,然后步行二十来里路,回到大塘子的破阁楼里。
有一天,他刚爬上低矮的楼梯,看到华师母的眼里蒙了一层泪水:“怎么,不舒服了?”
“没有。”华师母连忙用衣角揩揩泪痕,背着亮坐下了。
“米又接不上了?”
举止文静的华师母点了点头。
“又到了秦琼卖马的光景啦!”华罗庚的眉宇紧锁起来,两只熠熠闪光的眼睛,环视着这间既是卧室、书房,又兼厨房、厕所的“四合一”的房间,“还有什么可以拿出来卖的?”
“这年月,兵荒马乱的,有的教授都改行到仰光跑买卖去了,你也去找个别的门路吧?”华师母抬头瞧着丈夫的眼睛问:“是不是到哪个中学兼个课?”
华罗庚指着桌上的《堆垒素数论》的文稿说:“我哪里有时间呢。”
“总得想个办法,物价天天往上涨呀!”
华罗庚一边整理着层层叠叠的稿纸一边说:“过去,在金坛学数学的时候,全家人省吃俭用过穷日子;今天,当了教授写论文,还得省吃俭用过紧日子呵!哈哈!”华罗庚仰脖大笑起来。他那保留着稚气的娃娃型脸盘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他的一席话,说得华师母也舒展开细长的双眉:“那你就快写吧,我自己想办法去。”
“好!”
华罗庚顺手在旧棉絮上摘了点棉花,搓成细条,放在破香烟罐改装的油盏里,点燃灯芯,埋头写了起来。
突然,楼板下面传来“唔——唔——”的尖叫声。
华罗庚顺着声音从楼板缝往下看去,哦,马蹄子踏在猪身上了。他叹了口气,又趴在桌上继续写。
不知又从那里传来“咯吱、咯吱”的声响,他抬眼四下察看,发现小阁楼在晃动,他不由自主地又朝楼板缝向下看去,喝!一条灰色大水牛的脊背,正在破柱子上蹭痒痒呢!他苦笑了一声:“嘿嘿!猪马牛同圈,而我与之同息,怎能不打断思路呢?呜呼!”
夜深了,昆明的郊外,一片寂静,只有那棉纱头上的小火苗,仍旧在欢快地跳动着。
华师母睡醒一觉,看到丈夫还趴在桌上写着,“怎么?你还不睡呀!”
华罗庚调过笔杆使劲敲着桌子:“哎呀呀,你怎么也来打断我的思路呵!”
“看你这火暴性子,也不看看天都快亮了。”
“哦?”华罗庚直起腰来看了看窗外,赶忙赔着笑说,“我马上就睡,马上就睡。”
“咯吱,咯吱。”小阁楼又晃动起来,一股灰土从破旧的房顶上泻下来,落在那堆得小山头似的《堆垒素数论》的文稿上。华师母赶忙过来抖落上面的尘土,瞧着密密麻麻的数学符号说:“还没堆完哪?”
华罗庚伸了个懒腰,感叹地说:
“啊——古今中外的数学著作里,堆垒着科学家多少思维的精华,智慧的峰峦呵!”
“看你,诗兴又来了,快睡吧!”
“噢……”华罗庚强忍着腿骨的酸痛,双手撑着桌子站起来,一步一拖地走到床边。
晶莹的泪水在华师母的眼睛里浮动着,泪珠,一滴一滴落在《堆垒素数论》的文稿上……报效祖国华罗庚驾驶着瓦蓝色的小汽车,在美国阿尔巴城的一座优雅别致的小洋房前停下了。他一下车就拄着拐杖急步走进客厅,冲华师母喊了起来:
“中国解放啦!”
“什么?”华师母惊异地站起来。
“我们的祖国解放了,”华罗庚扬了扬手中的报纸,“贫穷落后的黄种人,站起来了!”
“这一天总算盼到了。”
“来美国整整四年啦!”
“昨天还梦见回上海去了呢!”华师母的眼圈红了。
“爸爸,大姐来信啦!”孩子举着信跑了进来。
华罗庚拆开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的中共地下党员、大女儿华顺的来信:“哦,有的华侨已经准备回国罗!”他那炽热的眼睛里闪动着泪花。
“那我们呢?”华师母问道。
“我们?”华罗庚推开客厅的窗户,抬头扫视着矗立在后花园中的高大的苹果树,他那英俊的脸上,酝藏着刚毅、果断的神色。突然间,他霍地调转身来,斩钉截铁地说:“叶落归根,回去,回自己的祖国去!”
“那房子呢?”华师母一边环视着宽敞的客厅和漂亮的家具,一边关切地问道。
“原封不动!”华罗庚胸有成竹地说。
“汽车……”
“先借给别人。”
“衣物呢?”
“只带随身换洗的。”
“被子,总要带几床……”
“不,两袖清风,到香港再买!”华罗庚走到沙发跟前斜躺下来,“千万不能透露风声,要是惊动了联邦调查局的先生们,就难以脱身罗!”
1950年初春的一天,华罗庚夫妇领着三个孩子,来到旧金山海湾。
美国朋友悄悄地登上海湾的码头,来送别相处四年的中国数学家、伊利诺大学的教授——华罗庚先生。
一位身材高大的数学教授走上前来握着华罗庚的手:“密斯脱华,真要走?”
“嗯,回自己的祖国去!”
“你的学识渊博,令人敬佩!如果把这一切抛到贫穷落后的国土上去,难道不觉得遗憾吗?”
华罗庚抬了抬近视眼镜,点头道:“是呀,学术研究固然是崇高的事业!可是,只有把它献给祖国的时候,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你已经被聘为终身教授,如果能继续留在美国,一定会有更多的论著。”
“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要为祖国尽力,”身量魁梧的中年数学家看了一眼自己的妻子,自豪地说,“是这样,来,是为了回去!”
和华罗庚同龄的华师母,嘴角挂着宁静的笑容,望着丈夫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