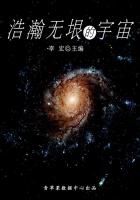对于没有小说经验的人来看,小说里谁在说话,他会毫不迟疑地说,是人物在说话。小说里谁在说话绝没这么简单,谁在说话,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声音。传统认为是作家在说话,这个作家声音肯定是没错的。但作家也有代人说话和自己说话的分别。自己说话的,作者是故事的参与者与评议者。自己不说话,找代替者,作者是隐身的,这便是一个集体意识在说话。
叙述者在说话谁也不会怀疑。但是我认为这对真正意义叙述还是一个肤浅的理解。最彻底的叙事者,应该是世界事物本身。世界作为整体向一切人敞开,包括人与事。作家只是借助了语言进行陈述,在陈述中有带作者强烈的主观意图的,也有纯客观的。我的观点是,世界事物自身与一切生命实体,他自身便是陈述者。他们是一种表达,人们只不过借助语言再说一次。例如我在小说中说,光在媒质中从一点向另一点传播时,总是顺着花费时间最少的路线。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费马说的,其实也不是费马说的,光的性质就是这样,光自身在说话。我说任何雪花的曲线总和是无穷长的,这话不是我说的,雪花自身如此表述。仅在于这个秘密由数学家科赫发现。大街上的树有阴影,遮光挡雨,这是事物自身显示的作用。如果我说望着一棵树,阳光下的樟树,枝头飞出无数金黄的蝴蝶。这是我说的,我发现了光影效果,在逆光中改变原有颜色。因此,我特别强调叙述者在讲话,应该是对人与事物一种发现,应该是一种自然的表达,即英语中含义的Nature。明白这一点很重要,这对小说家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再看谁在说话。
一、我说话。对任何一个客观对象而言都是我说话,因此才有第一人称。第一人称的发明实际告诉我们,主体是人。人体中心论。第一人称含有人对自然的霸权主义。在一个文本中我就是那个作家,那个叙述者。可是我的出场很复杂。一种情况,我会找一个替身,例如《金脑人的传说》中“我”给太太写信,“我”给太太讲故事。“我”是一个角色,人物。二种情况是作家讲述作家自己写作的故事。这种叙述叫元叙述。元叙述又有很复杂的类型,是后现代写作最热衷的叙述方法之一,关于元叙述,我今后还要重点论述到。三种情况,作品中有许多我,无数个分裂的我在说话。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这种自我的矛盾性是许多作品中都有的声音。我的长篇小说《城与市》中有无数个我,真我,拟我,人物以我的称谓谈话,主体的对象化后,我听到异者中的我。四种情况是叙述者与聚焦者分离。《没完》中观察是一个幽灵在聚焦,而叙述者是人物的我在进行。我随着人物活动叙述,并不随幽灵聚焦而叙述。
我讲述是小说中最自然的一现象。我这里要区别的是,我在文本中发现,在现实主义作品中出现,仅作为一种身份,一个替代,我一般是讲述他人的故事,外在于文本有一个明显的整体结构痕迹。《一千零一夜》便有一个山姆佐德反复讲述的故事。《金脑人传说》我讲故事没留下名姓,现实主义中我对文本没有实质性干预。
除了这个例子,我必须还要举都德的《金脑人的传说》致索取快乐故事的太太:
太太今天准备给你一点快乐的东西。我在一个离巴黎千里之遥的美丽乡村。我应该给太太一些玫瑰诗歌和风流故事。不,我还是离巴黎太近,巴黎给我送来的闲愁。我刚得到查利·巴巴的去世,心境怏怏不快,因此我还是只能给您一个凄美的传说。
从前有个金脑子的人,是的,太太,纯金的脑,医生看他脑袋太大认为活不了,最后还是活下来了,头大,走路磕碰,真可怜,常跌倒,一天从台阶滚下来,石阶上碰响,别人以为死了,他受了轻伤,头上还滴着三滴金汁。父母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们严守这个秘密,小孩只发现父母不让他去街上玩。妈说,我的好宝贝,别人会把你偷走。
到18岁父母告诉他命运给他的这个怪礼物,他们养育了他这么大也需要一点金子,孩子从脑里拿出一块桃核大的金子扔在母亲怀里,他离开祖屋去外面挥霍财富了。
在外面肆意挥霍脑子里的金子。渐渐大家见他双眼无神,终于有一天在灯红酒绿之后,孤身一人,他为金脑的缺口而害怕,于是开始新生活,去偏僻的地方工作,吝啬怕事,躲开诱惑,忘掉财富,不再染指奢侈,不幸一个朋友突然知道了。这一夜梦中醒来头剧痛,月光中看到朋友又取走了他的脑汁。不久以后,他恋上了一位金发姑娘,她喜欢他金色的外表,而且很任性,他顺从姑娘的把财源的秘密也告诉了她。
姑娘小鸟依人,总向他索要东西。这样过了两年,一天早上姑娘莫名其妙地死了。他用剩下的金子给亡妇办了一个隆重的葬礼,他把金子给教堂、挑夫,四处花费,从墓地归来脑壳又粘了几片金叶。那时他在街上失魂落魄地走,像醉汉。晚上他在橱窗灯光下看着天鹅绒蓝色缎鞋。我知道谁喜欢这双鞋。他买鞋忘了娘子已经死。店妇听到喊声,见男人拿着一双鞋站着,手指鲜血淋淋,在指尖上刮出金子送过来,店妇吓得倒退。
太太,这就是金脑人的传说。这篇故事有些玄,但从头到尾真有其事,世界上竟有这种可怜虫,他们被迫靠自己的脑子生活,用脑浆的精髓,有纯粹的金子来支付生活中的小事,这于他们是日常的痛苦,而他们在不屑于再痛苦下去的时候……
我讲故事,没错。但不是都德,是都德虚拟了一个我的身份。我是讲述者又是聚焦者。
现代主义作品中我,叙述者成为小说主体,特别超现实主义和意识流的表达。我便是叙事者本人的直接显露。伍尔芙《墙上的斑点》中实际的我,与文本中的我同位。把斑点视为各种想象物,让思维自由地扩展去联想,我成为文本的真正主体。我驱动文本中的一切细枝末节。
后现代叙事中的我,变成一种叙述策略,变成结构与解构的一种方法。但我不断地虚构故事,我又不断去干预拆解甚至反讽,想办法瓦解刚刚叙述的故事,或者用一种实以证虚的方法,用生活中各种已存在的人物与事实来证明我所言非虚。虽然二者采用了相反的方法,但目的均是针对文本的虚构而言的。《墙上鱼耳朵》便是采用的这种方法。
二、他说话。他说话一直是传统小说中的正统模式,他的标志是第三人称的,他,她,它。在西方文本中,人称变格使用。第三人称的叙述形式一直是小说的主流。这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探讨:其一,我隐退到幕后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一切都是我教给你的,而你却看不见我,这让人有一种很上当受骗的感觉,被你牵着鼻子走。但是文本却是最像小说的,人们会自觉地进入其中去充当一个角色。整体上是一个乌托邦社会,在里面自由,读者没有强迫感。其二,叙述者不出场,这突出了文本中故事、人物、环境的主体性。看不到我一个指手画脚的影子。这保持文本对读者全然一个陌生的感觉,你得到整体感知以后才明白文本是怎么回事。第三人称说话实际文本是一个自足的被镇闭的一个结构。是一个被作者设计的时空,《雨中的猫》和《海滩》三个少年在海滩上的脚印,及他自身手舞足蹈的形象,他们自己是不会注意,看不见的,而是一个旁观者在描述。在海边旅馆里有四个人物出场,发生关联,在人物之间,不可能有一个对室内室外全知道,人称的他只能在他的视听之内发生,超出人物之外的则是由叙述者概述一切在场的细枝末节,雨中的棕榈和猫、海滩,三少年影子都是一个隐在的作者表述的,问题是在一个文本发生的全部场景里,例如那个旅馆,不可能被全部详尽地像录像一样给予24小时追踪拍摄。因此,任何第三人称叙述均是选择性叙述。作者把一切都设计好,人物、故事、场景都呈示给你,是作者认为最重要有意义的部分,于是生活中还有许多你认为重要的东西都被遗漏了。选择叙述有局限,但也有几点值得注意:(1)我选择的东西均是有代表,有象征、隐喻意义。作者把主题藏起来而通过人与事暗示出来,这种阅读应该说是有启发性。(2)我选择的时空便特别适合那种封闭性的写法,如缺席法,故意不写某些东西而意图在于强化。这在《侨民》与《死者》中表现得很好。也可以把某人某心理或事物遮蔽起来,人物、事物仅徒具外形而实际内涵却很丰富,需要我们分析所获得。(3)第三人称的写法决定了我的直接干预少,文本便是一个小社会。虽然是选择的叙述反而显得比第一人称小说自然、真实。
有一个更深的理论问题,无论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只是称谓上的符号代码。从表达的本质而言,我,他种种的变体与化身,都是写作者,我。我为什么变化那么多种身份以不同面目示人呢?有文体决定的,有方法技巧的,也有根据材料而言,适合谁出面讲述的问题,例如日记体、书信体小说,无疑适合第一人称。
三、你在说。小说以第二人称方式实际是前两种的变体。注意凡第二人称均是面对面的方式,是对流的、倾诉式,这是一个特别不适合小说表述的角度,因为小说不能完全变成我跟你说心思,特定地针对你一个人编故事。因此古往今来的小说,第二人称极少。最有名的仅是一部实验小说,布托尔的《变》,小说写一个人上火车,从巴黎去罗马,以对他妻子口吻说话。这里的你只能是他和你的共同见闻。或者针对读者你,在说事,如果一段短小文字以第二人称言说,还可以,但保持在一个长篇小说中他会使叙述扭曲了,实际只要把人称变为我或者他,也不会影响作品的表达。一个情境以什么人称与什么人交流,形式上变化没有意义,意义是你的语义变化,要使用不同人称主要是改变人们在不同的观察视点上说话,不同人称是我们生活逻辑中因习惯发展来的。我是在场,他,是我不在场,你是我隐在场。上文说过你的人称仅适合双方交流的倾诉,严格来说,你,限制了在说话的方式。有针对性。而他则适合描述方式。我则适合观察方式,所以我,你,他三个人称均有很细微的表达上的分别。上面我列举了三种说话,无论人称怎么变化都是作者在说,作者可能会化装成很多种身份,甚至是混成的身份说话。我们明白了作者说话,但分析不同的文本,作者说话又成一种悬疑。作者说一些什么,这是他说的吗?真正属于作者的言语系统少之又少。因而这个我,又是一个有疑问的主体。上文举例雪花曲边总和是无穷的。因此推论,一切知识系统的表达不能算我的说话,我只是一个知识的传播者,制订知识规则的人,是一个发现者。这时我说话也是一种代词。一种我说,是代表真理而言。第二种我说,是一种时代社会价值的曲折反应。《金脑人传说》中浓厚的金钱意识与金钱批判意识,那种有效节制财富观,或者尊重知识的观念,这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人文思想。我仅代表那个社会知识分子而言,这表明文本中有一个连作者也没注意到的隐在的叙述权威。第三种我说,是我的理性在说,是我思考的结果,例如现实主义的巴尔扎克、司汤达、批判现实主义的托尔斯泰。他们说的都是针对社会时代的一种个人思考。第四种我说,是感性的表述。历史上的浪漫主义、超现实主义,发乎于身体对事物、个人、社会的直觉反应,第五种我说,是一种纯艺术想象的东西。不一定有那么多观念意图,他构筑的是一种乌托邦。这也包括那些科幻式写作,还有梦幻式的写作也属此类,当然也包括语言乌托邦式,国内孙甘露的写作就是此种。第六种我说,是一种精神幻想性,一种心理倾诉,他不以生活材料为依托而以自我呓语式。美国斯泰因便如此。第七种我说,是一种真正的我说,含有很强烈的自传性,无论生活事实和精神历程均在小说中展示。如亨利·米勒·卢梭的《忏悔录》。第八种我说,是一种创造性叙述上特别个人化的,有独特风格的例如沈从文、鲁迅、海明威、福克纳等,这一部分作家,他的叙述具有一种隐形标记,隐去作者,依然知道这是作者我在说话。我提出了八种,其实可能是无数种,谁在说,谁,真是一个问号,指涉一个有疑问的主体,即便作家本人明确地表示我在说,如果我们精细的分析文本,任何我说都是可以质疑的。
这里还有一个理论问题。法国克里斯托娃提出一个文本间概念(Intertextu-alite)他说,任何一篇文本的写成都如同一幅语录彩图的拼成,任何一篇文本吸收和转换了别的文本(《符号学,语言分析研究》145页)。这个概念被她丈夫索莱尔斯明确定义,每一篇文本都联系着若干篇文本,并且对这些文本起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的作用(《理论全览》75页)。这个概念对全世界的写作者都是一个挑战,所谓原创,绝对个人写作只是一系列神话,互文性从根本上否认了独创的存在。或许有许多人不承认他的写作是文本转抄。是的,部分人没有抄一个现存的文本。可是所有的写作者都来自无数阅读,他的脑子里已有无数大师的影子,有无数本具体的作品被他回忆,他的写作建立在这无数重叠的文本之上,沉思一下,我们的写作还有多少独创性而言呢。这时的我说,他是混成的,是一个杂种,因此,第九种我说,是一个捏泥人的师傅,是他把无数碎泥人融合了新捏出来的一个新泥人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