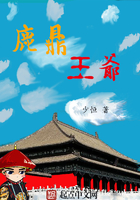1911年对于居里夫人来说,是一个大喜之年,但也是大悲之年。这一年她所经历的大起大落,足以让小说家写出一本动人的畅销小说。
从1月份开始就让人沮丧。居里夫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持有与皮埃相同的态度,即对于申请为法国科学院院士持谨慎态度,她尤其不愿意因为申请院士候选人而去逐个地拜访在巴黎的院士。因此,她在1910年以前,从来没有打算去申请为院士候选人。她的荣誉头衔够多的了,在1910年以前她已经获得了22个名誉头衔,其中包括6个国外科学院的院士,如瑞典皇家科学院、圣彼得堡帝国科学院等,她并不在意多一个或少一个名誉头衔。
但到了1910年底,居里夫人在彭加勒、李普曼和佩兰等法国最著名的科学家的竭力怂恿下,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地决定申请为法国科学院院士的候选人,争取成为院士。她这么决定,想必是她已经毫不怀疑她会当选。想一想:《论放射性》这样的权威性专著出版了,国际放射性会议也已决定将“居里”作为放射性强度的单位;纯金属镭由她单独提炼出来了……再加之同行们不绝于耳的颂扬,这些都使得居里夫人和她的朋友、助手们相信只要她申请,就肯定会当选。
法国传记作家吉鲁曾说:“她第一次表现出自以为是。”
那就是指“居里夫人完全够格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的确,以她的贡献、学术成就和国际上的威望,她当选院士绰绰有余;她所没有估计到的是在选举科学院院士时,还有许多非科学因素在起作用。她大概永远也不会明白,真才实学有时也会成为一种不利的条件,虽然不会必然如此。
著名法国生物学家卢克·蒙达尼耶曾说过一句俏皮话:
“我们法国,是一个非常讲究平等的国家。枪打出头鸟。我就是个活靶子,不仅仅因为我在科学领域获得的成功,还因为我在新闻媒介引人注目。”
居里夫人正好符合了蒙达尼耶提到的两个条件:成就和新闻人物。1903年她已经当过一次特大新闻人物,这一次为了竞选院士,她又一度成为公众关注的新闻人物。而且在这年的11月份,更成了一件轰动一时的可耻阴谋的中心人物。
法国最畅销的大报《费加罗报》在1910年11月16日一期上,迅速宣扬居里夫人的竞选。
居里夫人在我们公众中的形象可谓十全十美。她获得了高尚和令人羡慕的荣誉,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令人心灵震颤的痛苦。
《至上报》号召读者对哪些女性有资格进入科学院进行民意调查。投玛丽票的人很多,但首位不是她,是一位法国著名女作家。
《时报》也不甘落后。
面对这如潮般的宣传,居里夫人感到十分不安,她写信给《时报》编辑部,证实自己的确加入了院士的竞选。但由于学院的选举从未进行过公开的讨论,如果这一惯例由于我加入竞选而被改变,那将令我感到非常不安。
在一片赞扬声的下面,暗暗汹涌着一股反对居里夫人当选的势力,为首的反对者是院士阿玛伽门,他率领一群老态龙钟的院士们为捍卫科学院的“纯洁性”而大肆攻击居里夫人以及妇女加入竞选一事。
“无论是哪一位女人,哪怕是居里夫人,都绝不能进入科学的圣殿——科学院!”
还有一些性格卑劣的人则在民众间散布流言蜚语,不负责任地说“居里夫人是犹太人”。当时法国有一股右派势力正在抬头、发展,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军国主义狂热、教权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倾向。
居里夫人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竞选院士竟然扯到女性和民族问题上去了!如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开始的竞选形势对居里夫人还很有利,她击败了一位候选人,看来胜利在望。但在这关键时刻,选举的形势在暗暗转变,她的下一个对手是发明无线电报的布朗利。法国人认为他应该获得诺贝尔奖,为法兰西共和国争得一份光荣,但“由于某些不公正的原因”却没得到,这曾经使法国人感到十分愤怒。现在,反对居里夫人的人利用人们的这一情绪,操纵舆论,大谈“爱国主义”和“外来的干涉”,以此拥护布朗利当选,反对居里夫人当选。
“居里夫人干了些什么,竟敢与布朗利争夺院士这一崇高荣誉?她是一个波兰人,只不过是嫁给了皮埃·居里才会有今天的成就,她获诺贝尔奖的功劳应该完全归功于皮埃!”
“她在姓居里以前姓什么?姓斯可罗多夫斯基,多么古怪的姓!也许她的祖先中有犹太人的血统吧?这些人侵入了我们法国!”
居里夫人对这些蝇蝇之语,从来都是高傲地不予理睬,也许认为这些上不了桌面的玩意儿是成不了气候的。她的同事、朋友们也小估了这些邪恶势力的能量。她仍然按部就班地在半个月里,拜访了58位院士。
1911年1月23日,这天是星期一,是最后决定选举胜负的日子。4点开始,到5点才在第二轮投票中决定了胜负,结果居里夫人以28票落选,布朗利以30票当选。
居里夫人在她的实验室办公室里通过电话得知这一消息时,感到意外,也感到痛心,但她一言不发,不做任何评论。难道还需要评论吗?她把这一消息告诉实验室的同事们,他们更加感到意外。大家也深知居里夫人内心受到了伤害,因此都绝口不提这件实际上是法国科学院不光彩的事情。
居里夫人从此再也不愿提出任何类似的申请,再也不愿意为这些无聊的争论伤害自己和朋友、同事。我们从地1911年以后发表的论文看得出来,她对法国科学院的不满是很明显的:在1911年以前的14年里,她一共向法国科学院提交了16篇研究报告,但从1911年到1920年的10年里,她再没有向法国科学院提交一份研究报告,直到1921年她才提交了1篇;而且她一生再也没有申请竞选法国科学院院士,直到1922年巴黎医学科学院用一种“革命性的”办法,让居里夫人用不着申请就自动地当选为医学科学院的自由合作院士,居里夫人这才成为了法国的院士,但仍然不是科学院的院士。这显然并不是法国科学院的什么光荣之举。
如果说1911年初竞选院士的风波只是一件小的插曲,那么这年11月份法国报纸对她私生活所做的令人吃惊的毁谤,则使她遭遇到了一生中最险恶的暴风恶雨。不过,事情的原委我们得先从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索尔维会议讲起。
这年10月29日,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召开了第一届索尔维会议,居里夫人也被邀请参加了这次会议。索尔维会议是比利时著名企业家索尔维在1911年首倡召集的国际物理学会议,会议由他所创立的国际物理研究所主持召开。每次会议由索尔维出资召集20名左右世界最著名的物理学家,讨论当前物理学前沿最基本的问题,会议地点均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1911年第一次索尔维会议的主题是“辐射理论和量子”。被邀请参加的人有法国的彭加勒、佩兰、朗之万、M.德布罗意、布里渊,德国的普朗克、爱因斯坦、能斯脱、鲁本斯、索末菲、瓦尔堡、维恩,英国的卢瑟福、金斯、林德曼,荷兰的洛伦兹、奥地利的哈森诺尔,丹麦的克鲁曾等世界第一流的物理学大师。在现今保留的一张极珍贵的照片里,人们可以看到居里夫人坐在前排稍靠右处,她用右手撑着头正和坐在她右边的彭加勒一起看着什么文章,她的左边坐着佩兰,正后面站着卢瑟福。
1961年,丹麦著名物理学家玻尔曾在该年度举行的第12届索尔维会议上讲到1911年第一届会议的情形。他说:
“会上的讨论由洛伦兹的一次精彩演讲开始……普朗克自己对于引导他发现了作用量子的论证进行了说明……在会上的最后一次报告中,爱因斯坦总结了量子概念的很多应用,并且特别处理了他在低温下比热反常性的解释中所用的基本论证……”
那次会议在讨论量子论时,由于大多数科学家的不理解,反对的意见很强烈,讨论到爱因斯坦的“光子理论”,连提出量子论的普朗克本人都有非议。所以,他说“大会简直像耶路撒冷废墟上的悲嚎”。但居里夫人却十分支持爱因斯坦。当时爱因斯坦刚当上布拉格大学的教授,但格罗斯曼和赞格尔等一些人就已开始想方设法把他弄到苏黎世的理工学院任教,他们向一些关键人物提出请求,征求对爱因斯坦的意见。居里夫人在索尔维会议后不久,就应格罗斯曼等人的要求,为爱因斯坦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推荐信:
我对爱因斯坦先生所发表的有关现代理论物理学的论文极其佩服,而且,数学物理学家都公认这些论文水平很高。当我在布鲁塞尔与爱因斯坦一道参加科学会议时,我对他那样透彻的分析能力,他所掌握的如此广泛的资料,以及他的知识的深度极为欣赏。只要考虑到爱因斯坦先生现今仍非常年轻这一点,就完全有权利对他寄予极大的希望,把他看作是未来的首席理论物理学家之一。我认为一个科学机构可为爱因斯坦先生提供进行研究工作的机会,而任命他为他所应得的教授职位只会为该单位增添荣誉,并肯定对科学有极大的贡献。
居里夫人的话后来果真被证明是正确的。由此我们可知,虽然她终身以实验室为她活动的主战场,但她却有着非同一般的数理基础,而且始终对现代物理理论有很深的兴趣和敏锐的判断能力。
就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法国报纸上却突然发生了对居里夫人恶毒毁谤的事件。许多居里夫人的传记对这一段事讳莫如深,避而不谈,其实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这样反而会给广大读者留下深深的疑虑。
事情发生在1911年11月4日,这时居里夫人和她的朋友、同事郎之万教授正好在布鲁塞尔参加此后举世闻名的索尔维会议。这一天,法国的《新闻报》突然登出一条轰动而且特别有煽动性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居里夫人和郎之万教授的爱情故事”。我们且看这篇奇文开头的一段话,就能看出这篇文章作者的品格:
以神奇的光照亮周围一切的镭辐射,竟有意使我们大吃一惊:它固然点燃了勤奋研究它的作用的科学家们的心,但那位学者妻子的儿女却开始哭泣了……
这位叫豪塞尔的记者是在采访了郎之万教授的岳母后写下这段奇文的。一开始它就有一种不怀好意的煽动性。豪塞尔很会利用人类普遍具有的两种心理:嫉妒心和同情心。下面的文字就恕不引用了,那无非是一个文化层次不高的母亲在为她的女儿“伸张正义”的一些刻薄话,而且不乏造谣、无理的猜度、别有用心的含沙射影和小街巷里的飞短流长。
当然,朗之万岳母所说的也不是事出无因,只是那小人之心的恶毒,让人感到反感和恶心。我们知道,朗之万是一位出生于工人阶级的科学家,他是靠超人的才智和惊人的刻苦才走进科学家的圈子。人们很快发现这位年轻人有惊人的智慧,他的老师皮埃·居里更是对他欣赏有加,寄以厚望。在量子论还没有出现时,他就已经用“作用量子”来处理抗磁和顺磁现象,并得出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论。1906年,在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后仅一年,他就独立地推出著名的质能公式E=mc2;1911年他的有关相对论时空观的演讲,震动了科学界……总之,正如居里夫人说的,朗之万是一位“很有作为的人”。居里夫人果然说中了,他在日后的科学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于1929年被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4年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
但正当他在科学领域里大显身手时,他家里却爆发了无法和解的争吵。他的妻子也是工人阶级出身,但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在她看来,朗之万的研究工作没有任何价值,维持家人的生活还得精打细算。她没完没了地埋怨、数落,让朗之万的心情压抑到了极点。他向她讲为科学必须做出一些牺牲……然而这对他妻子一点不起作用。
他的妻子认为朗之万不是要做出什么高贵的“牺牲”,在她的简单逻辑里他一定别有所图。于是她盯住了居里夫人,还想尽办法从丈夫那儿偷到了居里夫人写给她丈夫的信。十几年来,朗之万和居里夫妇关系甚为融洽,来往也很亲密。这当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皮埃是他的老师嘛!皮埃去世以后,朗之万出于同情和尊重,常常帮助居里夫人,帮助她准备在索尔本大学开课,接替她在赛福尔女子高师的课程,当然还有科研上不间断的切磋和商讨。他们两个年龄相差不大,居里夫人比朗之万大5岁,他们在研究上志同道合,对于科学和人生的价值观又相当一致,因此彼此之间的感情确也超过一般人之间的关系,但这只是一种相互敬重、相互爱慕的高尚情谊。他们早就听到过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但他们并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他的妻子却抓住这件事,经常跟朗之万吵个没完没了,还威胁说要公布他和居里夫人之间的信件。
朗之万已实在无法忍受妻子无理的折磨和岳母尖刻的责难,他变得越来越神经质,经常无端地感到心情紧张。大学的同事们对朗之万都十分担心,害怕一位难得的人才会毁于家庭的不和。
居里夫人也为此十分忧虑,她曾对一位好友说:“郎之万教授是个有才干的人呀,我担心他会为家庭的不睦而不能自拔。他太软弱,应该救救他。他需要有人理解,需要爱抚……”
朗之万的一生是勇敢的一生,他曾为世界和平事业做出巨大的贡献,但他在处理家庭事情上却毫无男子气概。如果他当机立断地与妻子离婚,那就什么事情也没有了。但他却因为考虑到两个女儿的未来而采取了不明智的拖下去的办法。1910年7月,朗之万在大家的劝说下,离开了妻子,在巴黎租下一套房间,一个人单独过日子,但仍然没有离婚。
结果,这种不果断、不明智的做法,给了一些专在鸡蛋壳上找缝隙的新闻记者以可乘之机。于是在“他们两人到哪儿去了”的可笑猜疑中,爆发了这场可耻的“桃色新闻”事件。在巴黎找不到他们……两人私奔了?很有可能……
其实,此时他们两人正在世界最高级别的科学会议上发表意见!居里夫人在布鲁塞尔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愤怒地宣布:
“这是毁谤!”
彭加勒和佩兰宣称:
“对于报纸上对我们同行和朋友的不实之词,感到惊讶和气愤!”
卢瑟福气愤地说:“真正无聊之极!”
居里夫人决定不出席闭幕式,瞒着记者赶回巴黎。回到巴黎后,她立即在《时代》上发表声明:
我认为,报界和公众对我个人生活的所有侵犯都是极端恶劣的行为……因此我将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反对刊载与我有关的文章。同时,我有权要求一笔高额赔偿,这笔钱将用于科学事业。
在居里夫人义正辞严的驳斥下,那位《新闻报》最先挑起事端的豪塞尔自知理屈辞穷,急忙写信向她道歉,她把他写的信寄到《时代》上刊登出来。豪塞尔写道: